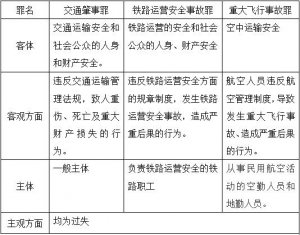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记者:看您的经历,1977年之前在公社当了三年团委书记,1978年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您还在农村挖河泥的工地上,一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后,马上扔掉手中的铁锹不再干活,回家准备去了? 何勤华:是这样的。当时一起干活的同伴,怕我继续干活,体检时又会出现肝肿大的情况,所以劝我不要再干活了。1974年征兵时,我就是因为一直在挖河泥的工地上挑担子,肝有点肿大,体检不合格,没有被录取。 记者:征兵幸亏没有成功,否则我国就少了一位法学家了(开个玩笑)。那么,您在大学里是否已经确定了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志向了呢? 何勤华:不是的。我开始比较喜欢民法,特别是婚姻法,所以我经常去从事民法研究的李志敏老师家里。后来听了张国华、饶鑫贤、蒲坚、由嵘等老师的课后,才开始喜欢上法制史。1981年考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时,看到法制史的招生名额最多,所以就报考了这个专业,下来,一直到现在就被这个专业溶化了,出不来了。 记者:法制史相比较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肯定要寂寞、清苦得多,那你有否想离开这个专业,比如下海啦,或改行搞其它专业啦,等等想法呢? 何勤华:寂寞、清苦不假,但我一直没有这种想法。主要原因还是我的性格,喜欢安静,不愿意多动。另外,总感到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搞应用法学研究受外界影响太大,许多时候,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过多少时间就过时了,法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缺陷则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它离现实要远一点。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点私心,每个人的兴趣、想法不一样。我认为,一个人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他从事此研究的理由,彼此之间应该尊重。所以,虽然我们这个专业要冷清、寂寞一些,但我还是非常喜欢法制史这个专业。 记者:那么,在近30年的法制史研究中,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何勤华:最为深刻的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界前辈的培养和提携。 如在北大读书时,得到了李志敏、张国华、饶鑫贤、沈宗灵、蒲坚、由嵘、王哲等诸位恩师的培养;到华东政法学院读研究生后,得到了我的导师徐轶民,华政的陈鹏生、余先予、苏惠渔,以及在沪上的周?、李昌道等诸位法律史学界前辈的提携。 经过这些前辈的精心培养,我从一个实际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正规教育水平,“的、得、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不清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法制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我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去日本,共呆了二年半不到的时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追随石井紫郎先生学习日本法制史。这段经历,对我的学术成长极为重要。一方面,我在日本收集了许多国内所没有的法制史资料,我的《西方法学史》和《中国法学史》两本专著中的相当部分的资料,都是在日本收集的;另一方面,在日本也学到了日本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在态度上,他们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不浮夸,不急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有的学者每天从早上到晚上10点,都在研究室中度过,从年初一至年三十,一天也不偷懒。在方法上,他们注重考证,注重小题大做,注重定量分析和微观研究,写出来的论文比较扎实。这些,对我后来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获益匪浅。 记者:说到现在,我们这个采访似乎已经很宏大,很丰富了。对中国法学研究30年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何勤华:我怕说不好。简要地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法学研究,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成果最多、进步最为突出的。虽然,当前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不平衡,我们在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如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精品还不多;研究方法运用得不少,但一以贯之、分析透彻的还不多;古代文献、外语文献运用得不少,但真正深入进去又钻得出来、融会贯通的还不多;中青年学者已经不少,但能够沉下心来、甘于寂寞、耐得住坐冷板凳的还不多;课题申报、项目经费投入不少,但产出量尤其是产出高水平的成果还不多,等等。 但毕竟我们已经步入了法学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已经成为我们的国策,成为我们全体法律人的奋斗目标。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已经溶入了法治建设的宏伟事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法学工作者当尽全力,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