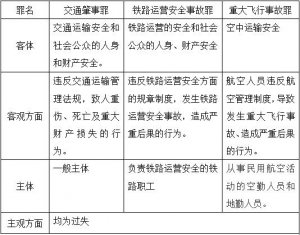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我还将“三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结了起来,我是这么说的:“上述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既然史学与法学研究,通过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方法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为什么作为史学与法学之综合学科的外国法制史学,不能张开双臂欢迎‘三论’这一现代科学方法呢?” 记者:这话听听也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虽然“三论”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可以说只是昙花一现,90年代之后就不再看到这类文章了,但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中国法学界对新的研究方法的敏感和追求,对繁荣中国法学研究是否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何勤华:应该是的。在法学研究方法上,我这里还要突出讲一下田涛教授主持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这一方法,田涛率领一批年轻人深入浙江、福建、安徽、山西等山区、农村,调查明清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以及现在还在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等所谓民间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推出了黄岩调查档案、徽州调查档案等珍贵的法律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法科学子”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家动乱了整整十年,年轻一代感觉被耽误的太多,所以,大家一旦考入了大学,就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希望将被耽误掉的青春追回来。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人,或农村,或工厂,或部队,或机关,或讲台,因此,进了大学在当学生时期,就开始收集资料,从事科研活动。 记者:说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研究的进步,还必须提及我们法学教育所培养的对象即法科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科研热情。您感觉你们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有些什么差异呢? 何勤华:差异还是很大的。 当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就是复印机也没有普及。我们要收集点文献资料,主要是靠做读书笔记、制作卡片。 我记得我们班级里的武树臣同学,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开始辛勤地制作卡片,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收集中国法律思想史方面的史料。 说出来现在的同学可能也不太相信,那时因为穷,用来作卡片的纸也是废物利用,将用过的废纸裁成一张张和五寸照片那样大小的片卡,在反面进行摘记。由于武树臣同学这种卡片做得特别多,大概有上万张吧,所以我们私下里就叫他“卡片大王”。 记者:非常有意思。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状况发生变化的呢? 何勤华:从80年代中叶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我们收集资料搞研究就方便了。到80年代末起,就有了电脑打印的业务。90年代以后,个人电脑就开始慢慢普及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科研就更加方便了。 那时,虽然出版条件不如现在,但是大学生搞科研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在我们读本科期间,就积极参与老师主持的研究课题,如我本人就在二年级的时候和两位师兄一起,参与了李志敏老师的一个课题:“买卖婚姻研究”,课题完成后,我们以专题论文《试析买卖婚姻》的名义,在北大法律系“五四”科研报告会宣读,接下来就被刚复刊的《法学研究》录用(1982年第2期)。 记者:听你们那一届的同学讲,武树臣当时参与了张国华老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课题,姜明安、李克强、陶景洲等参与了龚祥瑞老师的宪政课题,郭明瑞参与了王作堂、魏振瀛老师的民法课题? 何勤华:是的。不仅如此,当时我们学生还自己独立地编写法学著作,如还在一年级时,我们小组的何山(现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工作)就组织大家编写《法律基础知识讲话》,花费半年多时间完成的初稿有20多万字呢。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这部书稿最后没有能够公开出版。 记者: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搞科研的积极性不如那时的大学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何勤华:也不能说现在不如当时。主要是时代变化了,学生的情况变化了。当时,法学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读法律的学生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上考来的,经受过各种生活的磨练,甚至是受到严重伤害的生活磨难,所以,当他们一旦进入了大学这一知识的殿堂,又拥有一种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感受的环境,那么,他们就很自然地试图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对人生、对社会以及对知识的体会(体验)表达出来,这就催动了他们写作搞科研的热情和激情。我们那时科研的情景就是这样的。 我就举一个陈建功的例子吧。他虽然不是我们法律专业,而是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但他就住在我们隔壁一幢宿舍,他们的科研情况我们比较了解。 我记得大概是大二时,在他们中文系宿舍的墙壁上,经常会贴出陈建功创作的小说,写着很清秀的钢笔字体的稿子,一页页贴在墙壁上,看的学生围着一圈又一圈。热闹时,我们个子矮的学生在外边只能踮着脚隔着人头远远地看,好在当时脚劲也好,视力也好,以这样的姿势半个小时下来还不算太累。 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如小说那么吸引人,但某位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在同学之间传阅,让大家提意见,最后再让老师修改等等,当时就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班上的何山、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李克强、陶景洲、陈兴良、周振想等,在当时都是这样的科研积极分子。 记者:当时,上海复旦大学的卢新华写出《伤痕》,可能与你们这种情景差不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