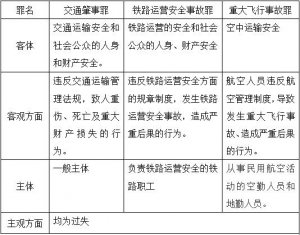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李老师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该主任住的宾馆,但宾馆的人说他出去了,李老师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始终没有见到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师通电话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告诉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书稿就先放着吧。 另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徐轶民教授接受一家出版社委托主编的《法制史词典》的出版。这是一部由我们教研室全体成员参加的、也是填补学术空白的作品(费时近10年)。 出乎意料的是,当词典编出来后,该出版社不愿意出版了(主要是出这类词典可能会亏本)。这一消息,对徐教授的打击非常大,他感到没有办法向教研室全体教师交待,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着觉,安眠药从一颗增加到三颗。最后,也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以我们承包一部分词典的销售为条件,在河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词典是出版了,但徐老师从此落下了一个每天晚上不吃两颗以上的安眠药就无法入睡的毛病。 记者:听来也真是辛酸。联想到现在学术著作出版的繁荣,真是今非昔比啊!中国法学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从哪一年开始热起来的呢?在您印象里,哪几家法律类的出版社引领了法律图书的潮流,或者说功不可没? 何勤华: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0年,全国各个学科出版的法学著作加在一起也不到10本,且内容非常单薄,字数也很少,如谷春德、吕世伦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和杨大文等著《新婚姻法基本知识》,都只有7万余字,张友渔、王叔文著《法学基本知识讲话》,金默生、柴发邦、刘齐珊编著《国家和法律基本知识》,龚祥瑞、罗豪才、吴撷英著《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等,也都在10万字左右。 中国法学学术著作出版的顺畅,大体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改观的。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 从1991年起面世的“中青年法学文库”,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和当时的编辑丁小宣策划的中国第一套法学学术文库,而且以作者平等、文稿质量、学术创新为入选标准,不要任何资助,也不要作者包销,张文显、王利明、徐国栋、陈兴良等中青年学者都参与其中,对当时的中国法学学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律出版社紧随其后,推出了“当代中国法学文库”、“中国当代法学家自选集”、“中国律学丛刊”、“中国传世法典丛书”等,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法学研究者,以及将一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品保存了下来,介绍给了后人。 “书店,也是法学研究变迁的一个窗口” 记者:听您说的这些,让人很是感慨。确实,我们也都能意识到,现在几乎每一个出版社,都在出版法学研究的著作和丛书,法律图书已是书店的新宠儿。可以说,我们现在书店经销的图书品种,也是中国30年法学研究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不知你们当初读书时,书店的法律书多不多? 何勤华:在改革开放之初,书店中几乎看不到一本法学著作,过了几年,开始有了一些法学著作,印象比较深的,如吴大英、任允正著《立法制度比较研究》,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孙国华等著《法学基础理论》,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唐宗瑶著《法学基础理论概述》,许崇德、何华辉著《宪法与民主制度》,高铭暄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江平编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王家福等著《专利法基础》等。 但与文、史、哲的著作相比,放的位置还不是很起眼的。 记者:这种现象似乎从80年代中叶有了改变,法律图书在书店经销图书中的比例开始上升。90年代以后,变化更加迅速。听法律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讲,仅他们一家出版社,一年就要出500余种法律图书。这在您看来,很不可想象吧? 何勤华: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书店里不仅法律图书的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各地还都开设了一些法律专业书店,如当时在上海曾经很红火的“法律书店”等,专门经销法律方面的图书文献。 除了法律出版社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这两家法律出版行业的领军舰队之外,还有如人民出版社的“当代著名法学家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法学文库”,三联书店的“宪政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教材系列”;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法理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的“犯罪学大百科全书”和“华东政法大学珍藏民国法律名著丛书”,等等。 就连一些理工科大学,也都出版了不少高水平的法学著作,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汉语法学文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法学读本”等,有些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还把出版的丛书分成各种系列。我们走进书店后都要仔细辨认,才不会弄错。 记者: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推出了“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里面重点推出一些法学名家的研究专著系列。现在法律图书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支柱产业了? 何勤华:确实如此,从书店这个窗口看到的上述变化,让人感慨万千。我记得,20年前即1988年我去日本进修时,看到书店里面一些最醒目的地方放的都是法律书,而且法律图书在书店中都要占据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数量时,就感叹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可能至少需要一百年吧。没想到,短短20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这一目标,真的让人振奋! “法学刊物,经历的变化要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