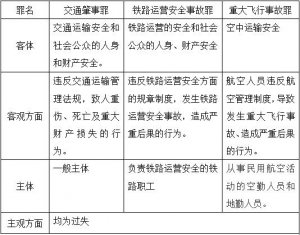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说起那些比较大的影响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学术讨论,何勤华教授回忆,从大的方面来说,80年代中叶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关于法的本位(权利还是义务)问题”、“关于人权问题”、“关于法律文化问题”、“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社会主义法的本质问题”、“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大讨论。 在他看来,不管得出的结论如何,这些讨论都进一步繁荣了我国的法学研究,推动了中国法学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记者:由学术研讨会,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法学界曾经的学术争鸣,改革开放30年来,法学界爆发了多次学术大讨论,这些讨论,对法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于1979年发生的“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从资料上看,这次大讨论在两年时间内共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参加了,是这样吗? 何勤华:是的。比如李步云、华辉、刘新、谷春德、吕世伦、吴大英、刘瀚、张警、周柏生、方克勤、张晋藩、曾宪义、张国华、高格、韩延龙、刘升平、孙国华、沈宗灵等,都积极撰写论文,参与讨论。不仅如此,还有许多非法学专业的领导干部和知名学者如陶希晋、于光远、于浩成等,也非常的投入。当时讨论的成果,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取名《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由群众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记者:那么,通过当时的讨论,大家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何勤华:当时的讨论,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大体上是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要法治,不要人治;二是既要法治,又要人治,两者应该结合起来;三是不要讲什么法治与人治,这两个概念都不科学。 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取消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发展,很快便失去了大家的支持。持第二种即“结合论”观点的学者,强调法律是不能“自行的”,总要人去制定和执行,这种观点将法治与人的作用对立起来,没有理解法治的内涵中包含了一个法学家阶层,随着我们对法治的真正含义的把握,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中国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记者:紧接着“法治与人治”大讨论,展开的是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 何勤华:是的。这场讨论的背景是我们刚从“四人帮”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大家在谈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时还心有余悸,故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指司法适用上的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在立法上,不能讲人人平等,因为对那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就不能参与立法活动,对社会各阶级也不能一视同仁。而其他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我国宪法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平等,体现了公民在立法活动中参与立法的平等原则。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便进一步取得共识:在立法和执法等各个方面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和保障。 “30年来,法学研究的方法丰富多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界在方法上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多次革命。从大的方面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中国法学界慢慢地溶入到这一时代之中,我国法学研究的方法也变得多元和丰富多彩。如历史主义的,比较法的,分析主义的,社会学的,经济分析的,心理学的,结构主义的,文化阐释的,后现代主义的,伦理主义的,以及知识考古学的,田野调查的,民间法角度(法人类学)的,等等。这些方法的运用,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学研究的繁荣,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记者:在学术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催动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早一般都是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后来开始运用一些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很有趣的是,听说中间还曾流行过一阵用“三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何勤华:所谓“三论”,就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将“三论”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8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做法。我记得,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来的。他在1985年4月26日召开的“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题目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强调要把系统工程和信息控制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 在钱先生的号召下,整个法学界都行动了起来,出现了一批运用“三论”研究法律的论文。如严存生的《运用系统论于我国法制建设》、黎建飞的《运用系统论加强法律监督》、马洪的《犯罪侦查的信息方法初探》和刘茂林的《宪法中有关问题的系统论思考》等。而有的论文就直接将“三论”作为标题,如1985年第4期的《法学季刊》就刊发了韩修山的一篇文章:《“三论”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科学方法》。 记者:文章主要提出了哪些新的立论呢? 何勤华:比如,文章中说:“‘三论’的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中日益发挥出重大作用,并且日益向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普及。可以说,只存在现在还没有引入和运用‘三论’的科学,不存在将来不能引入和运用‘三论’的科学,法学也不例外……‘三论’是思维的新工具、新方法,是人脑在考虑问题时不可缺少的新式武器。” 我自己于1988年6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外国法制史研究方法新探”,在该文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用“三论”方法研究外国法制史的必要性。挺有趣的,具体内容为:“外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把新的科学方法引进该学科中来,使之成为推动外国法制史学发展的锐利工具。具体而言,‘三论’中如下原理对该学科研究有指导意义:第一,系统观念;第二,动态观念;第三,信息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