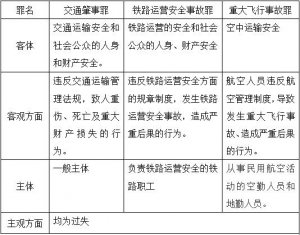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过失论从旧过失论到新过失论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是纯正的过失犯大量出现所推动的结果。对此,西田典之教授曾经指出:“主张基准行为说的背景在于,从昭和30年代到40年代(1955年-1965年),随着汽车的急速普及,业务过失致死罪的发案件数也急剧增加。如果按照传统观点,认 为过失属于预见可能性、责任要素,由于驾驶汽车本身便属于危险的行为,因而便能很容易地肯定预见可能性,进而认定成立过失犯,但这样一来,无疑意味着不允许驾车,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更是无法构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该说主张,鉴于汽车交通所具有的便利性,应该以一般人作为标准,只要采取了一般人而言具有合理性的结果回避义务即基准行为,即便具有预见可能性,由此所出现的结果也属于被允许的危险,并不具有违法性。”[11]由此可见,新过失论所主张的基准行为说其实是限制了过失犯的范围。因为,日本刑法中的交通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都以业务过失致死罪论处,而业务过失致死罪是一种特殊的过失致死罪。根据旧过失论,对于业务过失致死罪在构成要件阶层不作考察,只要在交通过程中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就在责任阶层认定是否具有过失,则十分容易入罪。而根据基准行为说,在构成要件阶层进行考察,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基准行为,即使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也不能认为构成业务过失致死罪,这就起到了限制过失范围的作用。由此,新过失论肯定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的旧过失论也开始承认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在构成要件中独立考察的必要性,这是在向新过失论靠拢,因此称为修正的旧过失论。这就是山口厚教授所说的,在立足于旧过失论立场的同时,对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作限定理解的见解。[12]这里所谓限定的理解,就是指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予以定型化处理。 应该指出,日本刑法中的业务过失致死罪虽然属于业务过失犯罪,但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纯正的过失犯。因为业务过失致死罪与过失致死罪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系特别法与普通法的竞合。对于业务过失致死罪,即便在构成要件阶段不进行实行行为的考察,完全可以采用过失致死罪的实行行为,而过失致死罪又与杀人罪共用杀人的实行行为。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基准行为还不是为纯正的过失犯而专门设立的。这也与日本刑法大量的业务过失,其中主要是纯正的过失犯并不在刑法典中规定,而是在附属刑法中加以规定这样一种立法例具有重要的关联性。 基于在刑法典中主要规定的是不纯正的过失犯这一事实,在各国刑法典中,对于过失的规定都是以不纯正的过失犯为摹本的,而根本没有顾及纯正的过失犯。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5条和《日本刑法典》第38条都没有对过失的正面规定,因而没有涉及过失的具体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德日刑法典对过失都是在与故意对比的意义上进行规定的。这个意义上的过失,是指不纯正的过失。相对来说,《意大利刑法典》关于过失的规定,既包括不纯正的过失又包括纯正的过失。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3条第1款规定:“在结果,即使有所预见,不是出于行为人的希望,而是由于疏忽、不谨慎、无经验,或者不遵守法律、法规、命令或者纪律等原因而发生时,是过失。”意大利学者指出,当该款规定提到“疏忽、不谨慎、无经验”时,是指源于社会一般经验或科学技术经验的抽象规则,违反这些规则的过失即所谓普通过失。而当该款规定说到“不遵守法律、法规、命令或者纪律”时,则是指包含于专门规范中的具体规范,违反这些规范的过失,人们称之为特殊过失。[13]以上所说的普通过失就是不纯正的过失犯,而特殊过失主要是纯正的过失犯。由此可见,刑法关于过失犯的立法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法典中的过失概念。 我国刑法摈弃了附属刑法的立法方式,将所有的犯罪,包括过失犯罪都规定在刑法典中,形成所谓统一刑法典。因此,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大量的纯正的过失犯。对于这些纯正的过失犯,除了少数罪名以外,大多数罪名都在罪状中对过失行为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可以提炼出纯正的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这些实行行为是对基准行为的违反,因此,基准行为说对于纯正的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的认定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不纯正的过失犯与纯正的过失犯在实行行为上还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不纯正的过失犯是以过失而犯故意之罪,因此,其实行行为基本上与故意犯的实行行为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不考虑主观要素的前提下,对实行行为进行认定。例如,对于致人死亡的案件,无论是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在客观上都必须具有致人死亡的行为。因此,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实行行为在实质上并无根本区别。纯正的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是其所单独具有的,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纯正的过失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业务过失与职务过失,在分析纯正的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时,应当考虑以下三点。 1.行政法规违反行为的性质 纯正的过失犯一般都是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的,例如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就将该罪的客观行为描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我们判断基准行为提供了法律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规定了交通运输人员的结果回避义务,因此,违反相应法规的行为就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的行为,同时也是基准行为的懈怠。根据行政法规的违反可以为过失的实行行为的定型化提供某种可能,而不致于使基准行为的判断变得过于恣意。然而,这里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将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直接认定为过失的实行行为,会导致过失犯沦落为行政法规违反行为的结果加重犯。例如,西田典之教授指出:根据行政取缔法规的义务判断基准行为,违反这些义务的即为过失,其结果便是:业务过失致死罪便成了这些违法行为的结果加重犯。[14]这就提出了行政法规违反行为与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