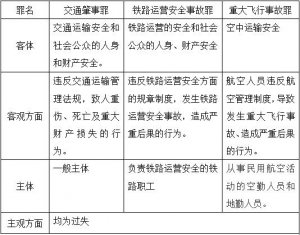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以上所列举的纯正的过失犯,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事故型过失犯罪,二是渎职型过失犯罪。事故型过失犯罪是指发生在生产、作业或者其他业务活动中,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过失犯罪。可以说,事故型的过失犯罪一般都是业务过失,因此具有业务过失的特征。而渎职型过失犯罪是指发生在职务活动中,违背其职责,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过失犯罪。可以说,渎职型的过失犯罪一般都是职务过失,因此具有职务过失的特征。 值得讨论的是,在我国刑法中存在较多的法条竞合的情形。例如,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致人死亡的内容,因此,交通肇事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如果在刑法中没有规定交通肇事罪,则对于这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能否认为交通肇事罪实际上对应于故意杀人罪,由此否定纯正的过失犯的概念?显然,这是一种实质分析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就罪名而言,交通肇事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虽然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包含过失致人死亡的内容,但其内涵已经超出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强调交通肇事罪的独立性。唯有如此,才能确立纯正的过失犯的概念。 三、法理分析 纯正的过失犯与不纯正的过失犯的分类,为正确认识过失犯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两类过失犯虽然都具有过失犯的共性,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其个性。这就需要从刑法教义学的理论上,对纯正的过失犯与不纯正的过失犯的有关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一)对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规定理解的意义 我国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与这一规定相对应的是刑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以上两款规定构成刑法理论所称的“刑法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4]的原则。这一原则,我国学者也称为“法定原则”[5]或者“过失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在对这一规定的理解上,我国刑法学界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在此,“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从我国学者有关论述来看,大多将这一原则视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物。换言之,我国学者都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理解“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这一规 定,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就已存在,而当时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以前,我国刑法学者一般都将这一规定理解为排除类推适用的法律根据。例如有学者指出,“这一原则的涵义是:过失犯罪的具体行为都必须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过失行为,不论其社会危害结果如何,都不得追究刑事责任,包括不得以类推定罪。笔者认为排除运用类推对过失行为定罪量刑的规定是确定这一原则的主要的立法意图。”[6]以上理解,在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将之作为限制类推适用范围的法律根据,在该特定语境下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但是,以上理解也会受到质疑。因为这一规定并非我国刑法的独创,而是各国刑法规定的通例。也就是说,在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国家,其刑法典一般也都规定了类似我国刑法“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条款,只是表述上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5条规定:“故意之行为始有可罚性,但法律明定处罚过失行为者,不在此限。”根据这一规定,对于过失行为的处罚仅限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又如,《日本刑法典》第38条第1款规定:“没有犯罪的故意的行为,不处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不在此限。”在此,《日本刑法典》虽然没有提及过失,但这里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显然是指过失。这些国家的刑法都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为什么还要对过失行为的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呢?显然,在此,排除类推适用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即使在我国刑法中,1997年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条款依然保留。 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必须在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所解决的是行为的可罚性的法律根据问题。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进行扩张的解释,例如,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是指刑法分则,而不包括刑法总则。当然,这里的刑法分则也包括附属刑法的分则规范。罪刑法定原则中的“规定”,是指对于构成要件行为的规定,而不是对犯罪成立所有要件的规定。因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紧密关联的,它主要是犯罪论体系的第一阶层,即构成要件阶层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因此,只有结合古典的构成要件理论才能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目前犯罪论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罗克辛的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试图挖掘出罪刑法定原则除了限制司法权滥用的消极功能以外的积极功能,指出:“在既有的自由的保障机能之外,罪刑法定原则也有了指导人们举止的目标;这样,该原则就成为变革社会的工具,而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工具。”[7]尽管如此,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功能还是通过限制国家司法权以保障人权,其对于构成要件的规制机能并没有改变。以此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可以得出其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关联性的结论。因为,这一规定是解决故意与过失的处罚根据问题,其逻辑位阶在行为可罚性的法律根据之后。 解释论上,对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何理解,在我国刑法学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因为在我国刑法中,除了部分过失犯罪,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不纯正的过失犯以外,其他过失犯罪,主要是指纯正的过失犯,在刑法分则中并无“处罚过失”的明文规定。对于这种刑法总则规定与刑法分则规定之间的疏离与脱节,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刑法教义学上的解释?张明 楷教授认为,对于这里的“法律有规定”存在以下三种理解:一是将“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法律有明文规定”,即只有当法律条文对某种犯罪使用了“过失”、“疏忽”、“失火”等明确指示过失犯罪的用语时,该犯罪才属于“法律有规定”的过失犯罪(明文规定说)。二是将“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法律有实质规定”,即为了实现分则刑法条文的法益保护目的,只要有必要处罚过失行为,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认定为“法律有规定”(实质规定说)。三是将“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法律有文理的规定”,即法条虽然没有“过失”、“疏忽”、“失火”之类的用语,但根据具体条文的文理,能够合理认为法律规定了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时,就属于“法律有规定”,因而处罚过失犯(文理规定说)。[8]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张明楷主张文理规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