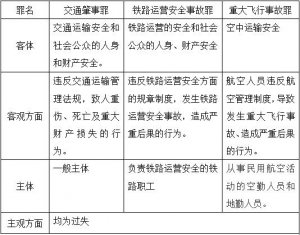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印度的火车,有许多人是坐在车厢顶上的,在那块并不平坦的铁皮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有时候分明已经十分拥挤了,看见下面有追着火车跑的,已经坐稳的人群中必定还会伸出几只大手给拉上去,然后再生生地给腾出一小块空地,一起安详地坐下。在这样的场合,倘若有人稍微骚动一下,坐在边上的那几位八成得掉下去。但据说印度火车顶上的秩序比车厢里还要井然,除非火车相撞,从未出现过意外事故。 这个国家虽然并不富裕,但医疗和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虽然物质有些匮乏,但人人都透着坦然平和;所有的公共资源都真正做到了共享,不光与人,还包括与动物们共享。对比其他有些国家,印度的这种现象并不那么容易理解,但当看见一边走一边诵经的苦行僧时,恍然明白作为一个宗教之国,在印度,宗教的力量主要是用来塑造秩序的,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信仰。 最早的秩序来自于自然,“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诸如二十四节气、顺天应时、自然哲学等无疑都是对自然秩序的社会解释和应用。但人终究无法完全厘清自然运行的全部内在和真正机理,尤其是早期人类对于斗转星移之类的变化只能依靠观察和感悟来认知,所以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惶惶然的敬畏,对神秘的敬畏,也就是对自然机理和秩序的敬畏。这种敬畏后来成为宗教之“端”,再后来成为法治之“基”。 自始至终,敬畏、秩序、宗教、法治这些东西都是共生共存、相互强化的。 信念并非是原生于自然的东西,因为它是功利性的,宗教在经过组织化之后才有了“信念”一说,而在未被组织化之前只是关于敬畏和秩序的,宗教的组织化过程就是将利益植入原发的敬畏精神和自然秩序的过程。至于世俗生活中的“信念”就更是纯粹的利益导向了,坚定一种信念,其实也就是要追逐和维护一种利益。 轴心时代,东西方的智慧都建立在对自然的观察基础上,直觉和顿悟是主要方法,虽然所形成的哲学观点受制于文明所在的地理环境,比如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就烙有四季分明的痕迹,但本质上却是殊途同归。那时候古老的宗教还没有形成气候,也不存在意识形态,因而轴心时代的思想光辉是朴素自然和生生不息的,因而也是令人着迷和经久不衰的。 但后来的发展之路出现了分歧,西方文明对秩序和敬畏的源头进行了建制,从而形成了宗教和宗教组织,将神和宗教理念解释为万物之源,让万千受众成为上帝的子民。东方文明则对秩序和敬畏的过程和方式实施了建制,从而形成了中央集权和天人合一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此之后,西方文明中的秩序基本上靠理性主义支撑,更强调对人性的尊重和引导,并且在些基础衍生出了法治;东方文明中的秩序基本上靠管制主义支撑,更强调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随着宗教与世俗的分化,西方宗教的这种本源性质越来越明显,逐渐收缩为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对于社会秩序的突出作用体现为底线确立和情绪排解,促进形成一种守底线、求超脱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建构民主、法治等各种制度自然更为容易。 管制主义是短期效用十分明显的治理方式,对于主流利益的维护效果相对突出,因而制度一旦成型,就很难再改弦易辙。但这种制度偏重于过程和方式,缺失源头管理和精神疏导,显得理性程度不足,情绪化、运动式的倾向比较明显,以至于管制的过程中总觉得社会道德水平不够,造成对个人修身和榜样示范较为倚重。而且因为管制本身就具有过程性,与法治的程序化范式也存在一定冲突。 但印度似乎是个例外,与上述两种文明完全不同。印度教虽然具备典型的宗教特征,但一直奉行着多神主义、生命神圣、种姓制度、因果报应等原则,具有明显的原发宗教色彩,尚未进行过足够的建制化转型,仍然停留在直接作用于社会秩序的层次,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与伊斯兰教有些相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事实上也很难在这些地区建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底线意识和自发式社会秩序的确立,因为有宗教的存在。 这大概就是从印度的火车顶上都能感受到宗教和秩序的原因。(文:人半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