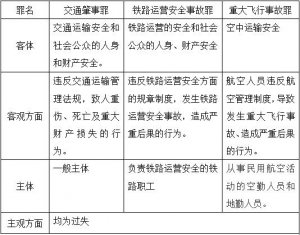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下弦月,疏落的星,鸡鸣划破了寒冷的空气,光秃秃的树枝上有冰粒掉落,我走出家门,扣上帽子上的扣子,开始往西边走。 往西,是洛阳,离我们村三十里。这三十里不算很远,但在我看来,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洛阳是城里,我们是乡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洛阳是繁华的标志,身份的象征,即使现在,如果在村里碰见人问他去哪里,他说我去洛阳,那口气还透着抑制不住的得意。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洛阳的情景,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头天晚上听父亲说第二天去洛阳,我嚷着要跟着去,父亲没办法答应了。睡到半夜,我迷迷糊糊地醒了,伸手一摸,没有摸住父亲。坏了,父亲已经走了,没有叫我。我赶快穿衣,撒腿就往外边跑,母亲在后边喊我也不理。那时候天还没亮,不多的几颗星挂在天空。农村的夜空旷寂寥,我的脚步有回音,就好像有人在后头跟着一样,心里害怕极了。顺着村西边的渠沟,我一边跑一边喊父亲,一边回头往后边看,一直撵到十亩坑才撵上父亲他们。坐在生产队的胶车上,坐在父亲身边,我贪婪地看着两边的田野、村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在黎明前的朦胧里。实际上,那次我没去成洛阳,说是去洛阳,只在洛阳郊区的一个村子装了东西就回来了,连洛阳的城墙都没有看见。 再去洛阳,是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哥去卖菜。哥骑一辆自行车,带两大麻包菠菜;我骑一辆自行车,带两大麻包菠菜。也是冬天,也是快过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路还没现在这么好,疙里疙瘩,上坡下坡,一路上趔趔趄趄、东倒西歪的挣扎。走到分金沟,我碾住一块砖头蛋儿,车子一下子栽到边沟里。哥停好车,把我的车拉出来,扶正,然后我们俩继续往前骑。小北门那里有条街,可以摆摊儿卖东西。路面上结着冰,背阴,风嗖嗖地吹,冷得我的脚都麻木了。菠菜不好卖,太老了。菠菜嫩的时候,父亲不舍得卖;等到老了,父亲又不管了。母亲对我说,你和你哥去卖,卖的钱算你明年的学费。生意很不好,便宜也卖不动,天快黑了还有一多半没卖完。哥让我看住摊儿,自己不知道去了哪里,回来后就让把菠菜装起来,推到了一个饭店,一下子卖给了人家,估计是连送带卖踢打了踢打。就这样,我和哥连续卖了几天,总算卖完了讨厌的菠菜。 高考那年我考的不错,一举过了本科线。我报的是郑州大学法律系,担心录取不了,我央俊州哥领着我去找启明哥,他是我们一个村的,人事局副局长。那是我第一次进到城里,前次去的小北门在城墙外边。看见宽阔的马路,马路上奔跑的汽车,高大的楼房,茂盛的梧桐树,我觉着好像到了天堂一样。最后很幸运我被郑州大学录取,从而走出了小山村,走向外边的更大的世界。 大学毕业的时候,双向选择,学生选择单位,单位选择学生。我很想到洛阳工作,润平哥领着我去找他妻子的表哥,表哥在洛阳日报社工作。洛阳日报社没有指标,没去成。我又找了殿卿叔,殿卿叔说区划调整,三门峡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肯定大量需要人才。他给黑子哥打电话,推荐我到三门峡工作。黑子哥是公安局的局长,很爽快,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天中午我赶到三门峡,黑子哥领着我到办公室,亲自写了接受函,让丽丽盖章,这样我就到了三门峡,与洛阳失之交臂。 之后我到了重庆,到了广州,多次从洛阳经过,有时也住上几天,但始终感觉是过客,没有根,留下的印象也没有之前那么深了。 我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一个小时到了白马寺。白马寺属于洛阳,但是离洛阳还有二十里。在我眼里,白马寺就是一个镇,和洛阳相比差远了。我找了一个饭馆,喝了一碗羊肉汤,然后搭车回家。我今天的任务只是散步,让自己离洛阳更近些而已。 洛阳是一个梦,直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