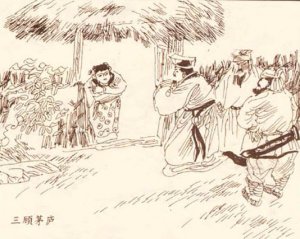|
古典刑法以对法益造成的实际侵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标准,具有较为浓厚的结果责任色彩。而进入20世纪以来,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社会的复杂多样决定了风险的无处不在,而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有必要消除或者降低这种社会风险带给人们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因此刑法介入提前化、预备行为实行化的问题逐步进入刑法学研究范畴。为了更好的保护法益和维护社会秩序,某些对法益有侵害或者侵害危险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现实的侵害结果,仍然会受到刑法处罚,某些犯罪的预备行为、抽象危险行为为刑事立法所确认和规制。众所周知,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被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并给诸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将实施恐怖活动之前的组织参与培训行为、联络策划行为、准备工具等预备行为实行化,规定专门的法定刑,并不以恐怖活动的实施为入罪前提。其中既有刑法理论的依据,又包含刑事政策的考量,是在反恐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立法机关对风险社会的有力回应。随着犯罪标准的前移,相应实行行为的范围也有所扩张,如《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要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将结果犯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以及删除《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中“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将具体危险犯规定为抽象危险犯。 但是以传统刑法观来审视风险刑法理论,学界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拷问,质疑的内容主要有:风险刑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否有违罪责原则?此类质疑不无道理,传统刑法原则经过了千百年的洗练,成为如今刑法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其根基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依据。但是笔者认为,风险刑法并不是对传统刑法之否定,恰恰是在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刑法的补充和例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刑法规制的前移,从而更加周延地保护法益,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肯定风险刑法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下对其提出严格的标准,以防过度干涉民众自由。笔者认为,法益保护前置化需要明确界域,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预备行为的发生具有高概率;第二、预备行为对法益具有紧迫的现实危险;第三、前置化所保护的法社会价值优位于个人价值。 在抽象危险犯的视阀下看贩卖毒品罪的行为方式,诚然,在风险社会中,刑罚处罚的范围不断扩张,处罚的时间点也不断提前,预备行为实行化,法益保护早期化,这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惩治毒品犯罪的需求。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可知,无论是“贩”还是“卖”都是贩卖毒品罪中常态化、高频率的行为,所以具有惩罚的现实必要性;“出卖”行为使毒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进而损害公众身体健康,而“为卖而买”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害结果,却使禁止流通的毒品进入了购买者自由支配的领域并最终会流向市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增加毒品伤害公众身体健康的危险;从法价值衡量来看,社会范围的公共安全价值要高于个人的行为自由。如果等到公众的健康已经被毒品所现实侵害的时候才发动刑法保护已为时过晚,行为人只要不是因为自己吸食而购买毒品,其“为卖而买”的行为就已经使毒品具有了向社会公众扩散的抽象危险,因此无需等到“出卖”之时才发动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毒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8],而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种抽象的表述并不能揭示刑法分则规定毒品犯罪的目的。有的论著指出:“贩卖毒品罪直接侵害国家对毒品购销活动的管制。”[9]但是这并不是法益保护问题,而是有无违法阻却事由的问题。张明楷教授指称,法益必须与人相关联,刑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故只有人的利益才能成为法益,只有人的利益才值得刑法保护。由此反观,贩卖毒品罪所处罚的不能仅仅是已经损害了公众健康的行为,还要对其进行提前保护[10]。 正因为如此,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即对“贩卖”行为坚持广义的、实质的解释。并认为在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以风险刑法作为传统刑法理论的例外和补充,是一条积极可取的进路。 (二)“以贩养吸”行为模式 以贩养吸,顾名思义是指吸毒者直接实施毒品贩卖活动,并将非法所得用于购买毒品进行吸食的行为,或者是吸毒者将购买的毒品一部分用于自己吸食,剩余部分用于有偿转让的行为。由于犯罪标准前移保护的主要是社会公法益而非个人私法益,所以我国刑法只惩罚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毒品贩卖行为,而非惩罚损害个人身体健康的吸食行为(一般只做治安违法处理)。较之于纯粹的毒品贩卖者,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以贩养吸”的主体界定困难,“贩”是手段,“吸”是目的,而对行为人目的的主观判断主要是基于其是否有吸毒背景这一客观要素,此种判断方法很容易将贩卖毒品的吸毒者都作为“以贩养吸”处理,进而放任了毒品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以贩养吸”的数量认定困难,在风险社会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背景下,我国对其数量认定方法从注重“出口”转而注重“入口”,并允许“反证”的运用以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1、 数量认定的争议 案例中于某在2013年7月间购买冰毒,部分用于自吸,部分卖给他人,是典型的“以贩养吸”被告人,其后于某又购买冰毒30余克进行分装,警方最终在其住处查获冰毒31.9克。对于这种“贩”与“吸”的复合行为,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争议焦点主要体现在:从被告人处实际查获的毒品是否计入贩卖毒品数量,在量刑时是否考虑其中部分毒品可能被吸食的情节。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应当将有证据证明其卖出的毒品数量和实际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但对于实际查获的毒品在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其被吸食的情节,很明显案例中某州市法院持此观点,认为应将搜查出的31.9克毒品计入贩卖毒品的数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应当将有证据证明其卖出的毒品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而对于实际查获的毒品因没有证据证明其是用于贩卖还是自己吸食,不能一概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而应该以非法持有毒品罪来定性。案例中公诉机关持此观点,认为31.9克毒品应为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 2、“贩卖毒品”数量认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