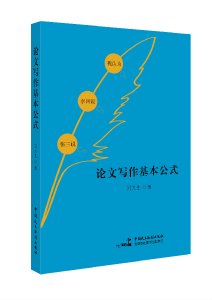|
——《西北法律资源研究》集刊序 前些日子,在微信朋友圈里,我发了一条帖子,就西部学术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表达了我个人的一些忧思。虽然有些观点可能因激愤而难免偏激,但其也确实是我长期观察西部学界后的肺腑之言。不妨借这个序言,把该段留言照录如下: “昨晚有些失眠,才起床。原因多样,其中之一是一位长期工作在西部学界、且工作极努力、成果极显著的朋友,说他准备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认为西部高校只重权术,不重学术。我回之曰:‘西部高校基本都是这个样。与东中部相比,学术的落后还会继续扩大并延续下去。’他回应说‘很精辟’。尽管在西部不乏雄心勃勃、踏实肯干的学界中人,但不能不说的是:在那里,总体思维方式仍深深地陷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所以,在人际交往中,炫耀自己如何扳倒‘敌人’,如何让‘敌人’难受了一下子,就是人们在耳边常能听到、并且被大话特话的话题,无论某些‘大’领导,还是不少普通工作人员,皆有此弊。同事们之间听到或看到某人因有成绩而被奖励、被赞许时,立马会招来相互告发、相互揭短、相互排斥的一封封信件:比对不同人的来信,似乎那里人人都很烂似的!这自然导致其相互间的协作精神、欣赏意识、怜悯情怀、团结技术即使不是说荡然无存,也确实是很稀缺的资源。 于是,顺昌逆亡、任人唯亲;打压英才、笃信蠢才;勾心斗角、惟权是尚,就司空见惯——虽然东中部地区在某些领域,此弊亦存,甚至也很严重,但在需要硬指标的经济、学术等领域,明显要好很多。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此种情形,甚至体现在某些貌似很有才华的学者身上,一旦为‘官’,便横行霸道,便嫉贤妒能,便自划‘势力’,便排斥异己,便培植‘特务’。这些观念因素再加之西部在财力上的捉襟见肘,我才与朋友在如上交流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东(中)、西部的差距,特别是学术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差距,还会持续下去。不少朋友知道,我的热爱西部,是渗透于骨子里的;我对西部的寄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或许因此,我对西部目前的失望,也是发乎肺腑的。 圣人云:失礼求诸野。吾国虽告别‘文革’近40年,但‘文革’遗风,在西部的学界尤盛。如下结论既或许是一个体制话题,也或许是一个文化话题——就个体观察,西部学人人人都很好、且吃苦耐劳、才华横溢,也都是很可交的朋友;但就群体观察,西部学人至少有对半熟悉相互拆台、习惯相互鄙视、擅长相互戕害,这常令我深怀忧心。或许我的上述言论,会伤及很多西部朋友的心,但借昨晚和朋友的如上对话,说出来,也算是我对西部朋友们的逆耳忠言,甚至小小贡献。”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会、也不可能会全盘否定西部学术界的巨大努力。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学术格局中,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一样,都是我国学术整体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学术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其也理所当然应被置于国家文化结构体系中)。这正如中国的政治结构体系、经济结构体系一样。无论在哪种结构中,西部在该结构中的缺席,皆意味着相关结构存在的破损。一种破损的结构,事实上也是无效的或者低效的。因为结构毕竟是一个整体,其效果既须从整体性中获得,也需要各要素、各部分互动地拱卫结构的整体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体系中,而且也生活于一个统一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体系中。 当代西部的学术事业,面向多元、内容驳杂,既涉及全国学界探究的一般话题,更涉及西部学人对西部问题的专门研究,而且后一研究本身直接涉及西部学人以结构要素之身份,对全国性问题的参与。这应是关注西部学术的重要锚点。其中在法学领域,对西部法律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特别令人向往和期待的关键课题。因为就历史言,西部尽管曾长期是统一国家领土的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也曾不断存在地方自治、甚至分裂割据的局面。自古以来,西部是各族群成员杂居之所,文化多元明显,规范交往独特,法律遗存丰富。就现实言,不但西部地区历史遗存的特征仍然存在,而且更兼之一方面,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明显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这种历史遗存;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治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赋予西部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这自然也会在那里导生新的、进化了的社会规范、交往方式和秩序理念。 谈到进化,我们知道:尽管近、现代以来,人类不断地被某种进化的理念所撼动、所裹挟、所牵引,但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任何进化,都只是我们历史和经验的一部分,是文明进化中历史和经验的当代表达。我们不可能因为进化而抛弃经验、逃脱历史。无论社会如何进化,如何变革,我们仍处在悠远的历史中,仍处于既有的经验世界中。这正如汤因比所言: “未来在真正降临之前一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我们只有观察过去才能找到未来的智慧之光。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经验是历史的别名……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使我们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和决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总要未雨绸缪。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地控制、塑造它,以便使之符合自己的期望。这种试图控制、塑造未来的自觉努力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它是令我们有别于共同居住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 这一历史观,清楚地表明人类进化中文化的规范性和逻辑制约性。今日之我尽管并非昨日之我,但也距昨日之我不遥远。昨日之我的文化密码一定会在今日之我中存留并持续作用、代代相传。所以,一切旨在刻意革除既有传统的努力,其结果不但不会革除传统,反而会被传统所革除。因为种种革除传统的努力,一方面,都把其用力方向置于自身的理念逻辑中,另一方面,却把历史经验的逻辑置于其理念逻辑的对立面,这必然会造成某种“理性的狂妄”,并因此戕害人类文明的进化。对此,林毓生曾剀切地指出: “我们批评某一个价值,必须根据另外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能够由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只能在文化演变过程之中发挥正面的效果,而不能脱离文化用本身的力量创新一切的价值。假若一个人认为他的‘理性’比所有的人都高、都多,所以他要用他的‘理性’创造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这个人将是毁灭文明的暴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