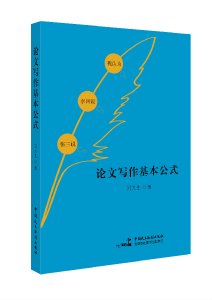|
字面解释是指对法律所做的忠于法律文字含义的解释;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时,对法律条文所做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限制解释是指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较之立法意图明显失之过宽时,对法律条文所做的窄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332页。 狭义解释,又称严格解释,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对法律的解释(与字面解释的不同在于:其不仅忠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而且主要是忠于被解释对象的立法意图);广义解释是指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文字含义,对法律的比较自由的解释(甚至可以改变立法原意)。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的文字,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论理解释,就是按照立法精神,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参见李希慧:《刑法探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转引刘浩:《刑法解释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都是为特定的大前提的真实含义提供理由的解释方法,参见[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51-52页。 转引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7页。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刑法解释理由与解释技巧的提出,使得原本就无力而含糊的刑法解释方法变得更加欠缺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解释理由很容易与刑法解释中的法律论证相混淆,而解释技巧实际上是刑法解释方法论中的应有之义。参见刘浩:《刑法解释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文理解释坚持规范至上和侧重于罪刑法定,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侧重于罪刑均衡,体系解释侧重于刑法解释的科学性与全局性,参见刘浩:《刑法解释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1、73页。 我国刑法学者认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大解释,实际上是类推解释;在扩大解释内部,需要进一步区分合理的扩大解释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我国法理学者则认为,按照解释是否符合词义推论规则,可分为词义内的类比解释和续造性的类比论证,参见雷磊:《类比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7、301页。 转引雷磊:《类比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293-296页。 转引自吴丙新:“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参见赵秉志:“罪刑法定原则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参见刘浩:《刑法解释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161、162、173页。 参见张明楷:“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21日。 台湾学者也作了类似的概述,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用语文义可能范围为标准;(2)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标准;(3)定型本质的解释观念;(4)以有疑时有利于被告人之考量原则为标准;(5)基于调和处罚要求与人权保障的观念确立的标准。参见黄朝义:“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之解释”,载林山田等:《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一)》,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7-147页。 参见陈志军:“论刑法扩张解释的根据与限度”,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参见雍琦:《审判逻辑导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参见解兴权:《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参见余继田:《实质法律推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1页。有学者将法官办案的推理过程分别界定为“事实推理”(即发现事实真相的推论,旨在确认证据并基于证据确认案件事实)、“法律推理”(即确认法律的推论,是探寻法律真实意思、平衡法律冲突、填补法律漏洞的推理,旨在发现、重构、填补与创制法律)、“判决推理”(即将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的结果为前提和根据得出判决结论的推理)。参见王洪:《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显然,此种“三分法”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法,不能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确认与法律规范确定之间的“往返流转”过程,难以解决解释学循环的问题。 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519页。 参见[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页。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3页。 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