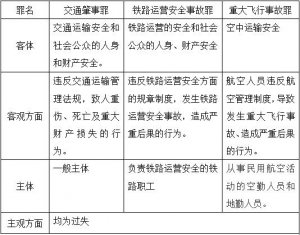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多元的,很多东西有着自身的限度。在以前,各种科目,人文,科学,艺术,美学,伦理,逻辑,发展低落的时候,宗教的边界就特别宽广了。后来,慢慢的宗教下面的学科,逐渐独立,想着分家。宗教有自身的限度,只不过,其它人文学科不发达,“寄生”在宗教里,这些学科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领地,自然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于,宗教慢慢的有自身的边界。大家都觉得这些学科,特别是“科学”,在近三百年中,一马当先,独领风骚,恍然间,科学的光芒,超过宗教了吧!这里,不妨给“科学”算一卦,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宗教,最多也就是与宗教旗鼓相当。谢学友,不是长“宗教”的志气,灭“科学”的威风。 为什么啊,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大学里边,同样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纠葛。一个是“人文”,文史哲艺术,再一个是“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漫漫文明史,“科学”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这是晚近的事情,但,由于应用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翱翔于天地之间,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文化的“中心”学科,“技术至上”,既改变了现实社会,也改变了大学自身。 “人文学科”,由于自身欠缺功利性,以至于沦落到“边缘”,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但,“人文学科”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人文学科”属于人类文明的“慢生活”,不必与“技术科学”争一日之短长,也不必“摆老资格”——想当年,“科学”还是个少年,“技术”还是“玩泥巴”的顽童,“人文”就已经有着丰富的积淀。 支撑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这些“人文学科”的,实际上,是背后的那个“意义”,那个“意义”,某种程度上与“神”、“神圣性”相联系的,就是怎么样,关切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缠”着人们,人之所以成人啊,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们到底怎么来的。人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敬畏,有一个省思,省思到一定程度上,从文明史来“追”,“追”到最后,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往往要“追”到宗教,或者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佛教、犹太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但是,追溯中国文明史,历史上曾经有多多种宗教的身影和踪迹,不过,中国文明的源头,有着鲜明的文明性格,那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周孔教化”,周孔教化,这是一种伦理,以至于任继愈先生,要把周孔教化,当做一种宗教——儒教。 这个世界,有“有用之用”,有“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纠结缠绕,建构了鲜活而丰富的文明史。“有用之用”往往追到“无用之用”,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用之用”主导着“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才是那个真正的“诺亚方舟”。 遗憾地看到,很多文明被灌注了一种“一神教”,总想把复杂多样的世界,弄得整齐划一,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现在讲什么,动物啊,植物啊,微生物啊,那种多样性。其实,人文与此相匹配,依然具有多样性。实际上,人类文明,也是一种多样性啊。既然具有多样性,所以说不要轻易的,一分为二,而应该一分为三。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总以为,这个东西起来啦,那个东西就应该趴下。实际上,我们建构了,或者被建构了“非黑即白”的一种观念。哎,脑海之内,很多东西,都在“交战”,“打架”,表现在课堂,或者宿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省自我,“课堂”一度成为“教堂”,自己也成为某种教义的“布道士”。所以,马克斯·韦伯说,保持一种价值中立,大有道理。 在研究或者教学中,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加以“斗争哲学”,驱之不散,现实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红卫兵”,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为什么老“打架”?略微思量,很多东西,其实“打架”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但是,遇到对立面,不仅生真气,还要批倒批臭。文革结束四十一年了,看待问题,没有提升到“一分为三”,还停留在“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是我对,就是你对,不是我错,就是你错。你我之间互相争论,只能有两种状态,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类人孩”或者“巨婴国”,大体是不错的。 实际上,在两种情形之外,还可能有这种情形:你也不对,我也不对,或者说,你也对,我也对。为什么,都是盲人摸象。你说“大蒲扇”,我说“大柱子”,“大蒲扇”或者“大柱子”,谁对谁不对?若说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都是大象身子的一部分,是这种情况呗?若说不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没有摸到大象的全部。 为什么“一分为三”,为什么中国古人要“一分为三”呢?怎么不“一分为二”呢?叩其两端而执其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太有道理哦。体会“一分为三”,执行“一分为三”,我的主张,反对我的主张,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极高明而道中庸。两种对立的主张之间,实际上怎么样啊,中间还有一部分。也许中间那部分颜色比较弱,以至于看不到。看不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的,人又不是全知全能。 中间那部分看不到以后呢,就以为在那顶着牛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包括宗教与科学的因缘,顺便说一句,谢学友对科学史,也比较感兴趣,这是科学史一个永久的话题。“传教士”为什么发展了“科学”,宗教裁判所判处布鲁诺火刑,烧死的是布鲁诺,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代科学的星星之火,成为照耀整个世界的燎原之势。这就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因缘。 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妙不可言。回眸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现中国“宗教”与“科学”,如影随形。中国的宗教与科学,依然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永久话题。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科学的滥觞,与墨子有着莫大的渊源。墨子是墨学的开创者,这个学派,其实,还是一个准宗教集团,墨子主张“非战”,“非攻”,希望让世界充满爱。难怪有人非要说墨子“祖籍”印度呢?墨子是否和释迦牟尼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