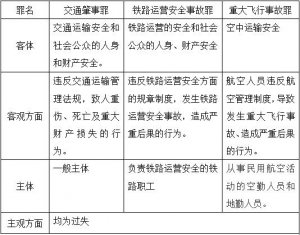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1条注意到了网络安全和法律利益的关系,但其表述本身却容易引起适用范围的歧义。该条规定:“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可见,表述上将作为直接适用对象的网络安全与作为适用而取得的法律效果一体化并列,如此不免模糊了法律适用范围的限定性。 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洲现行私法研究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参见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以下,第七章第三节。 《网络安全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支持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 参见百度百科“法律保留原则”,?url=PHRUuuDwtycs6ijpW1nDW8XuNRFWZY2t8fCNyjE9T4ZAteMlJ2RCF56gqRDxMfQL9NmCUzAxfXEgdyTYXL3NjyffAdXVtecBerxDnYkwtaq59dZPm12_kg0z0xlb8Tr_qvZUjHlzbWO1jS3So7wXxq。 参见百度百科“行政比例原则”,?url=YcfHM58NmNbFEaiarEUrP4ydbaxeln-I9b1YD3x_PXBTR_0n2CIf0J4OkS34BOkg8kqNnEl7Tv0U1jgzdeY6c1zZ0EhDp3CCLtmrktSr2gCX5LmlgkVHKO2FvdgHTzaz。 参见劳伦斯·雷席格《网络自由与法律》,刘静怡译,台湾商周出版2002年版,第99页以下,“第四章控制的结构”。劳伦斯·雷席格深刻阐述了网络的基础是代码的思想,由此提出网络管制仅仅依靠政府的直接管制方式是不可能有效的,需要政府和可以操纵网空间特殊架构即代码的网络机构或企业进行合作,应当透过控制代码而进行管制,或者根据代码不同而进行不同的管制区分(如公开代码和封闭代码就政府行为作用影响就差别很大)。 参见Brendan Sasso, "After defeat of Senatecybersecurity bill, Obama weighs executive-order option" (August 4, 2012), The Hill, Accessed August 20, 2012. 参见Stewart A. Baker and Paul R. Hurst, The Limits of Trust::Cryptography, Governments,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 edition (August 1, 1998), p.15-22. 参见美国《网络安全法》第一编即为“网络信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