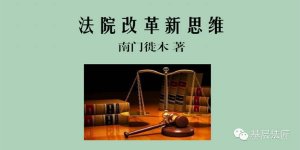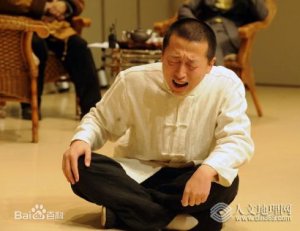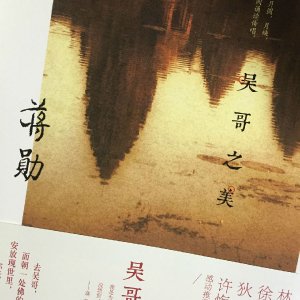| 黔东南历史上民间法推动婚俗改革的实践 ---以侗族苗族碑文资料为基础 徐 晓 光 [摘要] 历史上黔东南侗族苗族地区“姑舅表婚”现象最为突出。从该地区大量存留的婚俗改革碑文看,地方政府和民间精英对“姑舅转亲”以及彩礼的改革倾注很多精力,国家法和民间法在这个问题上达到高度的一致。但传统的民间习俗是一种顽固的势力,改革并不容易或过一段时间会死灰复燃,所以这项改革一直持续到近现代。 [关键词]黔东南;侗族苗族;婚俗改革;国家法;民间法 [作者简介]徐晓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 贵阳550001)。法律不是单一的现象,它为社会形式的多元化所构建。婚俗是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在一些民族中某种婚俗在一定历史时期曾经几乎主宰了婚姻。如“ 姑舅表婚”习俗曾盛行于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1],而在湘黔边民族地区特别盛行,黔东南侗族苗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历史上民间法顺应社会发展的形势,对“姑舅转亲”陋习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改革。我们拟应根据黔东南地区的碑刻资料及相关口传资料,探讨以改革“姑舅转亲”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法变迁及与国家法的互动问题。 一、 从婚姻改革碑看“姑舅转亲”习俗侗族的“款”是一定区域内联合制定的习惯法,“款规”是其具体内容,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款规用口头形式表达,款规就“姑舅转亲”说到:“你是我姑表亲表,娶你不要有怨言,娶你没有身价钱。我们不要,别人也不能娶到你,我们剩下,你不能成别人妻。表哥断腿断脚你要嫁,表弟眼瞎耳聋你要依。天上,你用竹竿来戳;下地,我们用锄头来挖”[2] 历史上侗族地区盛行“姑舅转亲”婚俗。康熙六十一年(1722)八月思州知府蒋深撰成的《思州府志》云:“婚嫁不凭媒约,姑家之女,必子舅氏之男,名曰‘酬婚’。”[1]清代民国“姑舅转亲”在侗族地区也比较常见。如果违反这种婚姻习惯,往往就在姑家和舅家之间产生矛盾,矛盾主要表现有:1、姑女和舅子年龄差距太大,导致不愿结婚或婚姻不和。男女的年龄差距大,仍要强行婚配。2、姑家本无女,舅家“要头钱”,导致财产债务纠纷。3、姑家许嫁他人,舅家强要钱,导致财产债务纠纷。4、姑家女不愿意,而私奔。5、姑表结亲的“悔婚”和“赖婚”纠纷。所谓“悔婚”是指由于“姑女”不满意舅家,在迎娶前私奔、逃脱、自杀等方式拒绝“估娶”。所谓“赖婚”,是指姑表结亲发生纠纷后,诉至官府,没有婚书、媒人等法定证据,无法认定婚姻关系的情形。以上这些矛盾便出现了拐骗妇女等控诉官司及暴力拆毁房屋等重大冲突,甚至出现了“屡次上城具控,总是舅公估要姑女之事”的累讼。如清道光年间紧邻黔东南的湖南靖州三锹中锹的万财寨一个叫潘好山的姑娘被迫嫁到背地寨舅父家为媳,因丈夫是傻子,潘非常怨恨,放毒药药死丈夫,尸首三年未埋,由此引起一场官司。道光十九年(1839)死者的舅父到靖州三岩桥陵溪司告状,此案惊动锹里24寨寨头,他们将此案呈禀于靖州府。州官宋晏春、陵溪司郭某审案后批示:“婚姻听人择配,岂容欺压霸占,倘有阻于陋习霸婚苟索情事,许于追究,毋容率情,示禁”。此后,中锹9寨头人吴光律等17人在背岩回“合款”,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立石碑载“禁款”4条:1、婚姻听人择配,不许舅霸姑婚,如违示禁,公同禀究;2、不许舅氏苟索钱银,如违示禁,公同禀究;3、聘金财礼,只许一十六两,如违公罚;4、过门财礼,议定银八两,如违公罚。同时规定:“以上款条正赖各遵州主示禁,如违者,被害之家备银三两三钱,通众齐集,公议禀究”。之后,锹里24寨头人为禁止“舅霸姑婚”分三款进行了讨论商议,上锹九寨头人龙彩鹤、龙昌培、潘远炽、谢永泽、张子秀、吴应久等68人在牛筋岭合款,并立有碑文(道光二十二年,1842),内容为:“尝思一阴一阳之谓道,故道之在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媒妁有言,配合宜均,此古帝国盛治祀重夫妇之伦,以端天下之俗然也。……道光十九年禀州司二主,均蒙尝示……不许舅霸姑婚,索诈土民等,如有不遵行碑记,各寨传知,同攻其人,以教风化”。下锹6寨头人吴昌鸾、潘高文、潘仕向、杨秀应、杨光华等十三人在大梁坡合款,合款议定:不许舅霸姑婚,并刻碑垂记,以示永远遵行。[3] 国家法律禁止“姑舅两姨姊妹为婚”,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根据翰林侍诏朱善的建议,已经松弛该禁止律条,但没有进入《大明律》。清代国家调整婚姻的法律中规定禁止“姑舅转亲”。《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2]但在所附条例中却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 这似乎很矛盾,乾隆五十三年修并过一次[3],对此清代地方官吏也应该是清楚的。从北洞九寨地区“彦洞、瑶白定俗碑”的碑文来看,其主要内容都是锦屏的地方政府的“晓谕”公文,就表明锦屏的地方官员了解国家法律及其解释的情况,于是官府就此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请看“彦洞、瑶白定俗”碑:定俗垂后……惟有我彦、瑶二寨,姑抚有女,非有行媒,舅公估要;女有不欣意,舅公要银数十余金,富者售尽家业以得为室,贫者绝灭香烟不得为家。…康熙在位时用毛银,舅礼要银九两,申扣纹银贰两八钱以下。至嘉庆之间用色银,舅仪要银十二两,扣归纹银六两。同治之岁,苗匪作叛,父离子散,难以度日,鞠育有女,不用冰人,至舍饭一餐就成缔偶。迨光绪以来得升平之世,普用宝银…舅仪勒要纹银数十余金。你贫我富,屡次上城具控,总是舅公估要姑女之事。府主俞爱民如子,睹见斯恶习,要首次(事)上城当堂领示禁改,则可剔斯舅仪,方得仁里勒石垂后,永定乡风,遗存千古。是为序。钦加盐运使衔补用道转授黎平府正堂铿鲁额巴图鲁加三级记录十次俞(渭)为出示晓谕,永远遵行示。案据瑶白寨总甲滚发保、滚天凤、滚必录、范永昌等禀称:“…惟有总甲等二寨,养女出室,舅公要郎家礼银二十余金,出室受穷,舅公反富。倘若郎家穷困并无积蓄,势必告贷;告贷不成,势必售产,穷者益穷,富者益富,祖遗薄产尽归于人。此等之规□□剔出。今欲依古从俭,公议上户出银五两,中户出银肆两,下户出银叁两,不过作订亲之仪,并不以(与)买卖相似……惟有总甲二寨之风,……或大十岁、二十余岁不等。舅公估要女转娘头,若女有不喜之心,不由媒说,随同后生私走,或去日久未回,舅爷要女匹配,或搕数十金,或以拐案呈控,或将屋宇拆毁。此等地方恶俗,总甲等难以挽回,公同邀恳赏准出示严禁。嗣后愿亲作亲,免致舅公需索,依示遵行”等情到府。据此,…查舅公礼虽系该寨遗风,然亦何得需此多金,自应酌定数目,所标分别下、中、上等户各色,定以三至五两之例属,酌中办理,自可照准。至于舅家之子必娶姑家之女,谓之转娘头,此事原干禁例,现虽听从民便,然需年岁相当,两相情愿方可办理;为此…自示之后,仰即遵照此次批示,凡有舅公礼者,必须分别上、中、下三等,祗(只)准自三两至五两止,不得再行勒索多金;至于姑舅开亲,现虽在所不禁,然亦年岁相当,两家愿意方准婚配,不得再行仍前估娶。…倘有不遵仍前勒索估娶,或经查处,或被告发,定行提案严究不贷。其各凛毋遵违。特示。右谕通知。(牌长十一人,除一名外,均为滚姓,姓名从略;另有彦洞同事总甲四人,牌长三人,二名刊刻人,姓名从略。笔者)光绪十肆年十二月初五日实贴瑶白晓谕[4] 此碑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初五日,碑文主要针对彦洞、瑶白二寨的婚姻陋习颁行。“彦洞、瑶白定俗碑”碑文则显示一定的包容性,官方对于民间婚俗陋习原则上是禁止的,体现了官府对户婚等普通民事案件的管辖,也表现出“因俗制宜”的特征。尽管已至光绪年间,当地仍然以上述“姑抚有女,非有行媒,舅公估要;女有不欣意,舅公要银数十余金,富者售尽家业以得为室;贫者绝灭香烟不得为家”为断案标准;舅仪勒要纹银数十余金,使得“你贫我富,屡次上城具控”,因户婚而结讼,与狱讼清结的追求背道而驰,自然为地方官所不愿,黎平府正堂出示严禁,加以剔除,但并没有对“舅爷钱”等习俗严行禁止,只是认为“舅爷钱”虽系该寨遗风,但需要这么厚的礼金甚属不妥,于是晓谕“自应酌定数目,所标分别下、中、上等户各色,定以三至五两之数例属,酌中办理,自可照准”。至于“转娘头”,即舅家之子必娶姑家之女的习俗,知府俞渭认为:“此事原干禁例,现虽听从民便,然亦需年岁相当,两相情愿方可办理;”若不论年岁必须估娶,势必滋生事端。此等风俗,均应极力挽回。在地方甲等的禀请之下,俞渭即如禀出示晓谕,示抑该寨人等知悉:“自示之后,仰即遵照此次批示,凡有所谓舅公礼者,必须分别上、中、下三等,只准自三两起至五两止,不得再行勒索多金;至于姑舅开亲,现虽在所不禁,然亦须年岁相当,两家愿意方准婚配,不得再行仍前估娶。此系为地方风俗起见,该民等务各遵照办理,以挽颓风而免滋事。倘有不遵,仍前勒索估娶,或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提案严究不贷。”对彦洞、瑶白二寨的婚俗,知府俞渭在出示晓谕之时,明显给予较大的宽容,“舅爷钱”按照家庭状况分为三等不得再行多索。至于姑舅开亲,晓谕的内容与《大清律例》相一致。但在民间,姑舅、两姨姊妹为婚习俗禁而不止。故而晓谕“现虽在所不禁,然亦须年岁相当,两家愿意方准婚配”。强调双方的年龄与意愿,亦即禁止以“转娘头”为名强行嫁娶的行为。又说:“至于舅家之子必娶姑家之女,谓之转娘头。此事原干禁例,现虽听从民便,然亦需年岁相当,两相情愿方可办理。”但从所辖村落遗存的碑文分析,即使官府大力革除,地方头人倡首禁止,但在许多的村落“舅爷钱”依然存在,且历久不除。 二、从婚姻改革碑文看结婚彩礼“彦洞碑序”开宗明义:“盖闻人伦之始,夫妇为先,王道之源,婚姻为重。”[4]据《开泰县志》载:锦屏、黎平等地“婚礼、问名、纳采、亲迎皆与中土同,其尤近古者,盛时结姻后或男家力歉女家即量力自备衣物,以完儿女之债,两家皆乏,至亲厚友助成之”[5]。这些只是正面的提倡,但由于一方想在缔结婚姻中获得利益和相互之间的攀比,在侗族地区男女结婚,彩礼越来越高,子女结婚弄得家里一贫如洗,也生出了不少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每到这时款组织或村寨就会制订规约,限制彩礼的数额。主要规定在男方聘礼、女方嫁妆、姑舅之间的彩礼、嫁娶迎送之间相赠的礼物等方面要降低标准。如清道光十一年(1885),婆洞、留洞、魁洞、寨楼、寨母、寨蒙、边沙、寨伍、八教、者晃、西洋店等寨寨老率重700余户聚集边沙合款,商议婚俗改革,形成著名的“八议”款规,并将该款规刻碑多块,立于各寨,俗称“八议碑”,摘录如下:因时制宜……而姑表分财之规,不无陋弊。或藉此而赖婚枉利,或因此而悬搁终身,以致内怨外旷,覆宗绝嗣,因以构讼经官,倾家荡产,呜乎殆哉,祸甚烈也!…于是一带乡邻,合同计议,…将见俗兴化美,益已利人。…谨将规例,特勒贞珉。 -议行亲之家,财礼六两,女家全受。舅父只收酒肉,水礼财礼不妄受分毫; -议送亲礼物,只许糍粑一槽,其酒肉多寡听其自便; -议送陪亲婆礼,只许酒肉,不得又送糍粑; -议嫁女之家,妆奁多寡,随便其有,手中概行禁止; -议纳彩之后,禁止节礼,日后行亲节礼,只许馈送一年; -议喜爱礼物,禁送卷联祭轴; 一议姑表结亲,不得混赖,必要庚书媒帖为凭,其财礼仍照六两; -议生男育女,只许嫡亲送礼,不许搭配。 以上诸条,凡合款之家,共计七百余户。若有故犯,俱在各甲长指名报众,倘或隐瞒,公罚甲长儆众。 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寨四十八人同立,姓名从略)[5]从整个碑文看,核心内容是限制“姑舅转亲”的彩礼。碑文认为这一婚俗实属陋习,本应永远革除,但因相沿已久,无法一时根除。碑文既限制“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又限制“藉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表明至道光年间在锦屏一带在地方政府政策的推动下,[6]民间款组织对婚俗陋习已经很反感,并在很大的地域组织范围内有改革行动。 “庆云乡例碑”第二款规定:“二比联姻,接承宗祀,皆以媒妁为凭,男不许依势逼婚,女不许登门坐虿。倘二比不偕,聪从改嫁,照俗碑记,毋许过索多金,未过门者五钱五分;过门者三两五钱。男女嫌怨,照例均皆如是。室妻不守妇道,所犯之条,休逐钱贰拾两,住及三年,无工力除此之外,洒扫工资每年一两,衣服从今革除。”[6]侗族过去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女子结婚后要先在娘家住上几年才到夫家与丈夫住在一起。如黎平、从江交界侗族村寨订立的《十二条款约》规定:“女大当嫁,男大当婚,女满十七始嫁,男到十八才婚。女嫁先问表哥,不娶再嫁别人。父母有命才订婚,订婚三年才过门。女退婚赔彩礼,男不娶不取分。”[7]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黎平茅贡乡寨母“碑记条约”说:婚娶乃人伦之始,风化所系理宜百年不移,岂容朝成夕改,但此習俗相沿已久,仍当从俗从宜,或无唆迫婚姻女心自不愿者,遵照古制。姑表财礼色银八两,非姑表四两,若查知唆迫之家使人妻离,构成仇隙,凭证拦阻就中。别贫富三等:上户姑表照现财礼加一十六两,中户八两,非姑表上户照加十二两,中户八两,自中户以下多寡不在条例。男放女财礼亦照此例,然此只许阻一二真实之家,不许思财多阻至。若改嫁别人,经过财礼花费、酒水照加四两,以补酒水礼费。设徒饮定亲媒酒,男女翻悔罚色艮(银)一两五钱,其媒酒谨遵旧制,无许更新。此俱系公议嫁娶定规违者公罚银三两二。[8] 《公纳禁条碑记》规定:(1)拐人姑表亲者,上等亲受财礼银十三两;中等亲受财礼银七两;下等亲受财礼银五两;如不遵;禁,额外重索者,将此项款缴入众。(2)上等亲男女嫁娶,男自愿娶,女自愿嫁,两造父母不依,男女私约拐带,上等娘家,准吃财礼银十一两;中等娘家,吃财礼银七两。[9]《高增款碑》规定:“议男女婚姻,男不愿女,女不愿男,出纹银八两八,钱一千七百五十文,禾十二把。” “于归完娶,是次生男育女,运命不和,爱新弃旧,改折等规定五十二千文”。[10]《乡规民约碑》关于彩礼方面的规定有:“一议求亲,不许相退,罚银八两八;一议姑表,勿论男女相退,罚银八两八;一议成亲,男女相退,罚银五十贰。”等等。[11] 三、 改革的推力与阻力 婚俗改革的目的是“为挽颓风”,“俗兴化美,益己利人”。方式有两种:一是地方头人在自己处于“无以挽回”的境况下,“鼎新连名具禀于黄堂,叠沛悬纶于天下,里捧天批而甚藉尼后以流传”,借助官府的“批示”,以实施自己的主张;二是地方头人共同商议,订立款约,利用地方力量以实现婚俗改革的目的。[11]康熙平江碑、乾隆四里塘碑、同治已得碑、光绪彦洞、瑶白碑属于前者;光绪启蒙碑和嘉庆四里塘碑则属于后者。地方官府为维护地方安靖,以示自己的政绩,不仅批示支持地方头人要求改革的婚俗请示,且自己也发出禁革的告示,可见清朝从康熙到光绪的200多年里地方官府和乡村绅士都致力于婚俗的改革。 1、社会精英的作用任何“立法”是制定一种适用于一定区域内所有人的规则,追求法普遍性和一般性,力求系统性、全面性和预见性。同时立法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它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其好坏无法从其本身得到答案,只有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才是好法。而在“民间立法”中社会上层的力量作用积极,而来自社会基层的力量的作用较为微弱,有时立法者不论是在自然的时间、空间,还是在人文的时间和空间上更接近于社会上层的力量,特别是以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为主体而形成以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姿态出现的社会上层的力量,就更容易受这种力量的影响,这时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成为了当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一种理想制度设计的蓝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更可能受民间“立法者”个人主观愿望、政治热情等因素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和良好的愿望的作用下,将引导社会的规则自觉或不自觉带进了“民间立法”之中。甚至“民间立法”倡导者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如清道光十一年(1885),边沙、寨伍、八教、者晃西洋店等寨头人率700余户聚集边沙合款,商议婚俗改革,形成著名的“八议”款规。“八议”碑的碑名就叫“因时制宜”,碑的“前言”痛陈“姑舅转亲”的恶果,认为:“姑表分财之规,不无陋弊。或藉此而赖婚枉利,或因此而悬搁终身,以致内怨外旷,覆宗绝嗣,因以构讼经官,倾家荡产,呜乎殆哉,祸甚烈也!……于是一带乡邻,合同计议,……将见俗兴化美,益已利人。……谨将规例,特勒贞珉”[12],倡导革除这种相沿已久的陋习。由于地方有识之士的倡议,地方官为维护地方安靖以显示政绩,不仅批示支持地方头人要求改革婚俗的请示,甚至自己也发出“禁革”的告示。福山认为:不论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它们自身都不足以产生出构成社会秩序的全都规则,在关键时刻它们都需要由等级制权威来进行必要补充。[13]在剑河小广环龙庵遗址上有一块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立的“永定风规碑”,记述以潘老乔为首,联合化敖、谢寨等侗族村寨的寨老王士元、彭宁绍、谢贵乔、杨德桂、文登朝等就“姑舅转亲”的陈规陋习具禀首告到府,经镇远府正堂大人批准,特立此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载:“嗣后男女婚娶照定例,须由两家情愿,请凭媒妁,发庚过聘。严禁舅家强娶滋事。如违重咎不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4]同治五年(1866),黎平知府徐达邦、光绪二年(1876)黎平知府原开第就曾出过“禁革”告示。从社会调查的情况看,当地苗族侗族群众对“姑舅表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为了“亲上加亲”、“肥水不落外人田”;有的说是为了“优生”(其实恰恰相反);有的说是因为知根知底,不会沾上“不干净”(“蛊”等)的人家,保持血缘“纯正”;有的说是“要回姑妈带去的钱财”,不至于财产外流。凡此种种,抑或兼而有之。但“要回姑妈带去的钱财”的成份大些,实质是财产权回归的问题。这就形成了苗族婚姻习惯法上的舅权。曾经盛行这样的规则:“姑妈的女儿须嫁给舅家的儿子。按古时成理,如不嫁给舅家须赔给舅家三百两银子;有可谅之情的减一半;再有特殊困难之情者可再减一半。”此后姑妈家的女儿,不经舅家表态不得任意出嫁。俗话说:“姑姑女,伸手取。”如果舅家不娶该女作儿媳方可允许出嫁,但须给舅家“还娘头”钱。这也是苗族婚姻中要给新娘母舅以较重的礼金的缘故。距雷山县永乐镇北1公里处的干南桥有一青石碑,系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两县联界的各保甲长及父老等集会议定的“榔规”,内容是确定苗族婚姻财礼金的“公约”。其碑文是: 万古不朽。 兹将丹、八两县联界邀集各甲长及父老等进行决议规定,财礼钱不得多取。所有婚嫁自由,不得强迫子女成婚,俏(稍)有违当众议决规定条例,多取及强迫者,均以碑章证明,否则天诛地灭,永不发达,仰望各界父老须知。此碑万古不朽,所议各条开例于后。 计开: 第一条:对于回娘头,先由媒人说定,或由双方子女愿意成婚者,乃能决定婚配,若不得双方子女同情者,而父母决无强迫阻滞及野蛮之行为。 第二条:准定财礼钱,富者,一百五十元八角(银元)。 第三条:准定财礼钱,贫者,一十二元八角。以上贫富财礼钱,须向嫁家取定收分。 第四条:准定娘头钱,一律七两二钱。依古法律,每扣小钱一千二百文,不许任意折扣。 第五条:施行本简章,呈请丹、八两届县府核准之日实行。[15]该碑的目的是改革苗族“还娘头”婚中强迫行为,提倡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由,改革婚嫁礼金标准,减轻娶亲男子的经济负担。这是两县联界邀集各甲长及父老等进行决议规定,说明苗族地区婚俗改革中有识之士的“首唱”作用。2、民间法律制度的调整在民间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伴产生,共同维系社会秩序,在进行制度创新时,非正式制度又作为先在的环境因素,对国家正式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时非正式规则在不同领域也在发挥着与国家法同等效能的作用,在国家法无法提供应有职能,即国家法短缺时,这些非正式规则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正式法律的“替代者”。国家法必须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稳定性以及原则性等特点,但到了乡土社会狭小空间反而显现出劣势。因为国家法为了统一性也就很难照顾到乡土社会事物的特殊性;要体现原则性它就不可能、也无必要涉及到乡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我国古代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基层司法资源配置差别比较大,造成国家法在一些乡土基层社会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供给不足,甚至是极度匮乏的情况。事实上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沟通与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和耦合,正是法律制度创新与变迁取得成功的关键。当国家制定法的禀赋与其作用下的民间法、习惯法相一致或大体一致时,后者就能成为前者的正确而积极的“解释者”,会加速前者的推进过程,从而扩充其效能。国家立法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调和意味着人们将借助非正式规则某种程度自觉遵守国家制定法,也意味着国家制定法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并以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所要求的制度模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从而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本降低到最低点,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清代的国家婚姻法在律条中是禁止“姑舅转亲”的,但在所附条例中却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从锦屏四里塘“恩垂万古”碑、“彦洞、瑶白定俗”碑的碑文来看,其主要内容都是锦屏的地方政府的“晓谕”公文,其中就说:“至于舅家之子必娶姑家之女,谓之转娘头。此事原干禁例,现虽听从民便,然亦需年岁相当,两相情愿方可办理。”,说明在“姑舅表婚”处理上,国家法、习惯法与民间婚姻习俗严重背离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也会采取妥协的立场[7]。[16]如康熙二十九年“平江恩德碑”说:“云贵总督部院范 巡府都察院 黎平军民府 良寨长官司督学龙 为禁革□民□□□□劫盗□变俗□□□□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奉协镇贵州黎平督学龙□□□元月二十日,提督贵州全省军民□府□批准,本协□□祥谕…一、求聘定亲,止许为凭,革除酒席会亲。……一、姑舅转亲,仍补外家礼银三両五钱,不得勒借。以上条□□□司寨不得□□□,本司以凭参宪两府请法重处。 特禁。”[17]该碑对全省居民婚姻聘礼、结婚宴席、姑舅转亲彩礼数量作了明确的规定。3、国家法、民间法互动拉德布鲁赫强调:“正是因为习俗自身把约束方式的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效力统一了起来,无论其是否只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所以习俗才比道德和法律更具有威力。”[18]“法律多元”的格局一直是黔东南民族地区法律文化的实质特征之一,在这种多元体中国家法是指由国家各级有权机构依法制定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而民间法则是指在法律多元文化背景下,存在于广大乡土社会中的与国家法不同的民间社会控制规范;而习俗则是村寨社会的人们祖祖辈辈相沿成习的惯行。由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使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法和民间惯行。历史上在侗族那些村寨中,纯粹以国家法建构的秩序没有出现,而是结合民间法和民间惯行形成的“混和型法”的法制秩序,即国家法、“款约法”、村寨法、民间惯行共同构成了村寨的规范体系。村寨法作为“地方性知识”,贴近村寨现实生活,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规范,在村寨发挥实际作用。对村民们来说,经验的、现实的、管用的民间法比国家法更有利于解决问题,他们更多地是选择民间法。但有的时候,国家法、村寨法与民间惯行也有突出的矛盾,比如在侗族一些地区人们普遍相信的“有蛊”迷信,近代以后国家法、村寨法一直持反对态度,并对残害所谓“蛊女”的不法行为进行制裁,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消除这一迷信的存在。“姑舅转亲”和“放蛊”的情况有些一样,作为一种惯行一直在黔东南侗族苗族地区盛行,但“姑舅转亲”的涉及面更大、影响更深,长期以来很多青年缔结婚姻都照此惯行行事,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历史上黔东南侗族地区文化相对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陈规陋习较多,偏远地方的侗族群众几乎完全不知国家法律为何物,他们长期遵守的习俗惯制,所以民间习俗的改革通过国家法律的提倡和政府的推动实现不了时,自然想到借助“民间立法”的形式来完成,但在一些更为落后的地方,国家法、民间法执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阻力很大,地方官府也只好采取肯定习俗、稍作限制的妥协做法。如前举雍正八年(1730)“平江恩德碑”,云贵总督部院、巡府都察院、黎平军民府、亮寨长官司督学联合发布的禁示,做出“姑舅转亲,仍补外家礼银三两五钱,不得勒借。”[19]即如果姑舅两家不结亲,姑女许嫁他人,就要给舅家三两五钱礼银,但是不能强迫写借据的规定。在民间“姑舅转亲”婚俗特别盛行的情况下,官府也清楚地知道通过一纸告示是难以改变,也就只好“因俗而治”了。 4、当今的婚俗改革目前,黔东南的婚俗改革还在民间悄然进行,还拿“姑舅表婚”来说,它作为长期形成的民间制度虽然整体上不存在了,但近亲结婚的情况还较多,这里肯定有一部分“姑舅表婚”,这和“放蛊”一样,是民间的“私密”,很难做充分的田野调查。但在黔东南民间,姑舅两家有子女结婚互送重礼的习俗还普遍存在。2009年3月、11月和2010年3月榕江县的八开南部地区加两苗寨、摆垭山地区和从江县的能秋一带先后按照传统的做法举行了“埋岩议榔”,三次“埋岩议榔”均是苗族自发的民俗改革活动,针对苗族地域社会面临的相同社会问题订立了“榔规”,内容涉及苗族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20]其中就有婚俗改革的内容,有的婚改条款还沿用了传统习惯法中罚3个100的做法来加以禁止。如“能秋榔规”第10条规定:舅家或姑家儿女结婚时,姑家不准牵牛给舅家,或舅家不准抬猪给姑家。违者均罚猪肉100斤、米酒100斤、大米100斤。由此看来,这是用一种传统的处罚方法改变婚姻旧俗,而且这种传统的处罚方法自身都在改变。黔东南侗族、苗族要沿用这种习俗主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和经济因素以及古老的规矩。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做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方式的“实用理性”。他们能够在其知识体系范围内,对力所能及积累的条件综合权衡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村民们在比较旧习俗与新习俗的时候,更可能会发现新习俗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好处(方便)或者说是减少更多害处(不便)。但是与此同时侗族人很好面子,又要恪守“古理”,小地域范围内亲属关系复杂,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村寨社会有很强的趋同性。在我们看来,从历史到今天侗族、苗族地区的婚俗改革是必要的、进步的,符合国家法律指明的方向和时代的进步趋向。从总体上说,以后在侗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法治观念增强,特别是在人口素质、身心健康和经济利益的前景展示下,广大侗族群众一定会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中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和调整。 [参考文献][1] (清)蒋深纂修:康熙《思州府志》卷1《区域志·风俗》(传抄本),第250页。[2]《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法律出版社,第53页。[3]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户律·婚姻·尊卑为婚》,法律出版社,第311页。[4] 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印刷:《锦屏碑文选辑》,1997年,第74~75页。[5]乾隆《开泰县志》卷二十《风俗》,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3页。[6]张子刚编辑整理:《从江石刻资料选编》,1990年,第53页。[7] 张子刚编撰:《从江石刻资料选编》(内部印刷),第54页。[8]笔者2008年在该村抄录[9] 张子刚编撰:《从江石刻资料选编》(内部印刷),第53页。[10]张子刚编撰:《从江石刻资料选编》(内部印刷),第54页。[11]徐晓光:《款约法——黔东南侗族习惯法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1]“姑舅表婚”习俗也曾盛行于太平洋上的仇布瑞安岛人、马达拉斯某地的雅利安人、美洲的印第安人等族群中。[2] 转引自吴浩:《从侗族婚俗看古越人婚姻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苗侗文坛》1988年创刊号。[3]案例和碑文内容转引自夏新华、王奇才:《论湖南靖州的“合款”-兼论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吴大华、徐晓光主编:《民族法学评论》,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61页。[4]“彦洞、瑶白定俗碑”内容参见 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印刷:《锦屏碑文选辑》,1997年,第74~75页。彦洞、瑶白均各立一块内容相同的碑,只是序与落款人名不同。二村现在均为侗族,但历史上瑶白曾有苗族居住,是明代从剑河迁来的一支,故而得名liul beeh瑶白,或miiul beeh苗白,现已被划为侗族。[5] “八议碑”相关内容参见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印刷:《锦屏碑文选辑》,1997年,第74~75页。[6]在此前乾隆五十六年(1791),锦屏文斗、尧里村等苗族村寨寨民姜廷干、李宗梅等禀请官府出示晓谕,黎平府向府属人等出示:“嗣后男女订婚,必由两家情愿,凭媒聘订,不得执行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及藉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于中阻扰滋事致于控告,严究不待。”地方村寨出首头人将此禁勒为碑,在锦屏县河口乡四里塘村,仍留存有碑一块,其碑文内容如下:“一、遵刊府主示:凡姑亲舅霸,舅□财礼,掯阻婚姻一切陋习,从今永远革除。如违示者,众甲送官治罪;一、众遵示禁勒:凡嫁娶聘金,贫富共订八两,娘家收受外,认舅家亲礼银八钱,如有违禁者,送官治罪。认亲礼在郎家,不干娘家事。一 、众遵示禁勒:凡女子出室,所有簪环首饰,郎家全受,娘家兄弟不得追回滋事。如违者,送官治罪。一、禁勒:凡问亲必欲请媒,有庚书斯为实据,若无庚书,即为赖婚。如违治罪……一 、禁勒:凡二婚礼,共议银两两两,公婆、叔伯不得掯勒、阻拦、逼迫生事。如违送官治罪……众勒:其有写外甥女礼银抵人银两者,大皆丢落,不许转追借主。如抗,送官治罪。计开各寨出首头人姓名于后,如有犯禁者,照开甲数均派帮补费用……“。皇清乾隆五十六年孟冬月 谷旦”。以上内容参见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印刷:《锦屏碑文选辑》,1997年,第68-69页。[7]碑文具体内容参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印刷:《锦屏碑文选辑》,1997年,第66~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