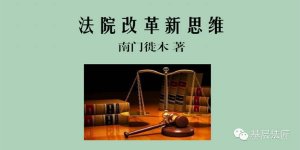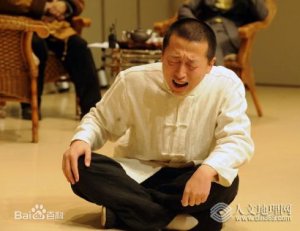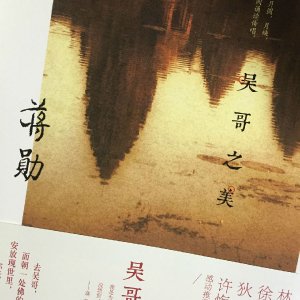|
�����������������������嶱��Ⱥ�ڶԡ��þ˱��顱��˵��硡�Ī��һ�ǡ��е�˵��Ϊ�ˡ����ϼ��ס�������ˮ������������е�˵��Ϊ�ˡ�����������ʵǡǡ�෴�����е�˵����Ϊ֪��֪�ף�����մ�ϡ����ɾ��������ơ��ȣ����˼ң�����ѪԵ�����������е�˵�ǡ�Ҫ�ع����ȥ��Ǯ�ơ��������ڲƲ��������������֣��ֻ�����֮������Ҫ�ع����ȥ��Ǯ�ơ��ijɷݴ�Щ��ʵ���DzƲ�Ȩ�ع�����⡣����γ����������ϰ�߷��ϵľ�Ȩ������ʢ�������Ĺ��������Ů������˼ҵĶ��ӡ�����ʱ�������粻���˼�������˼����������ӣ��п���֮��ļ�һ�룻������������֮���߿��ټ�һ�롣���˺����ҵ�Ů���������˼ұ�̬����������ޡ���˵:���ù�Ů������ȡ��������˼Ҳ�Ȣ��Ů����ϱ�����������ޣ�������˼ҡ�����ͷ��Ǯ����Ҳ�����������Ҫ������ĸ���Խ��ص�����Ե�ʡ� ����ɽ��������1�������ĸ�������һ��ʯ����ϵԭ����������ɽ������կ����կ����������ĸ����׳������ϵȼ����鶨�ġ��ƹ桱��������ȷ��������������ġ���Լ�����䱮���ǣ� ��Ų��ࡣ �Ƚ����������������������׳������ϵȽ��о���涨������Ǯ���ö�ȡ�����л�����ɣ�����ǿ����Ů�ɻ飬�Σ��ԣ���Υ��������涨��������ȡ��ǿ���ߣ����Ա���֤�����������������������������縸����֪���˱���Ų��࣬������������ں� �ƿ�: ��һ�������ڻ���ͷ������ý��˵��������˫����ŮԸ��ɻ��ߣ����ܾ������䣬������˫����Ůͬ���ߣ�����ĸ����ǿ�����ͼ�Ұ��֮��Ϊ�� �ڶ�����������Ǯ�����ߣ�һ����ʮԪ�˽ǣ���Ԫ���� ��������������Ǯ��ƶ�ߣ�һʮ��Ԫ�˽ǡ�����ƶ������Ǯ�������ȡ���շ֡� ������������ͷǮ��һ��������Ǯ�����ŷ��ɣ�ÿ��СǮһǧ�����ģ����������ۿۡ� ��������ʩ�б����£����뵤���������ظ���֮��ʵ�С�[15] �ñ���Ŀ���Ǹĸ����塰����ͷ������ǿ����Ϊ���ᳫһ���̶��ϵĻ������ɣ��ĸ�������������Ȣ�����ӵľ��ø������������������������׳������ϵȽ��о���涨��˵������������ĸ�����ʶ֮ʿ�ġ��׳������á� 2����䷨���ƶȵĵ��� ��������ʽ�ƶ�����ʽ�ƶ�����������ͬάϵ��������ڽ����ƶȴ���ʱ������ʽ�ƶ�����Ϊ���ڵĻ������أ��Թ�����ʽ�ƶȲ�����Ҫ��Ӱ�졣��ʱ����ʽ�����ڲ�ͬ����Ҳ�ڷ���������ҷ�ͬ��Ч�ܵ����ã��ڹ��ҷ����ṩӦ��ְ�ܣ������ҷ���ȱʱ����Щ����ʽ����ܴ�̶��ϳ�Ϊ����ʽ���ɵġ�����ߡ��� ���ҷ���������ձ��ԡ�ͳһ�ԡ��ȶ����Լ�ԭ���Ե��ص㣬���������������С�ռ䷴�����ֳ����ơ���Ϊ���ҷ�Ϊ��ͳһ��Ҳ�ͺ����չ˵������������������ԣ�Ҫ����ԭ�������Ͳ����ܡ�Ҳ�ޱ�Ҫ�漰�������������ķ������档�����ҹ��Ŵ�����������Ρ����á�����Ļ���չ��ƽ�⣬���ػ���˾����Դ���ò��Ƚϴ���ɹ��ҷ���һЩ���������������й����д����Ų��ٹ������㣬�����Ǽ����ѷ����������ʵ����ʽ�����ƶ������ʽ�ƶȵĹ�ͨ�������Լ��ڴ˻������γɵ����Ի�������ϣ����Ƿ����ƶȴ������Ǩȡ�óɹ��Ĺؼ����������ƶ������������������µ���䷨��ϰ�߷���һ�»����һ��ʱ�����߾��ܳ�Ϊǰ�ߵ���ȷ�������ġ������ߡ��������ǰ�ߵ��ƽ����̣��Ӷ�������Ч�ܡ��������������ʽ����֮��ĵ�����ζ�����ǽ���������ʽ����ij�̶ֳ��Ծ����ع����ƶ�����Ҳ��ζ�Ź����ƶ������������ǵ��ճ���������Ϊ�У������������ֵļ�ֵ����Ҫ����ƶ�ģʽ�ı����ǵ���Ϊ����Ӷ�ʹ�����ƶȵ�ʵʩ�ɱ����͵���͵㣬ʵ��������������Ĺ��һ��������������ǽ�ֹ���þ�ת�ס��ģ���������������ȴ�涨����þ��������Ϊ���ߣ�������㡱���ӽ�����������������š��������嶴�������ס����ı�������������Ҫ���ݶ��ǽ����ĵط������ġ����͡����ģ����о�˵�������ھ˼�֮�ӱ�Ȣ�ü�֮Ů��ν֮ת��ͷ������ԭ�ɽ���������������㣬Ȼ���������൱��������Ը���ɰ���������˵���ڡ��þ˱��顱�����ϣ����ҷ���ϰ�߷���������ϰ�����ر��������£��ط���ԱҲ���ȡ��Э��������[16]�翵����ʮ���ꡰƽ�����±���˵�����ƹ��ܶ���Ժ�� Ѳ������Ժ ��ƽ���� ��կ����˾��ѧ�� Ϊ���������������ٵ������ס�������������ʮ�������³����գ���Э�������ƽ��ѧ��������Ԫ�¶�ʮ�գ��ᶽ����ȫʡ���������������Э�������͡�һ����Ƹ���ף�ֹ��Ϊƾ�������ϯ���ס�����һ���þ�ת�ף��Բ�����������I��Ǯ�������ս衣������������˾կ���á���������˾��ƾ���������뷨�ش��� �ؽ�����[17]�ñ���ȫʡ�������Ƹ�����ϯ���þ�ת�ײ�������������ȷ�Ĺ涨�� 3�����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