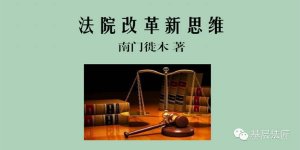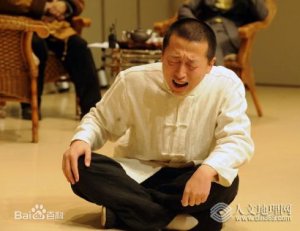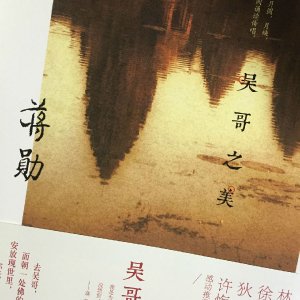|
从整个碑文看,核心内容是限制“姑舅转亲”的彩礼。碑文认为这一婚俗实属陋习,本应永远革除,但因相沿已久,无法一时根除。碑文既限制“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又限制“藉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表明至道光年间在锦屏一带在地方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民间款组织对婚俗陋习已经很反感,并在很大的地域组织范围内有改革行动。 “庆云乡例碑”第二款规定:“二比联姻,接承宗祀,皆以媒妁为凭,男不许依势逼婚,女不许登门坐虿。倘二比不偕,聪从改嫁,照俗碑记,毋许过索多金,未过门者五钱五分;过门者三两五钱。男女嫌怨,照例均皆如是。室妻不守妇道,所犯之条,休逐钱贰拾两,住及三年,无工力除此之外,洒扫工资每年一两,衣服从今革除。”[6]侗族过去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女子结婚后要先在娘家住上几年才到夫家与丈夫住在一起。如黎平、从江交界侗族村寨订立的《十二条款约》规定:“女大当嫁,男大当婚,女满十七始嫁,男到十八才婚。女嫁先问表哥,不娶再嫁别人。父母有命才订婚,订婚三年才过门。女退婚赔彩礼,男不娶不取分。”[7]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黎平茅贡乡寨母“碑记条约”说: 婚娶乃人伦之始,风化所系理宜百年不移,岂容朝成夕改,但此習俗相沿已久,仍当从俗从宜,或无唆迫婚姻女心自不愿者,遵照古制。姑表财礼色银八两,非姑表四两,若查知唆迫之家使人妻离,构成仇隙,凭证拦阻就中。别贫富三等:上户姑表照现财礼加一十六两,中户八两,非姑表上户照加十二两,中户八两,自中户以下多寡不在条例。男放女财礼亦照此例,然此只许阻一二真实之家,不许思财多阻至。若改嫁别人,经过财礼花费、酒水照加四两,以补酒水礼费。设徒饮定亲媒酒,男女翻悔罚色艮(银)一两五钱,其媒酒谨遵旧制,无许更新。此俱系公议嫁娶定规违者公罚银三两二。[8] 《公纳禁条碑记》规定:(1)拐人姑表亲者,上等亲受财礼银十三两;中等亲受财礼银七两;下等亲受财礼银五两;如不遵;禁,额外重索者,将此项款缴入众。(2)上等亲男女嫁娶,男自愿娶,女自愿嫁,两造父母不依,男女私约拐带,上等娘家,准吃财礼银十一两;中等娘家,吃财礼银七两。[9]《高增款碑》规定:“议男女婚姻,男不愿女,女不愿男,出纹银八两八,钱一千七百五十文,禾十二把。” “于归完娶,是次生男育女,运命不和,爱新弃旧,改折等规定五十二千文”。[10]《乡规民约碑》关于彩礼方面的规定有:“一议求亲,不许相退,罚银八两八;一议姑表,勿论男女相退,罚银八两八;一议成亲,男女相退,罚银五十贰。”等等。[11] 三、 改革的推力与阻力 婚俗改革的目的是“为挽颓风”,“俗兴化美,益己利人”。方式有两种:一是地方头人在自己处于“无以挽回”的境况下,“鼎新连名具禀于黄堂,叠沛悬纶于天下,里捧天批而甚藉尼后以流传”,借助官府的“批示”,以实施自己的主张;二是地方头人共同商议,订立款约,利用地方力量以实现婚俗改革的目的。[11]康熙平江碑、乾隆四里塘碑、同治已得碑、光绪彦洞、瑶白碑属于前者;光绪启蒙碑和嘉庆四里塘碑则属于后者。地方官府为维护地方安靖,以示自己的政绩,不仅批示支持地方头人要求改革的婚俗请示,且自己也发出禁革的告示,可见清朝从康熙到光绪的200多年里地方官府和乡村绅士都致力于婚俗的改革。 1、社会精英的作用 任何“立法”是制定一种适用于一定区域内所有人的规则,追求法普遍性和一般性,力求系统性、全面性和预见性。同时立法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它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其好坏无法从其本身得到答案,只有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才是好法。而在“民间立法”中社会上层的力量作用积极,而来自社会基层的力量的作用较为微弱,有时立法者不论是在自然的时间、空间,还是在人文的时间和空间上更接近于社会上层的力量,特别是以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为主体而形成以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姿态出现的社会上层的力量,就更容易受这种力量的影响,这时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成为了当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一种理想制度设计的蓝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更可能受民间“立法者”个人主观愿望、政治热情等因素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和良好的愿望的作用下,将引导社会的规则自觉或不自觉带进了“民间立法”之中。甚至“民间立法”倡导者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如清道光十一年(1885),边沙、寨伍、八教、者晃西洋店等寨头人率700余户聚集边沙合款,商议婚俗改革,形成著名的“八议”款规。“八议”碑的碑名就叫“因时制宜”,碑的“前言”痛陈“姑舅转亲”的恶果,认为:“姑表分财之规,不无陋弊。或藉此而赖婚枉利,或因此而悬搁终身,以致内怨外旷,覆宗绝嗣,因以构讼经官,倾家荡产,呜乎殆哉,祸甚烈也!……于是一带乡邻,合同计议,……将见俗兴化美,益已利人。……谨将规例,特勒贞珉”[12],倡导革除这种相沿已久的陋习。由于地方有识之士的倡议,地方官为维护地方安靖以显示政绩,不仅批示支持地方头人要求改革婚俗的请示,甚至自己也发出“禁革”的告示。福山认为:不论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它们自身都不足以产生出构成社会秩序的全都规则,在关键时刻它们都需要由等级制权威来进行必要补充。[13]在剑河小广环龙庵遗址上有一块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立的“永定风规碑”,记述以潘老乔为首,联合化敖、谢寨等侗族村寨的寨老王士元、彭宁绍、谢贵乔、杨德桂、文登朝等就“姑舅转亲”的陈规陋习具禀首告到府,经镇远府正堂大人批准,特立此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载:“嗣后男女婚娶照定例,须由两家情愿,请凭媒妁,发庚过聘。严禁舅家强娶滋事。如违重咎不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4]同治五年(1866),黎平知府徐达邦、光绪二年(1876)黎平知府原开第就曾出过“禁革”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