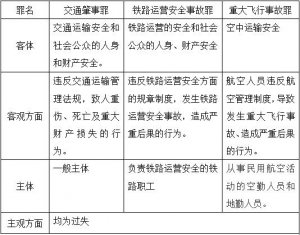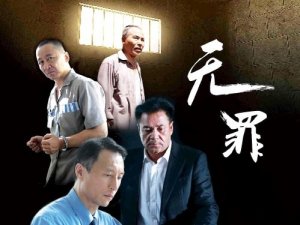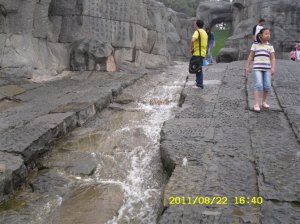|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6]鲁15刑初33号),本案因被害人可能存在侮辱苏明霞(于欢之母)情节而被称为刺死辱母者案。该案为媒体与公众广泛关注,成为一桩公案,通读本案一审判决书,心有所思,以为探讨。 关于本文,是基于如下三个前提:一是未生效刑事判决书具有法律效力。于欢案已经上诉并为山东省高院受理,因此,它目前是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书,最终能否生效,要看二审法院怎么裁判。一审刑事判决书未生效并不等同于没有法律效力,在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情况下,二审法院不能作出刑罚更重的判决,这至少可以表明一审刑事判决书一经送达,就有法定“既判力”。二是争议案件刑事判决书应当具备更多要素。每个工作日,法院都会产生数量众多的刑事判决书,这些判决书中,数量居多的简单案件,符合“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收集、出示的证据也无异议,对定罪量刑也无实质性异议。于欢案则属于争议案件,也是疑难案件,控辩双方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个别事实与法律的定性,意见很不一致,这就需要判决书更详尽地描述事实,更多地进行分析与论证。三是以看者的视角观察判决书。我不是法官,除了学习法律的时候写过粗糙的模拟判决书,未曾写过判决书。从阅读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受到的启发,我们观察和评论判决书,既可以从法官应写的角度,也可以从阅读者想看的角度。从阅读者的角度:判决书主体部分应该是议论文与记叙文的结合体,前半部分客观地记述案件事实,后半部分对相关的事实进行分析推理,还要视情况对判决的结果进行论证。 通过阅读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主要的感受是:争议案件刑事判决书,应当重点考虑以下三方面要素。 1、记述事实准确完整。总的而言,判决书是对相关案件的事实进行的法律评价,准确的记述事实则是必要前提,记述案件事实,应实事求是地记录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判决书记述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完全与客观情况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证人的记忆不清,法庭科学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有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亦是“两个基本”的要求;对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则不应被忽视,无法查明而存疑的,需要依据证据规则作出认定。在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中,所记述的事实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部分事实记述不全。比较突出的是“出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当晚出警情况”与“冠县公安局关于本案有关情况的说明”这两份证据,具体内容均未在判决书中进行更进一步的表述,这就好比一篇文章只见题目不见内容,于阅读者而言,写了等于没写,根本不知是怎样的一个出警过程。判决书认定:“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而于欢辩解称:“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让我坐到沙发上,我不配合……他们就开始打我了,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朝着他们指了指,……他们过来还是继续打我,我就拿刀子冲围着我的人肚子上攘了……”于秀荣(于欢姑妈)则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称:“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假如于秀荣所说的是真实情况,则判决书的认定是有问题的,而实际上,执法记录仪是最能客观体现“有无防卫紧迫性”的客观证据。因此,没有在判决书记述具体出警情况,显然是一个错误。 二是矛盾事实缺少说明。判决书中记述如下证人证言:“苏银霞证实,我们厂子因为倒贷款于2014年7月份从吴学占那里借了100万元,口头约定是百分之十的月息。”而书证则是:“赵荣荣与苏银霞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收到条、转账委托书、转账凭证、二手房买卖合同等证实二者之间的借款、还款事实。”两份证据对不上,法官照理应对此进行调查,并将这一过程记录到判决书中,否则的话,对阅读者来说,看到的是一个有缺漏的故事。 判决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证据进行的归纳与概括,因此,在记述证据的时候必然会有所取舍,过于冗杂显然是不足取的。但在取舍过程中,如果为精炼而精炼则更不足取,它有可能会词不达意,也可能会断章取义,两害相权取轻,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宁可多用一点文字,也要把事实全面准确记录。 2、庭审过程充分展现。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所有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都要在审判中提交和质证,所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项都要经过法庭辩论,法官的判决必须完全建立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之上,被告人的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以审判为中心,其表现就是在判决书中要完整记述整个庭审过程,仅仅在庭审笔录中有所体现是不够的。庭审笔录是一份详实的记录,相比判决书,其是未经加工编辑的原材料,可读性不强,而且不对当事人以外的公开。于欢案一审判决书,难以体现以审判为中心。 一是庭审过程记述不全。相当多的刑事判决书,其主体部分基本结构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辩解及辩护人意见,法庭查明事实,法庭认定证据,判决结论。这种判决书结构比较适合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但并不非常适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庭审过程记述完整全面容易言多必失,产生各种失误,从而招致阅读者的各种批评;但庭审记录过少,却可以使阅读者除了批评文书过于简略之外,连发现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争议案件民事判决书,往往把原被告双方的观点写得清清楚楚,证据质证采信过程记得明明白白,在征询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归纳争议焦点,相比之下,争议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相形见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