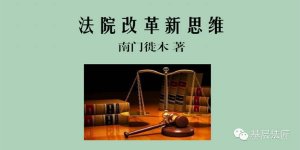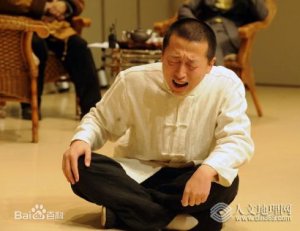辱母案和毛立新大律师商榷
来源:陈光武 作者:陈光武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05
摘要:晨光案例 【陈光武按] 和毛立新大律师商榷 赞同毛律师关于暴露生殖器和防卫无直接关联,但认为非法拘禁依然可以实施防卫的观点。这是前期法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但仍有商榷: 1、文章既认为判决书“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论证上依据不足”,又认为“量刑显然畸
|
晨光案例 【陈光武按] 和毛立新大律师商榷 赞同毛律师关于暴露生殖器和防卫无直接关联,但认为非法拘禁依然可以实施防卫的观点。这是前期法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但仍有商榷: 1、文章既认为判决书“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论证上依据不足”,又认为“量刑显然畸重。二审大幅度减轻处罚,改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充足的,是可以期待的”。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文章模糊不清。 2、关于警察离开,要考虑下列因素” (1)”离开“应当是指离开非法拘禁现场。 (2)非法拘禁正在进行,警察未妥善处置; (3)警察离开时,于欢娘俩欲追随警察试图摆脱控制,寻求保护,这时警察应就在身边。但仍然离开。 (4)于欢娘俩的"到外面调查”证言,应是办案人员的同行护短人为言辞,故意这样写,降低警察责任。因为警察离开现场到外面干什么,于欢娘俩并不知情,不应当清楚。 (5)关于警察“到外面了解情况”,并没有相关证据佐证。 值得重视的是,警察的离去是于欢绝望最终实施反抗的直接原因。 3、于欢被殴打行为无须继续调查,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至少是一巴掌。其它有推搡、肢体控制等行为。 4、只要认可正当防卫,死因问题不应当成为法律人讨论的重点。 尚权速递丨毛立新: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的司法论证存在严重问题2017-04-02 毛立新 尚权刑辩3月30日下午,由蓟门智库、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105期“蓟门决策” 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该期论坛的主题是“正当防卫司法标准的偏差与矫正——反思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论坛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轩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副教授王贞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志伟,北京大学教授沈岿、陈永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奋飞,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鹏等作了发言或点评。以下是主办方整理的毛立新主任的发言,本次刊发前,由其本人作了一些补充、修改,供大家参考。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的司法论证存在严重问题——在第105期“蓟门决策” 论坛上的发言前面几位专家、学者讲得比较全面了,我补充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关于一审判决书的司法论证问题存在的问题是明显,前面几位学者已经指出来了。我补充两点:第一,在证据内容的撷取和事实认定上,具有倾向性。从新闻报道和其他渠道披露的信息看,有些证据和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得到体现;即使从判决书列举的证据内容看,事实认定上也存在人为裁剪的问题,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情节,被忽略或者淡化了。例如,于2016年4月14日之前被害人实施的暴力催债行为,判决书只字未提;对杜志浩实施的“脱裤子露生殖器、让苏银霞闻鞋子”等行为,判决书仅简单概述为 “对二人有侮辱言行”;杜志浩被刺伤后,自行驾车前往数公里之外的医院就诊,并在医院门口再次与人发生争执,终在4个小时后“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判决书基本未提及,等等。司法论证的合理路径,应当是:证据分析→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结论。但实际上,在实践中,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法官先有一个结论,再去寻找法律和裁剪事实,最后再去挑选和撷取证据。这种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来认定事实和挑选证据的现象,实践中比较普遍,也是司法论证方面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二,判决书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论证上依据不足。首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审判决书并没有否认“不法侵害”的存在。判决书明确认定于欢“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即认定了“不法侵害”的存在。判决书认为不构成正当防卫,其立论的基础并不是否认“不法侵害”的存在,而是认为“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即认为除了要有“不法侵害”这个前提,还必须具备“防卫的必要性”,才属于正当防卫。判决书认为“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的依据有二:一是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二是派出所已经出警,结论是: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个论证过程,暴露出几个问题:一是仅仅关注了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权”,而忽视了其他权利被不法侵害,亦可构成正当防卫的理由;二是对方是否使用工具,不是判断“紧迫性”、“必要性”的唯一依据,如果对方人多势众,赤手空拳同样能够构成重大、现实威胁;三是派出所虽然出警,但并没有有效控制局面、防止侵害行为继续发生。至于是否要求具备“必要性”问题,刑法学界是有争议的。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是认为:正当防卫需以必要性为前提。“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依然是法益衡量说。一方面,如果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悬殊,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如为保护笼中一鸟而杀害盗窃犯的,不管具有多大的必要性也不得认定为正当防卫。这是法益衡量决定的。”“对于轻微的不法侵害,对于处于被保护、被监护地位的人的一般不法侵害,对于非暴力的敲诈勒索行为,对于自己所引发的一般侵害行为,不宜实行正当防卫。”根据这种观点,我分析,法官的论证思路大概是: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程度相对较轻,而且警察就在门外,因而,缺乏正当防卫的“必要性”。只不过,法官把“必要性”之论证,错误地表述成了“紧迫性”。而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紧迫性”是个防卫适时的问题,只要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就存在“紧迫性”。于欢案中,“非法拘禁”等不法侵害一直在持续,“紧迫性”当然不是问题。做此分析,是想洞悉在判决书文字背后,法官进行司法论证的基本思路。这一分析告诉我们,一审判决书对正当防卫的否定,其立论的基础并非否认“不法侵害”的存在,而是认为缺乏正当防卫的“必要性”。因此,在进行批评和批判时,不要批错了方向。二、关于“掏出生殖器”及“辱母”的问题 首先,媒体报道的相关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得到体现,也缺乏相关证据支持。媒体报道是:“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更令人发指的是,催债人员杜志浩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当着她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这令于欢濒临崩溃。”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书未予认定,仅认定杜志浩“对二人由侮辱言行。”从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证据内容看,被告人于欢的供述与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杜志浩确有言语侮辱、脱裤子露生殖器、让苏银霞闻鞋子等行为。但在证据内容中,没有人提及杜志浩“掏出生殖器,当着她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这一情节。即,该情节,目前是缺乏证据支持的。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掏出生殖器”“辱母”情节,对本案正当防卫的认定,并无关联性。因为,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该行为已经结束,不能再成为此后实施正当防卫的理由。“掏出生殖器”“辱母”行为对本案的法律意义,一是可以证明于欢是激愤杀人,二是可以证明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媒体报道中,把“辱母”与“正当防卫”建立因果关联,在法律层面,是不恰当的,法律人不能跟着走。对于是否具备正当防卫的理由,关键是看在警察走出接待室之后的4分钟内,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前面,陈永生教授做了深入分析,我的分析结论基本跟他差不多。从一审判决书所列举的证据看,有数份证据,包括于欢的供述、证人苏银霞、刘付昌的证言等,能够证明:在接待室内,于欢动刀之前,对方不仅阻止于欢出去,还对于欢实施了殴打行为。当然,此点,仍需要二审法院去进一步查明。既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于欢实施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一审判决书对“殴打”并未认定,需要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从证明标准的角度讲,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其证明并不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地步,只要有相当可能性就应予以认定。三、关于警察是否存在“不作为”或者“不当”的问题 警察到达现场后的作为和作用,对与本案正当防卫的认定,影响甚大。但遗憾的是,这一部分的事实真相,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该事实,对于判断于当时现场的情势、于欢母子的处境,至关重要。假设,警察到达现场后,积极作为,而且控制了局面,则于欢实施防卫的必要性、紧迫性是否存在,确实就成了问题。相反,如果警察消极不作为,于欢求助于公力救济无望的情况下,实施私力救济,实施正当防卫,就有了必要性、正当性。对此事实,媒体报道为:“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而一审判决书的认定是:“22时10分许,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与媒体报道大相径庭。从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证据看,被告人于欢的供述是:“这时,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证人苏银霞的证言是:“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派出所出警民警到了接待室问我们谁报的誉,我说对方的人打我儿子了,民警到门厅外边问怎么回事。”两人都是说警察出去是了解情况,并没说警察离开。其他证据,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可以证明:警到场接待室现场后,确实说了一句话“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然后走出了接待室。至于警察出门,是出去了解情况,还是说要离开不管了,目前并不清楚。鉴于当晚的处警情况,出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予以记录,而该记录情况尚不清楚,且公安机关尚未回应,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亦未作出,因此,尚不能确定警察存在“不作为”。 但从警察的现场表现,及最终的处置效果看,不当行为是存在的。根据处警的规范要求,警察到达现场后,首先是判断警情,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然后是,控制现场;再然后,是调查取证。本案中,警察到达现场后,对警情的判断疏忽草率,只进行了口头制止和警告(“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然后就出去了。对现场的控制不到位,没有及时隔离冲突双方,导致警察一出接待室的门,室内冲突就升级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实践中,公安机关对因为经济纠纷引起的冲突,一般不愿意介入。一方面,是怕有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另一方面是怕麻烦。但实际上,处置因经济纠纷引起的违法犯罪行为,属于警察的职责范围,与“插手经济纠纷”是两个概念,不能因噎废食,该处的警还是应当处。当然,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些,处置的难度也大一些,建议公安部总结一下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梳理一下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此类因经济纠纷引起的警情,制定出台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工作指引,指导基层民警妥善处置这种警情。四、关于杜志浩的死因问题 媒体报道:“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于秀荣的老伴说,事发后他曾去医院打听,杜志浩因琐事还在医院门口跟人发生争执。”而一审判决书仅表述为:“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被送往医院抢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2时许死亡”。没有提及,所列举的证据内容中也没有显示:杜志浩自行驾车前往数公里之外的冠县人民医院(未去距离更近的其他医院),且因琐事还在医院门口跟人发生争执。另外,从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证据看,杜志浩心血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48.0mg/100mL,即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另外,杜志浩被于欢捅伤,时间是在22 时21分许,而死亡是在次日凌晨2时许,这中间有4个小时的时间。这4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因其个人原因等,导致延误救治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否与杜志浩的死亡亦具有因果关系?此方面,一审判决书完全忽视了,需要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如果杜志浩自行驾车前往医院、与人发生争执而导致延误治疗,等于有其他因素介入了杜志浩的死亡,会出现多因一果的问题,于欢的刑事责任也应当相应减轻。至少,不能让于欢一个人对杜志浩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不应承担“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不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总之,不管是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认定,还是从被害人死因等方面论证,一审判决书判处于欢无期徒刑,量刑显然畸重。二审大幅度减轻处罚,改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充足的,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