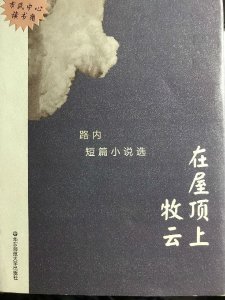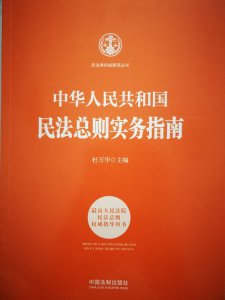|
一方面,相应新兴权利的主体资格应当是开放的;或者虽然是封闭的但却为封闭系统以外主体所接受。其中,前半部分是说,该新兴权利对于所有相关主体而言都是可能获得的利益,任何主体都不会因为某些先天条件或后天条件的存在而完全没有可能成为这项新兴权利的主体。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可能”性,强调的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至于经验中一个人是否一定会实际履行相应权利则在所不问。譬如即便确立了同性婚姻这项新兴权利,一个异性恋者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实际享验它。后者则是指该新兴权利的设定虽只能及于特定主体,但其他不可能践行该权利的主体却认可、接受了其主体资格的封闭性。典型者如儿童权益保护法领域:考虑到儿童权益保护法可能创设的新兴权利所指涉之主体一定只能是儿童,并且任何成年人从逻辑上都不可能“逆转”为儿童——这意味着儿童权益法所创设的新兴权利之主体资格是封闭的,但由于相应新兴权利的创设得到了“儿童”这一封闭系统以外的成年人的接受,则即便相应新兴权利主体资格对于成年人来讲虽是封闭的,也可能因为后者的接受本身而得以确立。必须明确的是,此处封闭系统外主体的接受、认同必须不是基于操纵、欺诈、强迫,而是纯粹出于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该新兴权利还应该至少具备如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首先,与该新兴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公权机关。如果确立公民的某项基本权利只是导致公权机关义务的增加,则显然并无道德或法理上的正当性问题,因为公权机关存在的根本目的及必要性基础就在于保障并不断丰富公民权利。典型者如虚拟空间权利的出现,其主要面向的就是国家公权机关之义务(提供足够的保障措施以及救济渠道)。如果一项新兴权利的义务指向的是私权主体时,则其次,它面向的只是其他私权主体的“消极义务”,也即只是给其他私权主体增设了不得作出损害相应权利行为之义务。譬如,承认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并没有增加其他主体的积极义务,而只是科设了一种“不得干涉同性恋者婚姻自由”之消极义务。考虑到如果不确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本也不存在相应干涉的可能,也就是说非同性恋者的其他人本也无法干涉同性恋婚姻,因此,因确认同性婚姻而科设给其他主体的“不得干涉”义务实际上很难说是对其他主体义务的增加。或至少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相对于同性恋者因同性婚姻权的确立而获得的巨大利益而言,对其他主体相应义务的科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既如此,则当然应该给予同性恋群体同性可婚这一主张以新兴权利之地位。概言之,当一种新的利益主张基于资源拓展的前提,并且只是给其他主体带来消极义务时,就应当赋予此种主张以新兴权利之地位。另外,如果新兴权利指向的是私权主体的积极义务时,是不是就绝对不应承认它?从逻辑上讲,当成就如下条件时,似乎也可以承认、确立该新兴权利:如果所有相应义务主体都愿意承受相应义务——当然,这种“愿意”同样必须不是基于操纵、欺诈、强迫而是纯粹出于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就笔者的观察而言,此种情形比较贴切的例证是妇女权益保护法领域:考虑到妇女权益保护法所可能创设的新兴权利之主体只能是妇女,而其针对的言说对象显然主要是男性(并且显然绝大部分男性将不会通过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因此妇女权益保护法实际上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对男性科设某些义务(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显然,这些义务之所以可以接受,只是因为它们得到了男士们的认可、接受。 至于如上第三个条件,最大的疑问可能是:此处是否有必要强调它?让我们以国际空间法为例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由于世界各国科技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因此,当部分“先进者”最初掌控空间技术时,它对外层空间的探索一方面当然属于典型的“可掌控资源的新拓展”,因而无论赋予它对外层空间享有怎样的权利,都至少在当时不会造成对其他国家造成权利的克减;但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始终存在“赶上来”的可能,因此,当只有“先进者”掌握外层空间探索技术时,如果片面确认或赋予它对外层空间的权利,就可能导致后来者权利的克减,进而实际上造成不公平分配之格局。也因此,即便一项新利益主张的逻辑起点是可掌控资源的拓展,并且也符合如上前两个条件,它要获得新兴权利的资格还必须同时满足这第三个条件。 四、结语,并及新兴权利理论的几个问题 综上,只有当一个利益主张至少具备如下两个条件之一,它才能被从逻辑上恰切地称之为“新兴权利”,也就是说,此时一种新兴权利才真正得以确立:首先,按照广泛被接受——其标志往往是通过特定之程序的考核、筛选——之社会价值判准,既有实在法关于权利的分配或安排呈现出不公平之格局,而一种利益主张有利于打破并调适该不公平分配格局时,将导致新兴权利的产生。其次,随着可掌控资源的拓展,一种利益主张既不会导致其他主体所不能接受的权利克减,也不会导致按广泛被接受之价值判准看显失公平的权利分配格局时,则应当赋予该利益主张以新兴权利之地位。 必须予以明确的是,此处从逻辑上对新兴权利产生前提条件所作的分析,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因此并不意味着经验生活中存在的所有新兴权利都能够严格地对应于如上某一情形。譬如我国于2016年全面放开的二胎生育权:一方面,它具有一定且明显的新兴权利之意味,因为它确实是“过去所无、现在所有”的法定权利;但另一方面,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如上第一种情形,即,它的基础尽管一定程度上具有、但却并非典型的对不公平资源分配格局之调适的意味;再一方面,它也并不严格地属于第二种情形,因为很难讲它的基础是“物理发现”型的可掌控资源之拓展(生育“资源”始终都在),甚至也很难说是“观念拓展”型的可掌控资源之拓展(它并不具有典型的“新兴”观念之意味)。毋宁说,二胎生育权同时具有如上三种意味但又不能典型地归类为如上任何一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前文通过逻辑分析构造的理想类型不能成立?对此,或许可以借用拉兹(Joseph Raz)的如下判断来予以回应,“我们应当记住,清晰的概念区分并不意味着概念所涉事例也清晰存在。所以,缺乏清晰事例不应当成为我们努力阐清概念区分的障碍”。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因为经验中的清晰界分非常困难甚或不可能,逻辑上、概念上的澄清、释明才显得特别必要而重要,因为唯有如此,一方面,我们才不至于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时而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也才符合本文开篇处提出的那个命题:新兴权利理论首先应关注的恰恰是它的逻辑起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