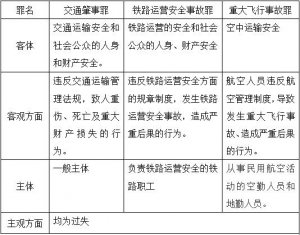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刑法分则研究 互联网金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解释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守解释*——侧重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参照魏东 田馨睿** 引用本文时请注明出处:魏东、田馨睿:《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守解释》,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108-120页。 内容摘要:行为人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多年来被司法解释和生效判决确认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新近出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同类型行为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并非一律违法,从而出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罪标准上的不统一乃至“二元标准现象”。从我国金融政策、尤其是金融刑事政策的发展观审查,当下我国有必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保守的刑法解释,行为人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只有在其具备“用于贷款”、“欺骗手段”或者“未尽审查义务”要素时方可以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素类型限于三种:一是“吸收公众资金+用于贷款型”,其侵害的法益为金融管理秩序;二是“吸收公众资金+欺骗手段型”,其侵害的法益为公众资金安全;三是“吸收公众资金+未尽审查义务型”。三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类型化限缩,可以通过对本罪的保守解释实现,并达致网上网下本罪犯罪构成标准的一致性。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刑法解释 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实体企业和个人在向银行借款困难的情况下,转向民间借贷领域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国家也一直在鼓励金融行业的创新与放开。但是,实体企业和个人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多年来均被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与此同时,以P2P网络借贷[1]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2]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一只重要力量。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共有P2P网贷平台2595家,其中2015年比2014年增长了1020家,增长数量创下历史新高。[3]并且随着监管“靴子”的落地,同类型的行为在实体金融领域中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却不被监管方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存在互联网金融和实体金融中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标准上的不统一乃至“二元标准现象”。因而理论上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剖析并探索解决路径。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解释“二元标准现象”分析(一)“二元标准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从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到的真实案件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解释二元标准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全国范围内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生效判决的随机抽样审查表明,在实体金融领域,实体企业和个人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以及相关中介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量刑,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形是如下“案例1”所描述的情形;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实体企业和个人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以及相关中介行为并非均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形是如下“案例2”所描述的情形。案例1(实体金融领域):实体企业A公司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向理财咨询公司B公司提出融资需求。B公司将其融资需求进行包装,并找到担保公司C公司提供担保,之后对外宣传,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4]案例2(互联网金融领域):甲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乙公司为P2P网贷平台,甲公司通过乙公司平台将其购买设备后租给生产企业所产生的租金债权转让给投资客户,但最终发现甲公司的融资租赁项目为虚构,在这种情况下,甲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集资诈骗罪无疑。但是乙公司不明知甲公司的债权让与行为为假。对“案例1”,司法人员认为A、B、C公司的行为均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四性”(即“四个条件”: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的要求,即使该集资是为了生产经营,仍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5]对“案例2”,司法人员均引用2015年12月28日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研究起草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2016年8月17日四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之规定作为解释依据,[6]认为乙公司的行为虽然客观上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帮助行为,但是主观上所认识到的甲公司的行为是“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尽管其符合《解释》“四个条件”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为《暂行办法》所禁止,属于合法行为。因此在乙公司所认识到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范围内,乙公司没有罪责,不构成犯罪。[7]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实体金融领域的A、B、C公司的行为与互联网金融领域乙公司所认识到的“行为”性质完全相同,都可以归属到“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范畴,但是法律评价却截然相反。这主要涉及到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两个规范性文本依据的引用不同:“案例1”引用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而“案例2”引用银监会等四部门《暂行办法》。(二)法律解释的参照依据不同所导致的入罪标准不同1、《解释》对入罪标准的影响《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简单罪状,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扰乱金融秩序的,处……”。《解释》第1条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归纳为“四个条件”:“(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且《解释》第3条还专门针对“生产经营”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依据《解释》的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观方面要件成立的唯一标准就是“四个条件”。而“生产经营”并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出罪的刚性要素,尽管“生产经营”要素可以成为免处、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条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是非吸行为刑事违法性降低甚至消灭的表现。但是问题在于,《解释》看似想起到提示性的引导作用,即对为生产经营的非吸行为慎用刑事措施;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反作用,即司法实践一般只关注“清退资金”,反之则肯定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从这里可以看出,理论界一直反对和批评的将为生产经营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现象,[8]根源在于《解释》将这一事项仅仅作为本罪可自由裁量、需实质解释的违法性要素而不是作为刚性的出罪要素来规定的。因此,我们对本罪进行保守解释的关键点也在于此。在《解释》的指导下,多年来法官一直选择性地忽略对此类行为定罪的不合理性,径行作出有罪判决。而十分矛盾的现象是,政府一直在鼓励发展民间金融。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政府专门打造了“金融一条街”,其中遍布各类投资理财、理财咨询类公司。这些中介公司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将作为借款人的各类实体企业和作为出借人的自然人串联在一起,在红火的时候,实现了出借人、借款人、中介人的双赢,此时政府不闻不问。而当经济下行,出现还款危机时,老百姓一闹事,公检法则抓人、判刑。相当于这些中介公司、实体企业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民间借贷时从源头上就是违法甚至犯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成为悬在向民间融资的实体企业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9]这是一个悲哀、无奈的事实。2、《暂行办法》对入罪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靴子”的落地,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P2P网络借贷“原罪”问题。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鼓励创新、支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并具体明确了P2P网络借贷的合法性——“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其后,《暂行办法》(以及《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和借款人的禁止行为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了规定。《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禁止行为共13项:“(一)为自身或或变相为自身融资;(二)直接或间接接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三)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四)自行或委托、授权第三方在互联网、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进行宣传或推介融资项目;(五)发放贷款,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六)将融资项目的期限进行拆分;(七)自行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募集资金,代销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八)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九)除法律法规和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允许外,与其他机构投资、代理销售、推介、经纪等业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混合、捆绑、代理;(十)虚构、夸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收益前景,隐瞒融资项目的瑕疵及风险,以歧义性语言或其他欺骗性手段等进行虚假片面宣传或促销等,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或不完整信息损害他人商业信誉,误导出借人或借款人;(十一)向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结构化产品及其他衍生品等高风险的融资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十二)从事股权众筹等业务;(十三)法律法规、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的借款人的禁止行为5项:“(一)通过故意变换身份、虚构融资项目、夸大融资项目收益前景等形式的欺诈借款;(二)同时通过多个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者通过变换项目名称、对项目内容进行非实质性变更等方式,就同一融资项目进行重复融资;(三)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以外的公开场所发布同一融资项目的信息;(四)已发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含有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内容,仍进行交易;(五)法律法规和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活动。”根据法不禁止则为允许的原则,网络借贷只要不涉及到《暂行办法》规定的上述禁止性规定,均为合法行为。在禁止性事项中,笔者将可能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产生交集的情形进行了归纳,包括:虚假宣传等欺诈融资,重复超额融资,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自融自用、自己担保,未尽审核义务,将借款用于高风险领域等。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实践中长期被争议的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只要不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均应当被认为是合法的。[10]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P2P网络借贷的合法行为的外延远大于《解释》相关规定的外延,而其违法行为的外延则远小于《解释》相关规定的外延。换句话说,根据《解释》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根据《暂行办法》不一定构成违法行为。但是目前这种出罪化的“政策红利”仅限于网络借贷。实体民间借贷中,即使不具有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虚假宣传等行为,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仍然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实体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合法与违法犯罪的界限不一致的问题。笔者将其称之为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二元标准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二元标准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真正的法律冲突,而是由于金融政策、尤其是金融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和法律解释立场所引发出的“新”问题,亦即依据《解释》或者《暂行办法》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梳理问题。(三)“二元标准现象”的不合理性笔者在此揭示出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二元标准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互联网金融活动并没有较之于传统实体金融更加具有值得特别保护的地方,相反,其反而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据统计,2014年,全国P2P网络借贷涉嫌非法集资发案数、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分别是2013年的11倍、16倍和39倍。[11]2015年问题平台数量高达896家,占全国平台总数的34.5%。[12]目前爆出的问题P2P平台动辄涉及金额上亿甚至上百亿,涉及群众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如E租宝、东方创投、华强财富、力合创投等。现实的状况是,实体的民间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或解释来确认其所实施的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的合法性。《解释》没有合理地规定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区分标准,两高其他关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解释性文件同样没有具体合理的规定。相反,《解释》第3条第四款关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的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恰恰确认了此类行为的违法性。较新的一些地方性司法机关的解释性文件均在《解释》的基础上亦步亦趋,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如2016年1月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我省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都是一种还本付息的行为,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集资对象针对不特定多数人,且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是否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进行认定”、“行为人按生产经营规模所需吸收资金,并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清退本息引发纠纷、其资产足以还本付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13]四川省的上述规定虽然在《解释》“免予刑事处罚、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还本付息,也即是说,还不起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作为犯罪处理。此类解释性文件的共同点在于,都模糊处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默示肯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将不处罚作为“政策恩惠”,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兜底口袋”。但是显而易见,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是有合理性的,因而也应当是合法或至少不是犯罪的。所以理论界孜孜不倦对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进行研究,甚至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存在,为这种行为去犯罪化、为行为人脱罪而奔走呼号。但问题是,学者们所研究出的区分二者界限的标准,如合理界定“社会公众”的含义、合理界定集资的用途(或以目的进行限制)、区分“资金”与“存款”、加入欺诈要素等等,[14]虽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一者没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区别的正面规定,二者《解释》的“反向确认”为生产经营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违法性的规定,三者广大司法官员尚缺乏系统性的法律解释学知识,四者此类案件往往面临较大的集资群众上访的维稳压力,司法往往选择性地忽略定罪当中的不合理性。这种情况下的定罪处罚,展现了司法机关不以结果妥当性为价值引领,滥用法律解释或者消极进行法律解释,致使刑事司法权力呈现出一种过度扩张、不受束缚的结果。“以解释为核心的方法助长了权力与权利扩张的趋势,并为权力与权利的争夺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15]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由于《暂行办法》的出台,司法机关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就可以将其规定内容作为解释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充分理由和“规范”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合理定性结论。《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到了制度上的松绑作用,给予了司法在处理P2P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类案件时以明确的指导依据,使得P2P网贷平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即传统实体民间金融领域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当以《暂行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保守解释、限制解释,以适应经济社会和金融政策的发展。在过去,理论界一直在提保守解释、限制解释的问题,但是总是学术的归学术、实践的归实践,老死不相往来。而建立在《暂行办法》基础上的刑法保守解释,则可以给予我们这种解释合法、合理的充分底气,并给予了我们保守解释的明确方向。可以说,《暂行办法》的出台一方面对部分借贷行为——网络借贷——作了出罪化处理,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凸显出了司法实践中区别处理网上和网下借贷的不公平、不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之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保守解释以与《暂行办法》的规定相协调,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保守解释的理由(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法益的认识变化与保守解释的正当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为何?过去的理论研究中较少见专门针对本罪法益的论述。有学者在论述中提到了金融特许制度,“金融特许制度所形成的思维逻辑在于凡是未经监管机构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活动均视为非法”[16]。我们从刑法条文以及《解释》出发作字面理解,也可以得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或者是国家金融活动的专属性。还有学者认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商业银行设立的准入制度。[17]该学者从立法目的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擅自设立商业银行的变种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商业银行的设立秩序,确立商业银行设立的审批制,而非其他的金融秩序和非金融目的的直接融资行为。这种论点将该罪的保护法益范围进一步缩小为银行业的秩序或者准入制度。笔者认为,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限定为银行业的秩序或者准入制度的理解具有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范围的目的和作用,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非实际情况。《暂行办法》规定吸收资金用于炒股、场外配资的也属于借款人的禁止行为,进一步讲,这种吸收资金用于炒股、场外配资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完全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定罪处罚。但是这里炒股、场外配资等在行政法上是属于证券法(属于广义金融法范畴)而非商业银行法调整的范畴。所以不管是从司法实践的现状还是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早已超出了银行业秩序或者准入制度。同理,“金融管理秩序”的法益范围也同样被现实所逾越。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的理解,必须从保守的客观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进行。“只有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直接追求所有解释之本来目的,一寻找出目的观点和价值观点,从中最终得出有约束力的重要的法律意思,从根本上讲,其他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人们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途径。”[18]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法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质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或者说,对法益的解释会发生变化。[19]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释而言,笔者的态度是应当对其进行限制解释。但是这种理想要招进现实,不是简单的呼口号或直斥现实之非所能达到的。而是必须要目光不断往返与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找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而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尊重现实。从最初的立法原意而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在市场经济之初、金融市场相对更加保守,视金融为国家禁脔、市场禁区的情形下设立。存款、贷款等金融活动均被视为金融机构独享的权力。我们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等规章制度的规定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意图。此时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将其理解为金融管理秩序或者银行业管理秩序可能是合适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市场在不断进行改革开放和市场化,金融活动不再被视为金融机构专属,存在从金融机构中心主义向金融交易中心主义的转变。[20]刑法的调整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以贷款领域为例,最初放高利贷的行为被认为是非法经营罪,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关于涂汉江非法从事非法金融业务行为性质认定问题的批复》即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断有以此罪名作出的有罪判决。这里的非法经营,显然是指非法经营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专属的贷款业务。但是一直以来,放高利贷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就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大量判无罪的案例。而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放高利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实际上是对贷款这一金融活动的放开,贷款不再被视为国家垄断的金融活动,不再值得刑法规制。而在吸收存款领域,由于小微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难的现象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国家所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等改革措施杯水车薪,而求助于高利贷市场无异于饮鸩止渴,所以民间借贷一直以来都具有极其广泛的存在基础。很多地方默许甚至鼓励民间借贷的发展,打造专门的金融街、金融管理部门为民间借贷站台,电视、网络堂而皇之进行宣传等均是对此的注脚。而民间借贷正是广义上的金融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关照到这种非银行专属的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应有之义。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最典型的情形——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中收取利息差——当中所体现出的金融性质。现在的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视角将非银行金融业务类的吸收公众资金行为完全无罪化,而是在正确认识法益变化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限制。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的理解,应当区分三种形式。一种形式为吸收资金又放贷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专属的金融活动是没有疑义的。上述论述所认为的放开的市场化的金融活动均只限于单纯吸收资金或者单纯放贷的行为。而同时兼容吸收资金和放贷的行为只能是由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实施。这仍然是当下制度上、理论上的共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认为该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是合适的。第二种形式为吸收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或其他非放贷用途的行为。这种行为就不能被认为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违反。因为即使银行也不能吸收资金用于贷款之外的生产经营——这是非银行业的金融活动。这种行为并不侵害金融管理秩序。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吸收资金的行为人有欺诈等手段使出借人的资金安全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下,仍然可以将其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之内。此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保护法益应当被认定为公众资金的安全性。这也是与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进行体系理解的结论。后者的保护法益是公众资金的所有权。而包括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内的一些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公众资金的目的,但是会使得公众资金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下。这才是本罪在此情形下具有科处刑罚的真正理由所在。当然,这种公众资金不安全性的法益必须从构成要件要素上加以具体化,否则,广泛地说,所有的民间借贷行为均具有这种不安全性。第三种形式为网贷平台对于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格条件、信息的真实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履行必要审核的义务。这种行为由于网贷平台未尽审查义务,使该资金陷入不安全状态的行为所以,笔者的结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或者公众资金的安全性。如前所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相应地应当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在不同类型的构成要件下,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为其中之一。得出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法益具体化的保守结论,明确不同的构成要件类型,将具体的限制要素加入到构成要件当中,成为硬性指标,避免将构成犯罪与否的判断点放在在违法阶段进行自由裁量,从而限制目前司法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二)刑法的谦抑性与保守解释的必要性刑法的谦抑性意味着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不轻易介入社会生活,只有当其他社会调控手段失效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进行刑法规制。“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21]刑法不是动辄问罪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法”,不应当动不动就以刑法对行政部门的社会治理不力或者失效买单,特别是这种治理不力或者失效是由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管理混乱、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所导致。就惩治违法行为而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刑法则充任“第二道防线”的角色。[22]因此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反对刑法过度化的命题,[23]倡导刑法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护秩序的“三大一小”理念。[24]此外,民事与刑事界限不清,刑法的谦抑性也要求刑法介入宜谨慎。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是理论与实务界纷纷扰扰纠缠不清的永恒话题。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被认为是权力极大、最可能随意出入人罪的部门,公安部也多次以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要求公安机关慎重处理经济犯罪案件,严禁违法插手经济纠纷。那么,一个行为可以被作为民事、经济纠纷予以有效处理时,刑法就不应当轻易介入,更不能动辄进行刑法评价。就民间借贷领域而言,刑法应当谦抑的原因还在于:一是法律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太过模糊,而司法解释又对其没有进行必要的限制,结果由于时代的发展,当民间借贷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实质违法性在逐步减小甚至小于刑法所要求的严重的法益侵害的程度之时,产生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行政部门对实体借贷中介机构以及民间借贷的管控不力。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行的是金融之实,却不能由金融管理部门进行监管。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这些中介机构的管理则是审查其有无超范围经营、非法经营。就其工商注册的职能来说,一般都是“理财咨询”、“投资理财”等。如果对这种咨询作形式化的理解,仅限于向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对方信息,收取咨询费,相信没有公司能够生存下去,而作实质理解则应当是就投资理财类的产品进行中介、促成双方交易的行为。事实上,如果有类似《暂行办法》之类的规范性文件对民间借贷及借贷中介机构进行规范,并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落实监管措施,是有很大可能在源头上治理好目前存在于民间借贷领域的诸多问题的。刑法不是不管民间借贷,而是说需要管的是严重违反行政监管涉嫌犯罪的民间借贷。但是目前由于行政前置程序的不规范,刑法不得不全面介入,并且对于规范进行的民间借贷行为与严重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能加以清晰的区分,不排除错误介入的情形发生,有违刑法谦抑的本意。三是在对待“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问题上,刑法的介入无效。由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难、向亲戚朋友借款是不可复制的非市场行为、借高利贷是自寻死路,民间借贷没有可行的替代手段。在“搏一把”和直接破产之间选择,绝大多数企业恐怕会选择前者,而不会考虑在还不起钱时的刑事风险,刑法在这里起不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都考虑到刑事风险的问题,都选择等死,虽然没有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但是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显然更大。并且,刑法的介入一般并不会对企业的还款形成促进作用,唯一的效果只是以抓人的手段安抚群众。(三)司法实践中打击面过宽与保守解释的紧迫性司法实践中,打击面过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以笔者所在地区办理此类案件的实践为例,在民间借贷中介公司中,除了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管外,对具体招揽客户的业务员,其中吸收资金金额较大的也被认为是共犯,受到了刑事追诉。虽然司法机关也会认为将这些挣工资、有少量提成的打工者作为犯罪处理不合情理,但是在缺乏教义学化的对构成要件进行限制性解释的方法论存在的前提下,纯粹从共犯理论和单位犯罪理论出发,这些业务员构成犯罪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运用实质解释论出罪吗?抱歉,可能很多司法官员还不知道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之争。试图将其不作犯罪处理的努力,可能的规范化的途径是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但是这种类似于对“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者“可罚的违法性”的定量因素进行论证的过程,主观臆断色彩比较浓厚,必然达不到令人信服的程度。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制解释,对其构成要件范围进行适当修正,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上述“案例2”中,正是由于遵循《暂行办法》的规定,对网络P2P平台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限制——加入了自融自用、形成资金池或者自己担保等选择性的构罪要件要素,乙公司因为对上述选择限制性的构成要件要素缺乏主观明知,从而不构成犯罪。在同一公司内区分共犯的场合也是如此。如果将上述内容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要求对其的主观明知,则公司核心管理层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就可以因为缺乏主观明知而得以洗脱罪名,因为他们不可能接触到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项目的真实或虚假、担保公司与中介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等秘密。反之,在当前的情况下,上述内容不作为实体民间金融领域的限制内容,因此只要行为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四个条件”有认识,[25]就可以构成犯罪。而基本上,可能公司里面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扫地的、守门的——都知道本公司非银行而在进行资金中介服务。这就在理论上给予了本罪不当扩张打击共犯的范围以极大的空间。因此,从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面的角度看,也应当对其进行限制解释。 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保守解释的路径(一)保守解释的基本思路保守解释要求对犯罪构成条件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保守的、限缩的解释。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制解释的方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将“存款”限制解释为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主要是贷款)的资金。其中又区分为将吸收资金的用途限制为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和将存款的使用目的限制为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两个不同观点。[26]二是将吸收资金的手段加入欺诈和高风险要素。[27]对这两种方式,学者一般的主张是同时并举,即一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才能以犯罪论处。如姜涛教授认为,将存款解释为以贷出为目的的资金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形式要求,而欺诈和高风险是其实质要求。[28]但是笔者不赞同上述结论。理由一是按照这种解释,非贷出目的类的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就被完全排除在犯罪之外,这既是与司法现实完全相左的景象,同时也与更加具有相对合理性的《暂行办法》规定内容不一致——《暂行办法》认为将资金用于炒股等高风险用途也是违法。二是将吸收资金用于放贷的情形,还需要实质考察其有无造成高风险的结果,这同样既与司法实践景象相左,也与法规范不符——在这种构成要件类型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抽象危险犯,仅需有非吸行为(及贷款目的)即可推定危险发生,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在探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制解释路径之前,需要明确的是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性质以及网络P2P平台和实体民间金融中介机构的性质。因为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后盾法”,必须与作为其前提的民事、行政法律具有内在体系的协调性。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行政犯,在被刑法所规制之前,还有其他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应当一并加以研究,以得出妥当结论。在此值得借鉴的是学者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划分的分析范式。[29]理论研究认为,直接融资是资金需求者直接向多个资金供给者要求提供资金,采取的形式是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法律一般通过证券法予以调整。间接融资是资金供给方不是直接将资金交给资金需求方,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将资金交给金融中介机构,后者再将资金交给资金需求方。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业监管方式进行监管。笔者所关注的企业为生产经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性质,则游走在上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从实质上理解,这种借贷属于融资活动,并且是直接融资;但是从形式上理解,由于其中一般介入了民间金融中介机构或P2P平台,又具有一定的间接融资的性质。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融资既不是证券法所调整的股票、债券等形式,又不属于商业银行法所调整的存贷款形式,而只能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而关于P2P平台的性质,虽然《暂行办法》由银监会等单位制定,但是并不表明认为P2P平台就是属于金融机构、P2P借贷行为就属于金融活动。相反,《暂行办法》规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等内容正是要求其不得从事由金融机构专属的金融活动。这不是立法的创新性规定,而是对本来应有之义的重申与强调,类似于法律规定上的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而投资理财、理财咨询公司等民间金融中介机构,则根本不由银行业或金融主管部门进行监管,而是由工商管理部门作为一般公司进行管理,其性质也不属于金融机构,从事的也就不应当属于金融业务而是一般居间中介业务。所以,笔者认为,对上述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其限制解释的前提是要区分不同种类的行为在“前刑法阶段”分别应当由民法、证券法调整还是银行法调整,分别分析不同“前刑法”规制下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构成要件类型,进而对其入罪构成要件加以教义学化,最终实现限制解释的目的。但是其中涉及证券法规制的相关罪名是独立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外的擅自发行股票罪等,本文不予讨论。而被民法和银行法所规制的两类行为均可能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分别予以讨论。结合前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金融管理秩序或者公众资金的安全性——的分析,笔者在此已经能够清晰的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分为三类:一类是违反民法,采取欺骗等方式吸收不特定社会公众资金,使该资金陷入不安全状态的行为;一类是违反商业银行法,以虚构项目、自己融资、形成资金池等方式吸收资金用于发放贷款,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三是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监管法,网贷平台未尽审查义务,使该资金陷入不安全状态的行为。显而易见,笔者这里所主张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制解释的具体方法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看似并无突破——也是对“存款”的限缩和加入欺诈手段,但是,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类型划分为三类,分别确定不同的要素,进而对其进行限制解释的思路还是一种新的解释立场和方法。(二)基于民法基础上的限制路径——增加“欺骗手段”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这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类型的情形为:行为人公开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给予利息回报,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非贷款类活动,但是对集资参与人使用了欺骗手段,使所吸收资金处于高度的不安全状态之中。企业为生产经营进行民间借贷的行为,即使通过了投资理财公司作为中介,本质上还是直接融资。因为在这类型的融资中,企业和借款人直接签订借款合同,资金直接从借款人账户打到企业账户,中介机构只起到牵线搭桥、居间介绍作用。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这种借贷属于民法上的借贷关系。在这种受民事法所规制的借贷关系当中,如果企业和中介机构在宣传、展示时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因为生产经营亏损而无法还款的,只成立普通的民事违约;而如果提供了虚假资料、进行了虚假宣传,比如提供虚假的担保、保证、虚假企业资产损益表、虚假的购销合同等,骗取借款人的信任的,则属于民事欺诈,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前者本质上还是属于合同行为当中的意思自治下的选择,法律也不惩罚这种意思自治,而仅仅根据结果来进行民事责任判断,因此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但是民事欺诈则具有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的基础。[30]所以这两种情形下的法律性质是不同的。刑法上的刑事责任,也应当建立在民法上违法的前提下。在民法上都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刑法上的刑事违法。微观层面上,每一个借贷合同合法的前提下,几十个合法的借贷合同合并起来评价就具有刑事违法?这从逻辑上也无法推论出来。所以,结论是刑法评价只能在具有欺诈的民事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具有欺诈的借贷行为如果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一种条件是借款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时,民事欺诈会升格到诈骗类犯罪;另一种条件则是向多个不特定社会公众借贷的情形,多个民事违法汇集在一起,由量变到质变,达到《合同法》要求的“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刑法所要求的“严重的法益侵害”的程度,这种情形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所得出的结论合乎逻辑。并且,在加入了欺骗手段的民事违法行为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涉嫌诈骗犯罪的可能性。从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可以说是所有罪名中证据要求最高、最难以达到证明标准的构成要件要素。笔者认为,从“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证明”的前提出发,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集资诈骗罪的“替补罪名”进行适用,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31]但是这种替补适用的情形,前提是集资诈骗的客观方面具备,也就是有欺骗手段。所以,从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集资诈骗罪替补罪名适用的角度出发论证,也要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中加入欺骗手段要素。落脚到《暂行办法》上来,加入欺骗手段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暂行办法》的规定相一致。《暂行办法》规定的借款人的禁止行为中,明确规定“欺诈借款”外,“重复融资”也相当于欺诈。所以“欺骗手段”的加入,也能够从解释论的角度达到与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协调性。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欺骗手段”的具体内涵如何界定?是与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中明确列举的诈骗手段相一致还是范围更加宽泛?具体地看,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中列举的诈骗手段属于较为严重的欺骗手段,将会使相对人产生较为严重的认识错误,使骗取的资金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的状态之中,如虚假担保、虚假证明文件、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单位等。与之相对的,《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的骗取贷款罪则只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一种形式化的解释会认为,两种立法规定的不同意味着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比上述列举式的诈骗手段宽泛,所以公司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流水、业务量等虚假均可以认为是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手段。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并不意味着欺骗手段解释上的差别性。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之所以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是为了强调这几种严重的欺骗手段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作用,符合这几种欺骗手段的行为方式,一般能够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情况是:行为符合这些列明的欺骗手段,仍然不能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使用了虚假的担保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骗取的贷款完全投入了生产经营,但是经营不善导致不能归还的,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构成贷款诈骗罪。这种情况下,由于银行实际受损,则可以以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相反,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制作了虚假流水、账目,但是担保真实,骗取了银行贷款,即使不能还款,银行也能从担保受偿的,则不宜以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32]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考虑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的思路可以反映出其实对欺骗手段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笔者的结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加入的“欺骗手段”要素,应当与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中列举的严重的欺骗手段相一致,只有使相对人产生较为严重的认识错误,使骗取的资金处于较为严重的不安全的状态之中的欺骗手段才具有构成要件上的意义。(三)基于商业银行法基础上的限制路径——增加用途或目的的限制这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类型的情形为:行为人公开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给予利息回报,将资金用于贷款。禁止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和P2P网贷平台涉足商业银行法规制的金融领域是《指导意见》、《暂行办法》等共同的思想。借款人不得涉足该领域更是不言而喻。《指导意见》规定“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暂行办法》在增信服务、非法集资之外,进一步增加了“不得设立资金池”的原则(第3条);并规定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13项禁止行为(第10条),其中归集出借人的资金、发放贷款、将融资项目的期限进行拆分;第12条规定“不得用于出借等其他目的”。上述几条规定的内容,通过实质解释,其实都指向一个意思:不得涉足银行法规范的、只能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专门实施的吸收资金并放贷活动。由此可见,在网络借贷领域,中介机构和借款人不得将借用资金用于金融用途已经有法可依。当然,在实体金融领域,借款人不得从事上述活动也是同样有法可依的。但是不同的是,互联网领域,《暂行办法》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列明了违法之后,吸收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情形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而实体金融领域则仍然无法可依(《解释》没有此规定内容)。所以,笔者认为在资金用途上加上这一限制之后,在犯罪的门槛上正好借鉴了《暂行办法》的内容,实现了网上网下一把尺的合理性。从理论上看,学者早已论证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正本清源之道——从词源学上理解,“存款”不等于资金,存款是为了贷出牟利的资金。[33]因此,将资金加入贷款用途或者目的不是毫无根据的限制解释,而是还原该罪的本来面目。但是,一则从《暂行办法》的内容上看,禁止性的资金用途或者目的包括但是不限于贷款,还包括炒股、信托等等其他领域;二则从司法实践上看,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也常常被认为是犯罪(并且不一定是错案或者不合理);三则结合笔者前一部分论述的“吸收资金+欺骗手段型”的构成要件方式,将存款解释为银行专属的存贷款中的存款这种文义解释的方法已然不符合实际了。因此,笔者认为,以“存款”的原意为基础的解释方法不成立,但是可以借鉴其“加入贷款用途或者目的”的论证过程,将资金用途或者目的限制为:不得用于出借、炒股等金融、证券业务或以其为目的。而对于学者存在分歧的用途还是目的的问题,笔者认为二者居其一均可,没有大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吸收资金+欺骗手段型”和“吸收资金+特定目的或用途型”是两个选择性的、并行不悖的构成要件类型。(四)“未尽审查义务”作为限制性的构成要件的加入《暂行办法》中明确了P2P网贷平台对于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格条件、信息的真实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进行必要审核的义务,并规定P2P网贷平台未尽审查义务时构成违法。笔者认为对于实体的金融公司来说,同样应当将进行必要的审查义务作为强制性要求,也就是说将“未尽审查义务”将作为限制性构成要件加入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中,以达到对该罪进行限制解释的目的。那么这里的审查指的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审查的合理界限又在哪里呢?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要求P2P网贷平台应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格条件、信息的真实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等进行实质审查,同时应当适当限制这种实质审查的合理界限。其一,实质审查的必要性。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在居间借款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出借人对于借款人的了解往往仅仅局限于中介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情况介绍以及借款人身份证、户口薄、不动产产权证等证件的复印件,根本无法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时如果中介公司也仅仅对借款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那么借款人很容易就能够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蒙混过关,出借人的资金安全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通过法律来将我们所预见的风险最小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利益,同时在社会控制中要能够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予满足。[34]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仅仅是形式审查,那么法律规定的目的就难以实现,《暂行办法》如此规定就是要通过审查成本相对较低的P2P网贷平台,对出借人的信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借此最大程度地降低出借资金的风险。这点对于实体金融中介公司来说应当同样重要,实质审查将大大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减少非法集资事件发生的几率。其二,实质审查的合理界限。当然,不论何种审查方式也只能是降低资金的风险,不可能完全将风险排除。不管是P2P网贷平台还是实体金融中介公司,其本质都只是起到居间介绍作用,借款本身肯定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出借人在借出资金时就应当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我们不可能要求中介公司不顾成本地去将风险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其运营成本过高而不利于民间金融行业的发展。因此在要求中介公司进行实质审查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合理的界限。对于个人借款人,金融公司应当通过银行来审查借款人的个人收入是否属实,同时对于个人的车、房等财产,应当核实无有抵押登记或者存在抵押时其价值能否覆盖全部债务。对于以公司名义进行借款的情况,平台应当对公司或其融资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近几年的经营状况、负债状况、资产抵押情况,并对公司或项目的未来发展前景做出客观的评估。 On the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to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Focus on the Referenceof <<>InterimMeasures of Business Activity Management for Internet Loan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Wei Dong; Tian XinRui Abstract: The behavior which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had been confirmed as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 by judicialinterpretation and effective judgment for many years. But the which put forward recently specifies that the same type behavior is not allviolation of law on the internet financial field, this result in disunity criterionof constituting to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 (binarystandards). When we censor our national financial polic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of financial criminal policy, it is essential to do some conservative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t this moment. The behavior which absorbsfunds from nonspecific public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public deposits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aving the elements of “for loans”、 “deception” or “nosupervision”. Thus, the type of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n objective aspectsto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 should be defined into threetypes: one is “absorb public funds + for loans”, this type assaults the legalinteres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rder; the other one is “absorb public funds +deception”, this type assaults the legal interest of public fund security;thethird one is “absorb public funds + no supervision”. To complete the typerestriction for these three behaviors, could be actualized by conservativeinterpret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keeping a coincident standard of criminal constitution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Keywords: internet finance;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interpretation to criminal law*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刑法解释原理与实证问题研究”(12AFX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魏东,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馨睿,男,四川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副处长。[1] 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2]根据百度,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其中,P2P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也属于互联网金融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广义上的金融的概念,将各种类型的融资、借贷活动均包括其中。而传统的狭义的金融是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基本是属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专属活动。本文一般将在广义的概念上使用金融一词,有时将民间借贷、网络借贷与民间金融、网络金融混同使用。[3]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2015年P2P网贷行业年报简报》,http://www.wdzj.com/news/baogao/25548.html,2016年8月18日访问。[4]由于笔者所引用的是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案件尚在诉讼过程中,因此不具实名。案例二亦同。[5]参见魏东、白宗钊主编:《非法集资犯罪司法审判与刑法解释》,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6]在笔者写作此文过程中,2016年8月17日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颁布(银监会令〔2016〕1号)。[7]有实证研究者研究了13例P2P网贷平台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发现其中4例资金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及归还债务,但仍然被判有罪。但是该判例全部是截至2015年11月之前的判例,《暂行办法》出台之后是否有此类判例未知。参见李永升、胡冬阳《P2P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8]参见郑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融资》,载《特区经济》2008年第5期。[9]根据《2015年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企业家犯罪中排名第一的罪名。数据来源:http://news.sina.com.cn/o/2016-04-13/doc-ifxrcuyk2809327.shtml,2016年8月18日访问。[10]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暂行办法》是行政部门规章,不是直接认定罪与非罪的刑事法律规范或者司法解释,理论上与《解释》不直接冲突,甚至刑事司法可以不理会《暂行办法》的内容,但是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暂行办法》当然可以被作为刑法解释的理由来源,并且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必须考虑刑事司法、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一致,特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行政犯,不可能在行政不违法的基础上成立刑事违法。[11]何志、黄砚丽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精释精解》,第1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12]数据来源:网贷之家《2015年P2P网贷行业年报简报》,http://www.wdzj.com/news/baogao/25548.html,2016年8月18日访问。[13]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我省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川高法(2015)414号。[1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第687页;刘宪权:《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谢望原、张开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15]陈金钊:《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16]刘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与限缩》,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17]王韬、李孟娣:《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6期。[18]【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1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6页。[20]姜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21]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22]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23]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24]魏东:《刑法理性与解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25]其中“非法性”条件根据违法性认识不要论的观点,其实不要求有认识,实践中也基本不考察。[2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第687页;姜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谢望原、张开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27]姜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28]姜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29]彭冰:《非法集资活动规制研究》,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30]《民法通则》将欺诈认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合同法》对此予以修正,认为欺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如果欺诈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的,属于无效合同。[31]类似的情形有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被认为是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困难情况下的替补罪名。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任安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的说明》[32]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中的三个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33]王韬、李孟娣:《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6期。[34]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