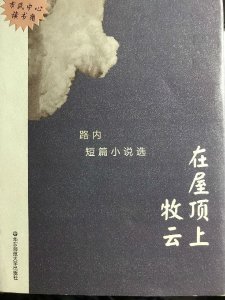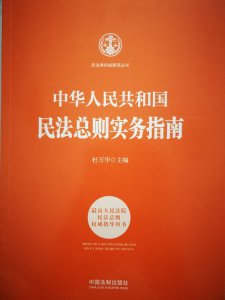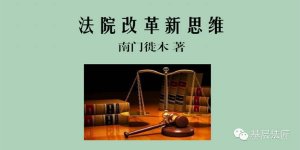张礼洪:民法典的历史和功能——兼评《民法总则》
来源:碧水蓝天 作者:碧水蓝天 发布时间:2017-06-15
摘要:环境民法 民法典 功能 历史 民法总则 张礼洪:民法典的历史和功能——兼评《民法总则》(张礼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2017-06-12 《政治与法律》 首先感谢会议组织者,给我安排这个机会,我是作为民法的学者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主要是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法典化的
|
环境民法 民法典 功能 历史 民法总则 张礼洪:民法典的历史和功能——兼评《民法总则》(张礼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2017-06-12 《政治与法律》 首先感谢会议组织者,给我安排这个机会,我是作为民法的学者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主要是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法典化的一些历史经验和它的功能。为什么谈这个主题?因为现在环境法,有人提出环境法要搞一个环境法典,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有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法律规定,那就是法律漏洞,进行需要国家立法来填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正如英美法法谚所说“More laws, more offenders (“法律制定地越多,越是被人违反”)。立法不应当是解决法律漏洞的主要手段,以下具体阐述一下这个理由。首先说跟主题有关,但不完全跟主题密切联系的几句话。法学的研究,首先要看历史,西赛罗说过historia magistra vita est(“历史是生活的老师”)。法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全部都应以历史为基础。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相当于数学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谈法律的问题不讨论历史,一定是缺乏深度的。第二点,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我们看的是物、环境,实际上环境、自然资源,虽然是表现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但本质上都是人的关系的媒介,反映的都是法律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环境就只不过是法律关系的一个媒介体。第三点,法律最关键就是要研究法律怎么适用(law in action),而不是看法律怎么写的(Law in books)。今天上午有同事谈到了政府索赔权,无从适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里面,据我所知,通过个人打单纯的民事官司,请求环境侵权,侵权方已经成功获得赔偿的案件极少。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或者是有关的集团,环保组织主导下而完成,国家政府在宪法上有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这个义务就包括提供清洁的,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环境的义务。环境法是一个公法私法混合交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从实际层面并不是很大的民事责任的实际适用的范围,主要是行政责任为主。第四个是法是社会现象,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的时候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的问题和历史发展轨迹。下面结合民法法典化的历史、民法典的功能谈《民法总则》的得失。一、民法法典化的历史现在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法典化,法典化(codification)这个词是著名英国法学家边伈第一次提出的。在他看来,法典与普通立法不一样,它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完整性,它的法条是完整的,它涵盖一个部门法的全部内容。第二,它是所规定的法条内部不存在裂痕,概念是体系化的。第三个是一个国家部门法渊源的核心(法源中心主义)。民法典替代民事部门法里面其他的所有规范。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称为法典化,这是关于法典化最经典的认识,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认识。以这个标准来判断,1794年就有普鲁士联邦的民法典,但其条文不是体系化的,因此只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达到这个标准,后来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在条文体系化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两部法典被认为是近现代民法法典化的模本。但是,从法学史上考察,“法典(codex)”一词,在拉丁文中原意指树干,被用来指用树干做成的单片的书牍,与可以卷起来的书卷(Volumen)相对应。其核心含义是公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文法律汇编,本身并没有要求所包含的规范逻辑上的体系化。法典是公开的,书卷却是秘密的,记载的是可以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因此,法典的第一大特点是公开性。为什么要公开法典化呢?因为法律最开始就是取决于宗教,一部分人把法律玩的很神秘,法律规则掌握在祭司集团手中,通过法律的公开之后,法典化以后就脱离了神秘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讲,公元前451年《十二铜表法》以铜表方式把法律规范制成铜表放在公共广场也是法典化,叫做成文法。但是,法典还必须具有规范的系统性,即对一个部门法的全部规范,通过概念体系进行整合。世界历史巨擘,汤因比,在世界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非常敏锐地发现,体系化意义上的最早的法典化起源于公元前二世纪,即罗马法学家尤里安在阿德良皇帝支持下,制定的永久告示集(edictum perpetuum)。尤里安把裁判官对同类案件经常性做出的告示整理成集,也就是把对同一法律问题实践中形成的相同解决方案进行整合,这是法典化。法典的法源中心主义,作为民法典的第三个特点出现得较晚。法源的中心主义是公元6世纪,即529年到534年尤士丁尼皇帝主持下编纂的《民法大全》最先完成的。《民法大全》颁布后,以往的所有私法规范全部失效,以后统统适用《民法大全》,从法源中心意义上讲,《民法大全》是民法典,它规定的法律规范有一定的系统化,但是,更多的是法律文件的汇编,在形式上,远未达到《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体系化,所以《民法大全》也还不是今天很多人所指的法典化。就尤士丁尼皇帝编纂的《民法大全》而言,我想特别注意下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其的评述。汤因比指出:“在法律标准化接近法律统一的大一统国家,帝国当局往往进一步编纂统一的帝国法典... ...编纂法典的高峰往往出现在社会灾难的前夕,此时法学成就的高峰早已成为过去,立法者在与难以驾驭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地节节败退。”《民法大全》就是在东罗马帝国日薄西山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在其编纂完后不久,东罗马帝国皇帝就被永远赶出了意大利半岛。汤因比的这一论断也为中国历史所证实:中国晚清时期,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颁布后的第二年,清皇朝就灭亡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颁布后不久,就被驱赶到了台湾。汤因比的这一论断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法学规范的产生并不是产生于法律立法者本身,因为法典化是通过立法机构通过行使立法权制定规范,立法。私法体系的法源多样性,立法、习惯、判例、学说,绝对不可以把立法作为法律产生的唯一来源。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并不得到很大的重视。我们长期以来,中华法系中,法律就是有规范的成文的东西,梁启超1904年撰写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着重研究的是中国成文法律规范,主要涉及刑法和行政法。而中国古代的私法规范主要是习惯法。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老百姓的婚姻嫁娶等民事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习惯法来调整的。总结起来,从民法法典化的历史看,民法典的成文化(也就是公开化),体系化和法源中心主义的三个特点是渐进形成的。从较宽的意义上理解,成文化和体系化,法源中心主义其中任何一个特点结合,都可以称为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第一个融合上述三个全部特点的民法典,也就是现代意义的民法典。二、民法典的功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它起到什么样的功能?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为基础,以民法典作为排他性私法渊源为立法理念,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追求体系化。从其社会功能来看,它起到保障市民社会对抗政治权力的功能。政治人物变来变去,老百姓的买卖交易,婚姻嫁娶,财产继承规则应当是稳定的,这就需要民法来规范和调整,通过颁布民法典来维护私法自治。正如,法国民法泰斗Carbonier所说,法国大革命后,“就法国瞬息万变的多种政治体制而言,实际上,法国民法典才是法国真正的宪法。”《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还解决了习惯法多变性,法律稳定性和可知行的问题,起了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作用。法国民法典对世界影响很大,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采用,包括意大利和比利时。萨维尼历史法学派对法国民法典的评价非常低。他认为法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民族意志。在萨维尼看来,没有必要搞什么民法典,推动法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是来自民族内部的、无声无息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作用的习惯。虽然法律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科学理性。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性,萨维尼称之法的完备性。它如同几何学上的术语,三角形之中从两条边及其夹角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关于三角形的一切情况。在我们的法中的每一个部分中都存在一些要素,可以从中推论其他部分。萨维尼看来,通过科学思考对习惯提成就形成了法律规范,没有必要不可能将这些规范都成文化,也就是说民法典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于民法典的局限性,日本著名民法学者穗积陈重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法典化有以下几个大弊端:第一、法典不能伴随社会的进步;第二法典不能包含法之全部;第三,法典不能终止单行法;第四法典不能终止判例的适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显然与萨维尼的思想相悖,完全是理性主义的立法的产物。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此外,还反映了私法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奉行的不再是私法自治,而是要实现社会正义,限制合同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自己责任。我们特别要注意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是第一部规定社会经济权利的宪法,它是近代宪法的开端,它的颁布也使得传统的民法典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魏玛宪法》颁布后,成文法律规范越发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协商妥协的产物。由于短期议会的频繁出现,每一个执政党上台都为其一党之私利颁布法令,很多这方面的法律都是民事法律,老百姓生活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在已经完成民法法典化的国家,民法典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德国著名民法学者Wieacker在1954年发表了《民法典的危机》一文,提出了民法典的危机,后来在1974年出版的名著《工业社会和私法秩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民法典危机的三个基本原因是:第一,民法典不再是确定和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法律基础;第二,国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自由竞争向社会正义转化;第三,立法的活动直接表现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协商交易的结果,而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延续对传统民法典的危机的认识和批判,诸多欧洲法学家都对传统民法典的危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德国Fiedrich Kuebler教授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法典化将导致权力集中,导致专制,不适合于多元文化社会。在比较法领域,意大利著名学者Monateri也持这一观点。在这位学者看来,英美法的判例法体系,相比于罗马法的成文法体系,更体现民主自由。罗马法学家所造就的法典化传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禁锢法学思维。当然最出名的是伊尔蒂在1978年的民法典的分解时代。他提出法典化已经处于边缘的状态,不再作为私法法源的中心地位,在已经完成法典化的国家,民法典处于被分解的状态。他的基本观点和理由是:首先,在国家对于经济政策不断的干预以后,成文法国家中,法官也不断逐渐造法,在司法判例中产生大量规范,不断取代了民法典,在民事领域中发生重要的功能。其次,不断颁布的民事特别法形成一个内部的微观民事规范系统,适用自身独特的解释规则和体系,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婚姻法,商事特别法,如保险法等。这些民商事特别法优先于民法典得到适用。最后,游离于民法典之外的大量不断出现的民事特别法,灵活多样,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结果。以往的“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就是法律”变成“法律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必然导致民法规范的碎片化,一部民法典已经无法解决民法规范碎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宪法来解决。这种情况下,伊尔第教授认为出现的新型的车幅状民法立法模式。在有民法典的国家,民法典作为车轴还是整个国家私法体系的中心。民法典解决的是宪法和单行法之间的连接器和减震器,更多的是规范媒介条款和一般性规定。民事特别法是车轮,承载着大量实际得到运用的私法规范。司法判例就是连接车轴和车轮的车幅条。民法这架马车驾驭者主要是立法者。当然,还包括法学家和法官。这种新兴的民法典的代表主要是1992年《荷兰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抛弃了传统大陆法国家的体系化追求,整体上可分为人法和财产法,完全抛弃了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结构,也没有采用法国的人、物、财产取得方法的三篇制结构。人法部分由第一和第二编构成,涉及自然人法、家庭法和法人法。财产法部分又可分为总则部分和其他部分。总则包括第三编(财产法总则)和第四编(继承法)。第五编物权、第六编债法总则、第七编典型合同和第八编运输法构成其他部分。目前还在考虑将知识产权编为第九编。 类似的情况还有俄罗斯民法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芬兰、瑞典的单行法为主的立法模式。这些新型的民法立法模式和我国的太阳系立法模式一样,都反映出英美法和大陆法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从欧盟的民法典制定的情况,以冯·巴尔为主导的一些欧洲学者,试图搞一个欧盟统一的民法典,为此费尽千辛万苦制定了一个学者型的示范的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Commona Frame of Reference of European Private Law),但是这个计划2013年就已经彻底流产。这个草案不仅内部存在很多问题,而且由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巨大,欧盟统一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被认为不可行。有一点需特别指出,从民法典功能的历史变迁来看,无论民法典遇到什么危机,民法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基本公民权利,保护意思自治的基本功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民事领域,“法无禁止均自由”的基本理念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特点。这也符合最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以制作政府机构负面清单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在公法领域,和民法完全不同,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均不得作为”。三、《民法总则》的简要评析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可以称为太阳系模式。也就是说, 《民法通则》(和新近出台的《民法总则》)构成民法规范的核心,形成太阳;大量民商事单行法构成行星,司法解释构成慧星,包含在公法中的调整私法关系的公法规范构成小行星。现有的这个民事立法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修改的成本低,在世界立法中独树一帜,效果也不错,我认为作为一种立法模式,完全没有必要改变它,要做的只是对各类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进行梳理。作为未来民法典的总则而颁布的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 实际上完全在模仿西方成文法国家的传统的民事立法体系,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谈到的传统民法典立法模式出现危机。一旦制定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的民法典,中国现有的太阳系民事立法体系的实用主义优势和灵活性将丧失,大大提高未来修改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成本,西方国家民法法典化后出现的问题将跌重而至。汤因比所说的法典化导致国家政权衰弱的历史教训完全可能再现。这里,我简要谈《民法总则》非常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把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混同,另一个是立法技术的粗糙和逻辑混乱。第一,《民法总则》没有脱离旧中国把道德和法律混在一起的立法思路。中国历史上,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道德经常被法律化,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不分,特别是私法领域。遗憾的是,这一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立法观念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民法总则》中。比如,《民法总则》第1条,把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写入立法指导思想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毫无疑问,这些价值观应该得到大力宣传和弘扬,但是,这些价值观都属于道德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没有必要作为法律规范写在民法典里面。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这些价值观反映都是高于最低底线的道德要求。另外,《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很多学者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绿色条款”,保护环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原则的新突破。这部民法典也因为这个条款被称为“绿色民法典”。其实,这是一种过度的解释和不恰当的理解。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考察,第9条完全是一个宣誓性的条款,它反映的是道德规范。我认为该条款完全不具备法律实际操作性。理由有三个方面。首先,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一种道德要求,正因为是一种道德要求,违反这一规范,并不一定发生法律效果,为此,该条款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必须保护环境,但是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没有保护环境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根据这个条款,认为一切不节约资源,不保护环境的民事行为都无效,这显然是不成立的。不然的话,淘宝购物的快递包装这么多,浪费这么多资源,这些合同都无效。即便因没有保护环境,民事主体要承担法律后果,除非发生环境侵权,大多数都是公法来规定,发生公法效果。比如,我不在家的时候没有关电灯,浪费能源,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要求我支付更高额的电费,但是这不应当由民事法律规定的,是节能方面的行政法规定的,这是公法规范,不可能规定在民法典中。其次,环境保护属于环境权,应该放在宪法中,放入比民法更高阶位的法律中,才更体现其价值。把环境保护作为民事义务规定在民法典中,违反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属性,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是不成立的,在逻辑上说不通,是对民法体系的严重违反。环境保护需要公法私法手段并用,更多涉及的是政策考量,就像今天早上郭延军教授所说,环保责任主要是国家,国家和政府是主要的责任者。全世界大规模环境侵权都是国家机关冲在前面,用国家的税款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责任者有义务保护生活在其国土领域内的公民安全。这不是说环保应当完全由公法来处理,民商法就不重要。在环境侵权造成民事责任的时候,民事立法中应当作出详尽的具体规定,比如环境侵权的举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康权的侵犯,所有权保护等方面。没有必要规定一个原则性的第9条。最后,制定民法典的根本目的是使得民事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变得更有可预见性,但是第9条造成完全和这个立法目的相悖。保护环境是道德义务,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是任何时候都会产生法律后果,但是《民法总则》第9条的规定,赋予了法官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权力滥用。 在什么情况下法官可以启动这个条款来认定民事主体没有节能环保的民事责任,需要以后的司法解释。在民法领域,这一条款内容含糊,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实施过程中,好比达摩克利斯之剑,可以随时被法官启动确定民事行为无效或者让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第二,《民法总则》中存在大量违背技术中立和理性主义,逻辑混乱,用语含糊的条款。我们在前面通过对民法法典化的历史的回顾,可以清楚看到民法典的制定是法律科学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奉行技术中立是全世界所有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民法总则》的颁布情况来看,这个立法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存在大量逻辑混乱,用语含糊的条款。比如,在关于“法人”的第三章中,以法人是否营利为目的,把法人区别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这个区分是周延的,法人要么营利,要么不营利。但是,随后第96条又规定了特别法人,并把它们限定在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这几类。按照逻辑,这类特别法人,这些特别法人既可以营利也可不营利,如果营利就是营利法人,不营利就是非营利法人,分别适用营利和非营利法人的规定就可以了。从逻辑上看,特别法人作为第三类法人形态,其分类标准和前面两类法人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是这个标准是说明,特殊法人和一般法人的分类标准是什么?没有说明清楚。这三种法人形态的区分存在逻辑混乱。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一律平等,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在人格权保护方面也是如此。侵犯任何死者的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益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显然包括英雄烈士在内。这个条款中,写入“英雄烈士”表面上看是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实际上,还会给人造成只有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才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误读。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意思。从中文语法上分析,这个条款的规定造成了不应当出现的歧义,反映出立法技术的粗糙。再比如, 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这句话中文念起来都明显语句不同,非常拗口,表达的意思也非常不清楚,没有说明清楚哪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有效,判断它们有效的标准是什么。由于没有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可有效的构成要件,这个条款就是废话一句。此外,《民法总则》规定了许多完全没有操作性,既不可以作为裁判性也不可以作为行为引导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条款。比如第13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的规定,第134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的规定。就民事法律行为而言,第143条关于其效力的规定,竟然没有考虑到把民事法律行为形式和条件期限的满足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要件,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世界各国的民法总则要么是对民法典分则规范的公因式提取、要么涉及民法一般原则和一般条款,或者要么涉及其他不适于在民法分则中规定的内容。民法总则的条款应当高度概括简洁。但是,从最近颁布的《民法总则》来看,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举例为证,第36条第2款所指的“有关组织”和第24条第3款的“有关组织”内容基本一致, 唯一区别第36条所指的“有关组织”多加了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抛开有关组织是否只包括上述机构不说(实际上,除这两个条款中列举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依法成立的保障限制性民事行为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公益机构都应当包括在内),从法条简洁的角度上看,第36条第2款只要直接援引第24条第3款的有关组织的规定就可。具体表述为:“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除了包括第24条第3款规定的有关组织外,还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而不是如同现行规定一样,36条把第24条中有关组织的内容重新抄一遍,不仅无端增加了法条的长度,而且还使得法条冗长拖沓。四.结论2017年3月15日颁布的《民法总则》的历史评价不会高。它是一个很粗糙的立法产物。《民法总则》的制定者没有清楚认识到民法的核心功能是维护意思自治,在当今社会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由于民事特别法的层出不穷,民法典应当是单行法和宪法的连接剂。我们原有的以《民法通则》为中心,民事单行法为补充的太阳系式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世界领先的民事立法模式,是贯彻我国改革开放后务实实用立法指导思想的结果。放弃我们本来就是先进的立法模式,去制定已经不断分崩离析的西方国家传统的民法典,是邯郸学步。汤因比关于制定法典是帝国衰落的前兆的结论,值得引起我们重视,重新认真审视已经开始的民法法典化。就环境权保护而言,环境保护更多的是政策考量和人权保护的问题,应该规定在宪法中而不是民法典中。而且节能环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写入民法典是不妥当的。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应该既要仰望天空,又要俯瞰大地,也就是说既要给立法者提供科学依据,考察立法者的意图,又要从老百姓的民事活动中,从民事习惯中吸取营养,从历史中,从民事习惯中吸取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萨维尼所说,只有习惯法才是法律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动力和源泉。就《民法总则》第9条而言,我完全赞同台湾学者苏永钦的主张:中国需要一个纯粹的民法!应当在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维护纯粹的民法。第9条把节能环保作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的原则,是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系统性破坏,这个条款污染了民法,玷污了我们的民法基本理念和精神。我们应该大胆对它说:“拒绝污染,保住健康”!谢谢大家! (本发言经张礼洪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