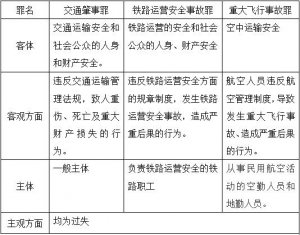梁漱溟:中西之间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6-12
摘要:梁漱溟:中西之间——《中国文化要义》席明纳发言 一 之前长点,现在我聊的时间短点。这个吧,我觉得席明纳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为本子啊,可以解释的东西多,往里边可以填充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吧!从里边可以找出想看到的,
|
梁漱溟:中西之间——《中国文化要义》席明纳发言 一 之前长点,现在我聊的时间短点。这个吧,我觉得席明纳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为本子啊,可以解释的东西多,往里边可以填充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吧!从里边可以找出想看到的,想读到的,想思考到的,基本上,各个方面都能够涉及到。刚才,2015级中文系刘慧玲学友,对《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进行了梳理,第四章的题目是——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慧玲学友梳理之后,学友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涉及到宗教、科学等领域,这正是我所喜悦的,如果说“席明纳”需要一个名称,我想到了“鹅湖之会”,1175年,在吕祖谦的倡议之下,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一座寺院——鹅湖寺,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会,争辩了三天三夜。鹅湖之会,闪烁的光芒,一直没有熄灭,薪火相传,今晚的“席明纳”,流淌着“鹅湖之会”的气息。所以,谢学友,欣喜不已。相对来说,思想的交锋得以产生,一大因缘,话题本身的深刻性,涉及到大本大源,就是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所引发的“话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常的交流和切磋,有时候,相对比较“致用”,不妨称之为“技术性话题”,比方怎么“考证”呀,怎么“考研”呀,怎么“考公务员”呀;有时候,相对不够“致用”,不妨称之为“人文性话题”,比方恋爱呀,交友呀,以至于宗教呀,信仰呀。宿舍卧谈会,两种话题都有,跟好朋友聊一聊看到的视频,电影,电视剧,其实,已经是一种“人文性话题”,但,聊看过的一本书,怕已经不是很多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卧谈会所聊的话题,一枝一叶总关情,关涉家国天下,关涉大本大源,宿舍卧谈会,不聊什么,什么是宿舍卧谈会的禁忌?不要小看了这些“当身历史”,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字天书”,需要破解。这个世界,既需要“有用之用”,也需要“无用之用”。关涉到大本大源的问题,不会是那么“致用”,为什么说不是那么“致用”啊,就是说,不是那么“有用之用”。谢学友在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明导论》、《西方文明导论》,面向全校开设的任选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往往是第一节课,开宗明义,这门课,既不能拔云见雾,也不能指点迷津,只是谢学友与学友们,一起跋涉的一段足迹,一点记录,比不了有的老师,既有意义,又有作用,总而言之,谢学友眼中,所上的课程,没有一门,是“有用”的。有的学友,不免疑问:没有一门是“有用”的,谢学友,为何乐此不疲?咱们的“席明纳”,何尝不是如此!内心充斥着“有用”,那么,无论如何,上课还能获得一定的分数,两周一次的“席明纳”,连最基本的“学分”功能都没有,岂不是“无用”的平方甚至N次幂,简直是“无用”到家了。尽管如此“无用”,每当谢学友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心中的“鹅湖”——牧星湖畔的中文系,进行两周一次的“席明纳”,有一丝甜蜜的感觉,在心头流淌。轴心时代的哲人,都是喜爱聊天的,中国的孔夫子,希腊的苏格拉底,莫不如此,对话是交流的最高境界。据说,有人开发柏拉图聊天软件,有点意思,看来柏拉图遇到了“知音”。这个世界,你看,有一个“有用之用”,有一个“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在近代发展为“科学”,发展为“技术”,在“有用之用”方面,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大异其趣。与物质世界构成的“有用之用”不同的是,由精神世界构成的“无用之用”,那就是什么啊?那是“宗教”,那是“伦理”,那是“价值”。如果说物质世界的面貌,是由大航海以后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带来的,那么,精神世界的面貌,则镌刻着文明史丰厚的土层,有些基本面,逐本溯源,要到轴心时代去寻觅了,比如宗教,比如信仰,比如伦理。人类文明史,古今是可以而且必须贯通的,古今一体,展示了精神世界的坚韧和执着。这世界上的“人”,首先不是“工具”,首先怎么样,首先得赋予“意义”,如果说“人”没有“意义”,“人”就没有脱离蒙昧。“人”之所以成“人”,在于“人”有“意义”,有“价值”,这个东西是什么啊,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种“有用之用”,而是一种“无用之用”。若说“有用之用”的话,蚂蚁都有“有用之用”,蜜蜂也有“有用之用”,蚂蚁和蜜蜂那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比人更有“集团性”,大家看是不?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上有隐士,有隐逸,就是说:不干活啦,“隐着”。有的是“大隐”,有的是“小隐”,是这样的吧!但是,蜜蜂的世界,蚂蚁的世界,生为蜜蜂,生为蚂蚁,能“隐”吗!能说我是“隐蚁”,我是“隐蜂”,那是不行的。到时候,担任什么职能,扮演什么角色,该怎么干活,就得怎么干活。生为“工蜂”,什么活都得干,能闲下来吗?哦,闲不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蜜蜂和蚂蚁的世界,严丝合缝,那么合乎科学规律。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没有“人”这样的智慧,无论是蜜蜂,还是蚂蚁,它没有发现,自身的那个意义。发现了那个自身的意义,那人就怎么样?有些人自以为看透了,裴海涛学友说,人没有看透,这种态度是可取的。为什么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科学”再发展,“技术”再进步,看不透的东西多了。看不透的东西,那怎么办?如果仅用“科学”来解释这个世界,那很多东西,就会怎么样啊,不符合“科学”,“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怎么样啊,很多东西,在“科学”发达之前,就一直存在,“科学”发达以后,似乎,依然拥有自己的地盘。在“科学家”看来,这没有道理呀!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大量存在。原因很简单,“科学”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所依托的世界文明史,往往是不讲“科学”道理的,也不按照“科学”道理存在,而是按照“科学”之外的道理存在,“科学”之外的道理,有些直接和“科学”对着干,“科学”还拿它没办法。这可怎么好?“科学家”只能在那里立志: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它存在,是这样的吧,很多东西,不按照“科学”道理的方式存在,令人头疼。呃,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的东西合理,既可能合乎正理,也可能合乎歪理。但是,黑格尔还说过,合理的就应该存在。黑格尔翻来覆去说这个事,实际上,很多东西啊,是一种多元共生,存在的东西,既有合乎正理的,也有合乎歪理的,多么奇妙的世界!不过,在不少学友看来,这个世界,简直不可思议,合乎正理的东西,都不一定存在,是无天理!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多元的,很多东西有着自身的限度。在以前,各种科目,人文,科学,艺术,美学,伦理,逻辑,发展低落的时候,宗教的边界就特别宽广了。后来,慢慢的宗教下面的学科,逐渐独立,想着分家。宗教有自身的限度,只不过,其它人文学科不发达,“寄生”在宗教里,这些学科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领地,自然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于,宗教慢慢的有自身的边界。大家都觉得这些学科,特别是“科学”,在近三百年中,一马当先,独领风骚,恍然间,科学的光芒,超过宗教了吧!这里,不妨给“科学”算一卦,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宗教,最多也就是与宗教旗鼓相当。谢学友,不是长“宗教”的志气,灭“科学”的威风。为什么啊,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大学里边,同样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纠葛。一个是“人文”,文史哲艺术,再一个是“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漫漫文明史,“科学”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这是晚近的事情,但,由于应用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翱翔于天地之间,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文化的“中心”学科,“技术至上”,既改变了现实社会,也改变了大学自身。“人文学科”,由于自身欠缺功利性,以至于沦落到“边缘”,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但,“人文学科”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人文学科”属于人类文明的“慢生活”,不必与“技术科学”争一日之短长,也不必“摆老资格”——想当年,“科学”还是个少年,“技术”还是“玩泥巴”的顽童,“人文”就已经有着丰富的积淀。支撑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这些“人文学科”的,实际上,是背后的那个“意义”,那个“意义”,某种程度上与“神”、“神圣性”相联系的,就是怎么样,关切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缠”着人们,人之所以成人啊,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们到底怎么来的。人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敬畏,有一个省思,省思到一定程度上,从文明史来“追”,“追”到最后,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往往要“追”到宗教,或者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佛教、犹太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但是,追溯中国文明史,历史上曾经有多多种宗教的身影和踪迹,不过,中国文明的源头,有着鲜明的文明性格,那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周孔教化”,周孔教化,这是一种伦理,以至于任继愈先生,要把周孔教化,当做一种宗教——儒教。这个世界,有“有用之用”,有“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纠结缠绕,建构了鲜活而丰富的文明史。“有用之用”往往追到“无用之用”,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用之用”主导着“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才是那个真正的“诺亚方舟”。遗憾地看到,很多文明被灌注了一种“一神教”,总想把复杂多样的世界,弄得整齐划一,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现在讲什么,动物啊,植物啊,微生物啊,那种多样性。其实,人文与此相匹配,依然具有多样性。实际上,人类文明,也是一种多样性啊。既然具有多样性,所以说不要轻易的,一分为二,而应该一分为三。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总以为,这个东西起来啦,那个东西就应该趴下。实际上,我们建构了,或者被建构了“非黑即白”的一种观念。哎,脑海之内,很多东西,都在“交战”,“打架”,表现在课堂,或者宿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省自我,“课堂”一度成为“教堂”,自己也成为某种教义的“布道士”。所以,马克斯·韦伯说,保持一种价值中立,大有道理。在研究或者教学中,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加以“斗争哲学”,驱之不散,现实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红卫兵”,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为什么老“打架”?略微思量,很多东西,其实“打架”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但是,遇到对立面,不仅生真气,还要批倒批臭。文革结束四十一年了,看待问题,没有提升到“一分为三”,还停留在“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是我对,就是你对,不是我错,就是你错。你我之间互相争论,只能有两种状态,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类人孩”或者“巨婴国”,大体是不错的。实际上,在两种情形之外,还可能有这种情形:你也不对,我也不对,或者说,你也对,我也对。为什么,都是盲人摸象。你说“大蒲扇”,我说“大柱子”,“大蒲扇”或者“大柱子”,谁对谁不对?若说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都是大象身子的一部分,是这种情况呗?若说不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没有摸到大象的全部。为什么“一分为三”,为什么中国古人要“一分为三”呢?怎么不“一分为二”呢?叩其两端而执其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太有道理哦。体会“一分为三”,执行“一分为三”,我的主张,反对我的主张,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极高明而道中庸。两种对立的主张之间,实际上怎么样啊,中间还有一部分。也许中间那部分颜色比较弱,以至于看不到。看不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的,人又不是全知全能。中间那部分看不到以后呢,就以为在那顶着牛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包括宗教与科学的因缘,顺便说一句,谢学友对科学史,也比较感兴趣,这是科学史一个永久的话题。“传教士”为什么发展了“科学”,宗教裁判所判处布鲁诺火刑,烧死的是布鲁诺,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代科学的星星之火,成为照耀整个世界的燎原之势。这就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因缘。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妙不可言。回眸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现中国“宗教”与“科学”,如影随形。中国的宗教与科学,依然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永久话题。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科学的滥觞,与墨子有着莫大的渊源。墨子是墨学的开创者,这个学派,其实,还是一个准宗教集团,墨子主张“非战”,“非攻”,希望让世界充满爱。难怪有人非要说墨子“祖籍”印度呢?墨子是否和释迦牟尼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徒发展了科学,祖冲之发展了数学,葛洪发展了医学和化学,不妨把视野从“科学”扩展到“人文”,王羲之发展了艺术,至于唐代的李白,发展了文学,有目共睹。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啊,太有意思啦。现在“科学”是“有用之用”,但,仅仅用“有用之用”,想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很长时间,“科学”在“宗教”的襁褓之中,“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科学”萌芽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社会生态中,“科学”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科学”自身不能认定“科学”,为什么啊,因为“科学家”那时候还没独立出来呢,还处于“业余”和“兼职”的状态。“科学家”得怎么样啊,“科学家”就得穿其他的马甲。哎,比如在欧洲,就得穿“传教士”的大袍子。在中国,叮了当啷那个武当山那个袍子。文明史很长时间,“科学”自己不能认证自己,它得怎么样,得通过外力。科学是现代世界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很晚的事,是后来的事儿,以前怎么样啊,是“神学”。科学是第一推动力,那么古代,第一推动力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啊?牛顿就说了,给这个世界找个支点,最后找到哪去了?找到神学去了。牛顿作为大科学家,竟然找到神学去了。历史课本说,牛顿给神学留下了地盘。那么大的科学家,还给神学留下地盘,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科学家的软弱性。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简单,太看不起神学,太看不起神学,总觉得“科学”和“神学”是势不两立的。宗教裁判所烧死了布鲁诺,这是铁的事实,但是,没被烧死的“布鲁诺”,还是多数,就是这些“教士”,发展了“科学”,这里边其实有个“共生”,文明是一种“共生”。 二 文明是一种“共生”,比方说西方某种程度上发展的这种“集团性”,与中国的一种非集团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就是一种“共生”,这要从那个地区的族群所处的生态,进行梳理和分析。梁漱溟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没有说,“集团性”或者“非集团性”,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哪一种文明样式,都是一部奋斗史,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如果有相似的生态,也许会走上一条道路,如果换一种生态,也许,西方走上“非集团性”的道路,中国走上“集团性”的道路。梁先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圆融”。依照赵元任先生所说,言有易,言无难。说中国有什么相对比较容易,说中国没什么相对比较难。中国社会生态,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说中国有什么,相对比较容易,此之谓“言有易”;说中国没什么,要慎重,哪一天,有条史料蹦出来,证明这种说法错了,岂不是前功尽弃,白忙活一场。比方说,说古代中国没专制,没独裁,慎重一点为好;反过来,说古代中国没自由,没民主,也不要斩钉截铁,还是慎重一点为好。赵元任先生的六字箴言——“言有易,言无难”,很是受用,实在高明。梁漱溟先生就下了一个断论,中国人欠缺集团生活,没有集团性。梁漱溟先生不欢迎廉价的掌声,所以,就不要轻易跟在梁漱溟先生后边,摇旗呐喊:梁先生说得好,梁先生说得妙!梁漱溟先生听到有人这么夸赞,也不一定多么高兴,因为,梁先生主张,表里如一,独立思考。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集团性,是动了一番脑筋,经过了一番思考的。梁先生说中国是一种家族本位,在梁先生看来,家族本位,距离“集团性”,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谢学友看来,中国是一种“非典型性”的“集团性”,相对来说,西方是一种“典型性”的“集团性”。中国“集团性”的“非典型性”,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集团性的层次不高,表现在家族本位;二,集团性的烈度不够。依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没有“集团性”,就会背离赵元任六字箴言,中国有集团性,但是,中国的“集团性”具有“非典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跟西方文明相比,中国表现在家族伦理这个方面,非常突出。也不能说,中国一点都没有“集团性”,不能那么说,也许不妨说,中国的“集团性”不够彻底,中国的“集团性”不够浓厚。这里提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中国本身,不要把中国看低了。朱维铮先生有一句话,音调未定的传统,大有道理。要从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国是衍生的,一直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里不妨反对一下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不是一直没有集团性,在易代之际,中国是有着“集团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有着很强的“集团性”。实际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就有“集团性”。晚清“礼法之辩”,劳乃宣先生,就曾从文明类型,阐发中国文明的性格。劳乃宣先生说,中原地区,属于农耕文明,家族是耕种的合适单位,所以发明“家法”;长城以北,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发明“军法”。从根本上来说,“集团性”本身属于能征善战的民族,如果世界充满爱,军事集团,就不会出现。无论游牧民族,还是航海民族,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想一想,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和充满着惊涛骇浪的大海,每个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要想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高度协同一致和同舟共济,在草原上和大海上,可不像农耕地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面对凶狠狡猾的狼群和变化无常的大海,农耕社会的理想,简直遥不可及。不能说所有航海的民族都是海盗,但,不妨说一句,航海民族一定程度上脱离不了海盗的嫌疑。黑尔格喜欢说,想起希腊,就有一种摇篮的感觉,希腊文明来自海上,这句话,大有深意。是否可以理解,希腊文明的丰厚的物质基础,来自于海上,这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于“自由贸易”,还有一部分,怕是就不大光彩了。欧洲文明是离不开海的,从地中海到大西洋,这就是一部欧洲文明扩张史。欧洲文明,从希腊到瑞典,从罗马到英国,挥之不去的,正是海盗的身影。就可以看,维京人活跃时期,北欧海盗,闻之色变,那是不得了的。索马里海盗,不管谁来了,留下买路钱,否则不客气。从大历史的角度,索马里海盗,太小儿科了。大航海之后,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崛起之中,蔚蓝色,海洋时代来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都没有闲着呀!如果说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动物凶猛呀!那么,航海民族,半斤八两,异曲同工,航海民族在茫茫的大海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海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海盗凶猛呀!斗得过海盗,那可不是一般的本领,某种程度上,比海盗还要具有战斗力。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不说也罢。传说中北欧海盗的大本营,瑞典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啊,福利国家啊,高度发达啊。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带有或多或少的原罪吧!自己反省去吧,点到为止!茫茫大海上,不管遇没有遇到加勒比海盗,在一艘船上,是一种军事化的编制,以便遇到突发事件,随时进行应急处置。船员首先服从谁——船长呀。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触礁了,不行了,这时候怎么样,船长就是“舰队司令”,发布命令:爷们儿都得把救生圈让给老人小孩和妇女。不想让出来,也得让,军令如山倒。在紧急关头,大家可以看,危机处理当中,泰坦尼克号的船员要把救生设备让给老人妇女和小孩。不守这个规矩,就会遭天谴,下地狱,明白了吧。不是说中国,公交车来了,不守规矩,能挤就挤,哪管妇孺?关键怎么样啊,沉船的时候守纪律,这个守纪律,是不是守到家了?像海涛学友说的,这是不是一种神圣性,哎呀,我的主啊,这就是神圣性!船长这时候,在上面就是主,就是“主人”,就是“司令”,就是“总统”,就是“牧师”,让大家怎么着,绝对要听从。为什么呢,因为船长下达的命令是最公正,最无私,为什么呢,船长也得将救生设备让出来。可不像中国,哎呀,大姨子,小姨子,七大姑,八大姨,家里人多,咱都弄上,大家一看这个,还会服从吗?所以,集团性怎么来的,毛润之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大有道理啊!“集团性”首先得有纪律性,为什么呢,因为集团性首先得打仗,是个军事集团,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集团性”来自于哪,来自于打仗。遇到海盗容易打仗。少数民族入土中原,骑着马来了,嘎达嘎达,主要干啥,要抢粮食啊。包括成吉思汗它,这是个军事单位啊。包括满洲八旗,本身是个军事单位。集团来自于军事单位,军事单位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兵。兵得怎么样啊,兵得加强纪律性,就得纪律严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这样的吧!当年西方怎么来的,西方中世纪,天主教长期感化蛮族人。为什么骑士特别尊重妇女?骑士想不想有荣誉,想不想有face?想,就得遵从命令,这是规矩,大家看是不!骑士是最小的单位啊,是这样的吧,相当对于中国看家护院的,但,中国看家护院的,可不大手纪律呀,有时候,还调戏妇女。这与骑士相比,可差了行市了。骑士有纪律性,而且纪律性强到一定程度,为什么?实际上,有一点“克己复礼”,实际上,遇到战乱,参与战争,这是很荣誉的事情,荣神益人。西方,很长时间,只有贵族,才有打仗的权利。英勇善战,立有军功,公侯伯子男。实际上啊,来自一种军事生态的长期积淀,在公共生活当中,在组织生活当中,遵守纪律。为什么说守纪律,本身是军事集团的一分子,习惯成自然。中国也打仗,中国也打仗,主要是“被揍”,主要是“被揍”,明白了吧!中国的阿Q精神,怎么来的?鲁迅读古书甚多,不会没有基本的判断。直到现在,历史课本上,还有一种说法——征服者被征服。成吉思汗被征服了,还是八旗被征服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意淫啊!睁着眼睛说胡话。中原地区,主要是种粮食。西方主要来自于哪,来自于海上,当然,首先是地中海了,大航海,把视野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海上军事集团,哦,过了俺们的界了,违约了,海上一个浪头就过界了,大家看是不?昏天黑地的,一个浪头鲁滨孙就到岛上去了。一个浪头就过界了,那海上的不确定性。但是,陆地上,“二愣子”家,“三胖子”家,房基地界限分明,有时候也有纠纷,找帮大哥,发现没有,那个比较清楚。海上没有那么清楚的边界,为什么啊,这就是不确定性。还有游牧民族,天气一冷,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还非得往北边去,去找爱斯基摩人去啊?肯定往南边跑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打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这就是不确定性。所以,竺可桢先生,气象学大师,就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分析中国的物候变迁。特别有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气候是不是也决定经济基础啊,是不是,气候决定冻死多少“喜羊羊”啊。大家看,只要“喜羊羊”冻死到一定程度,不是成吉思汗,也能锻造一位成吉思汗。为什么啊,恩格斯说了,历史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只要成吉思汗喊一嗓子:弟兄们,走,那就走啦!谁想和“喜羊羊”一块冻死啊。有些民族,本身是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的话,不仅仅是需要一套纪律,还有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伦理,或者宗教。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军事集团需要宗教,来感化这个部落,这才有了那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觉得这话,是冲着成吉思汗或者多尔衮说的。文明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兵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南方还是北方,当兵的有信仰。西方当兵的,信什么呀,天主教呀,大家看是不!这个教或者那个教,某种程度上,它们承载了一种天道神性,是一种正义性。那时候不是为国家打仗,不是为朝廷打仗,不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谁打仗,为上帝打仗。中世纪,一僧二兵三工四役,很长一段时间,僧和兵,结合在一块,就成为僧兵了。这不正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社会的基本面吗!为教皇打仗,积极性是不是高?最后有圣战啊。这个社会,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中国确定性的东西是——朝廷,但是,朝廷给大家的感觉是特别远,天高皇帝远。它是一种确定性,但是,这种确定性,有和没有差不多。梁漱溟先生就说,中国有一种非国家的取向。但是呢,中国就有这种确定性,就是所谓“大一统”这东西,中国不管怎么样,以“政”来统“教”,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朔之分,含糊不得,但,宗教之间,不妨多元,最初,也许是大地域共同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应对之策,天长地久,反倒成为“生存智慧”,这才有了儒道释三教合流。比方说在希腊,确定性是什么,是几何——点线面体。在希伯来,确定性是什么,是上帝——犹太教。一神教,实际上是在亚洲诞生并传播开来,亚洲是世界宗教的大本营。佛教是不,琐罗亚斯德教是不,犹太教是不,祆教是不,道教是不!亚洲作为世界宗教大本营,实至名归。就说犹太教的经典——圣经,经过改良之后,接续成为天主教、基督教的经典,在阿拉伯地区,犹太教的经典,还启迪了穆罕穆德,成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令人诧异的是,不说自己的宗教,受到犹太教的启迪,也就算了,还将犹太教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一神教”的一种不是了,唯一性,意味着一种排他性。“集团性”喜欢与“唯一性”相互依托,也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军事集团和宗教集团,都具有排他性,集团就得有排他性,是一拨儿,就是自己人,不是一拨,就是敌人。毛润之不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打仗首先得看衣裳,穿的一样怎么打,头发一样,服饰一样,这不是自己人吗!穿的一样就没法打。洪秀全那个“天兵”和清军的那个官兵,都梳着辫子,衣着也相同,怎么打,就没法打了,这不是一拨的吗?所以,洪秀全的天兵就得想辙,披头散发,不梳辫子了——长毛,洪秀全的天兵是长毛啊!长毛看到对方,远看服饰不一样,近看留着辫子,拔剑便刺,挥刀就砍,这就是集团性。集团本身带有排他性,它是一种排异,用什么来确定,用宗教来确定。宗教是这个文明的“定海神针”。等于说,先确定了宗教这个东西,再确定其它的东西,以“教”来统“政”。可以没有国家,可以没有部落,但是,不能没有宗教;国家可以改变,部落可以改变,但,宗教是万世一系的,等于说宗教的唯一性。这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种“大一统”。有一个主教,世界上很多人就信,这是怎么样,这是以“教”来统“政”。教皇有一个,朝廷可以分裂,大小无所谓。千万别成立国家,成立国家干嘛啊,给教皇添乱。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地方的孩子,经常上“最后一课”,孩子们上完课,听到老师说:孩子们,明天就不要来了,不上课了,这是最后一课。经常上最后一课,此地的孩子也能接受,这后面有宗教的支撑,只要过来以后,不改我的“教”,就可以接受。明白了吧。国家也是一种“个性”啊,教皇不是不允许大家有“个性”,大家的“个性”,体现为“教民”,该多好呀!非要说自己是某个国家的“国民”,非要说自己有利益需求,那可不大好,有了这种心理,时间长了以后,保不齐发生文艺复兴,也保不齐搞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当然是“个性”的勃发。这对欧洲的定海神针——宗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中国是所有原则的例外,中国实行的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大一统”,以“政”统“教”。比如说在中国,不管是成吉思汗,不管是多尔衮,来了我问他,我还是中国人呗,他说是,是我接受;那我还交粮食呗,交,比起以前交的多还是少,少,OK接受。为什么啊?入中国则中国之,入夷狄则夷狄之。按着中国的方式,比方说你考科举,按着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治国理政。中国人不接受,成吉思汗的后代,铁血政策,高压统治,进行初步的磨合,也得接受呀!文明史上,不止是落后就要挨打呀,中原地区先进,不是照样挨打吗?依照鲁迅的说法,元朝和清朝,岂不正是做奴隶做稳了的时候!中国这种类型的“大一统”,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多见,中国以“政”来统“教”。中国的正朔之分,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体现了古人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宗教往往是多元的,在西方,国家往往是多元的。西方国家可大可小,变着玩。中国可不一样,掺和着,各种“教”来吧,啥好用用啥。中国人的“非集团性”极强,不是没有集团性,少数民族入土中原,就带来了强烈的“集团性”,“集团性”有两种指向,对外和对外。蒙古占领了中原地区,把人分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要有集团性,一圈一圈怎么回事,它就把人分等,这是具有平民色彩的中原地区民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中原地区,向来是从家族伦理来分,一圈一圈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中国人分等,遇到一个问题,分着分着就分不出来了,因为,出了五服了。中国文明建构在血缘之上,但,血缘不足的地方,发展到了地缘。把人分等是不对的。但,“集团性”强的地方,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贫富之分,这倒是可以,挪威瑞典发展的那么好,福利那么高,依然有贫下中农呀!据说挪威瑞典的贫下中农,比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滋润,住房、教育、医疗保障,不得了。欧洲有贵民,有贱民,有贵贱之分。但是,把中国人分成贵贱之分,就受不了,为什么,均贫富,等贵贱,主要是——等贵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能有贵贱之分。但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蒙古人来了,就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把人分成四等,“南人”就不服气了,凭什么我们是第四等?满族来了,严满汉之大防,到林则徐禁烟时,还防着呢。中国的士农工商,也分了,中国的士农工商,也不是论等啊。中国的士农工商,农啊工啊商啊可以转化为士,通过一定条件可以转化的,但是,“士”这个阶层不是封闭的,可以说,谁不是“士”,但,不能说,谁永远不能成为“士”。小户人家,有一位读书种子,自学,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可不是神话和传说。想加入这个阶层,然后,怎么努力也加入不进去,这倒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阶层是闭锁的,不向社会开放,这就是集团的排他性。比如印度贱民,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前边那几个。进不去,就是说从DNA就失败了,投胎投错了,那就分等。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强化等级之间。至少从教理上,宗教不应该强化等级,这个婆罗门教,太邪门了,没有想到的是,印度贱民,在那里,还有些甘之如饴,真是匪夷所思。印度把人分等,贱民还得承认自来贱,俺们是自来贱。印度的国情,让人看不懂啊!那谁能这么认可,中国人就不这么认可。凭什么陈胜吴广就是贱种,秦二世就是贵种?俺们不认可,揭竿而起,拿个粪叉子把秦朝插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凭什么那样啊!这里边啊,一个社会,总有一个轴心。中国的轴心是“政”,那就以“政”统“教”,欧洲那边的轴心是“教”,就以“教”统“政”。欧洲,国家大小无所谓,只要不让改“教”就行了。“中国”是不要改成“外国”就好了,中国地儿挺大,问题不少,但,那也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只要不改成“外国”就好!成吉思汗来了,高压态势,不管有没有条件,反正是接受了成吉思汗子孙的管控。但是,把人弄成贱等,老百姓不大容易接受。因为集团意识不强,所以,不大有国家情怀,鬼子入侵,无恶不作,只好奋起反抗,保卫家乡,保卫和平。中国人自卫的时候,才显得中国人的团结性,就是同仇敌忾,但是,毕竟没有集团的根底,同仇敌忾没几天,中国人就开始乱了,“楚云飞”、“李云龙”,就开始互掐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态,使得中国人不可能自觉地进行集团性训练。非得到没办法了,就是把田地破坏了,把族人祸害了,恼了啊。如果田地没被破坏,家人没被祸害,依仗着那点生存智慧,还得给人合作啊,是这样的吧!别人家的人被祸害和俺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俺们家人没被祸害。如果俺们家人被祸害,那就不干了,俺们投“楚云飞”去,或者“李云龙”去,要不然拉起一支队伍,想办法对付鬼子啊。再一个。非得说中国人有奴隶性,呃,也对。举目四望,校园内外,到处能看到“奴性”。为什么啊?赵元任先生不是说啦,言有易,言无难;非得说中国人没奴性,也对,从哪都可以找到。人家孟子,吾养吾浩然之气,谁说孟子有奴性。国王,过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是亲近“士”啊;到你那里去,那就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中国是所有例外的总和,在中国,所有原则都成例外,放之四海而皆准,到了中国,极有可能失效。就是一加二等于三,在中国也能变,中国特点的数学——模糊数学。这个特别有意思,别轻易说中国没什么,如果轻易的说,中国没什么,最后会发现,中国有而且还很多。诸位学友,以后写论文,做演讲,千万别轻易的说“中国没什么”。当然,说中国有什么,也要慎重,信口开河,那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下一番工夫,读书思考,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中国“集团性”的欠缺,实际上是一种“非集团性”取向。但,也不排除,“集团性”在中国的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复杂性。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啊?多尔衮是不是中国人啊?元朝和清朝不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啊!正统的历史学家,不认可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有一种说法,宋朝之后,华夏就没有了。明代的话,也就是四百多万平方公里,要承接明代的地盘,现在,最多也就是三百万平方公里。清末民初,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不平等条约,清朝割地赔款,大家发现没有,割了地,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啊。要在明朝的基础之上,不割地,不赔款,最多也就是四百五十万,割地好呢,还是不割地好呢?这是中国的囚徒困境。 三 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刘慧玲学友在席明纳,梳理了两回。4月24日一次,今天(5月20日)一次。学界把梁漱溟先生当成新儒家的开端,以为梁漱溟先生念兹在兹,让中国人发扬光大周孔教化,这也不能算错。但是,这只是梁漱溟的一个方面,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另一面”,从事乡建,组建民盟,主张宪政,有意无意,被遗忘了。如果没有“席明纳”,没有读书会,今晚会在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参加梁漱溟和孔学重光的学术研讨会。谢学友水准高低,另当别论,去到那里,定能活跃气氛,大喊一声:梁漱溟先生可不仅仅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先生还是一个宪政先驱,民主斗士。梁先生的心思是,打倒了孔夫子,中国建设现代化不见得更容易,有可能更不容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文化运动当中,确实有一派——国故派,认准了一个道理,中国传统怎么样,中国传统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中国有好东西,自古就好,很多老先生都是这个样子的,究竟为什么好,是不能问的,问为什么好,就已经站在鬼子的立场上了。中国人一定要注意,坚定信念:中国就是好来就是好,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好来就是好!中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毛润之时代,穿越到文化大革命,引吭高歌,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反革命,不能问。呵呵呵……别看一两句话,但是,铿锵有力,现在曲子套用,歌词已经改了,也算是另类的“旧瓶装新酒”——传统文化就是好。梁漱溟先生非常高明,属于非常冷静理性的保守主义者,“西人所长,吾人所短”。平心静气论述中国人的短处,这是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说,老先生启迪之处就在这里,实事求是。并不是说,睁眼瞎说,中国这个比西方好,中国那个比西方好,不是这样。客观看待:奥,中国有长的地方,西方有长的地方,中国有短的地方,西方有短的地方,特别符合辩证思维。比如有一老先生——费孝通,准备下一回,由王红芳学长,聊一聊。费孝通晚年说过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东方说东方文化好,西方说西方文化好,这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西方说东方文化有魅力,东方说西方文化有魅力,美人之美,吸收借鉴外国文明啊。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先生很明确:第一,不反对白话文,第二,赞扬民主,第三,赞扬科学,第四,赞扬现代生产技术。梁先生支持新文化,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是一拨的。梁漱溟先生一生,有两大主旨:顺应世界潮流,发扬中国文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国故派”主张发扬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既要顺应世界潮流,也要发扬中国文化。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是一分为三吗!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中即西,非善即恶,这都是“一分为二”造成的祸害。最有意思的是,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越能接受“一分为三”,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深陷在“一分为二”的泥沼不能自拔。特别是知识界的左派、右派,其实是极左派、极右派,连左派和右派里面的温和色彩,都不能接受,文革红卫兵的毒害,何其深也!梁漱溟赞成民主,赞成科学,但,梁漱溟也赞成孔子,为这件事,跟陈独秀、李大钊“干仗”,何必把孔子说的太坏呢,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没有搞好,搞责任追究,没有问题,但,没必要追到孔子,把孔子“拉黑”,凭空认定,孔子挡住新文化的道了。孔子在春秋时期,创立私学,编辑图书,其实就是一种“新文化”。孔子也要承前启后啊,是这样的吧!孔子是喝着什么奶长大的啊,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守先待后。大家注意,孔子本身,不是“保守派”,而是“革新家”,这才是真实的孔子。在社会大巨变中,孔子再三再四,吾从周,吾从周,号召大家克己复礼,看似是一位“保守派”,实则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发扬优良传统,汲取变革的精神滋养。其实,传统有生命力,不用守,也守得住。京剧昆曲有生命力,不用中国非物质文化传统遗产传承人守着。郭德纲的相声,恢复了相声小剧场的传统,涵养了水土,激活了相声生态。非得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整天挂个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懒得去公园,给老头老太太唱,只想给“中南海”唱“堂会”。一群人活蹦乱跳的,没有必要挂个牌牌,是这样子呗?非得挂个牌牌,证明没有生命力了,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李零先生说了一句极端的话,如果那样的话,“国粹”就是“国渣”。西方化不了的东西,西方认为是“渣”,中国则说,谁说是渣——“国粹”,这样一来,“国粹”就是“国渣”。比如说中医,西方化不掉,中国说是“国粹”。今年有一桩趣事,徐晓冬那小子一拳把太极大师打蒙了,是这个样子吧!多少太极大师在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大师被揍,国家尊严,传统脸面,广大劳动人民能干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能干啊!武林要开大会,华山论剑——哎,这小子,太狂妄了。李零先生这话吧,说的有点极端,但话糙理不糙。“国粹”往往是“国渣”,就是什么意思,西方的东西化不掉。看到没有,有太极,有武当。再一个怎么样,中医在近代中国,命运不济,总有些人想取消中医。但是,梁任公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准备写中国文化史但是没有写成,割腰子割错了,医疗事故啊,头死的时候对家人说:别说啊,我是变法维新的人,别说。家属就没说。为什么啊?那时候啊,“西医”刚刚站稳脚跟,梁启超割腰子割错了,中医大师听到了,有可能据此对西医发动新一轮进攻。后来,毛润之时代,毛润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干出不少荒唐事,反右,四清,文革,但是,毛润之有一点做对了——中西医结合。有一个屠呦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医疗卫生部门,依据毛润之最高指示,进行消灭疟疾的大兵团作战,年轻的屠呦呦就在其中。屠呦呦取得的成绩,具体印证了中西医相结合,是很高明的。屠呦呦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家里就是药铺,后来学了西医,但,中医典籍并不陌生,屠呦呦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葛洪的教导,葛洪说,用凉水弄,屠呦呦就弄凉水试验,结果弄成了,这个非常有意思,中西医相结合,某种程度上,校正了中国没有医学的偏见。西方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医学啊?现代医学所要求的严格的实验,中医没有。这里,谢学友建议:将“中医”改成“汉医”,为什么?因为给人感觉,“中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医学,有一种“外医”的感觉,但“藏医”,还有“蒙医”,还有“瑶医”,本身都是中国的啊。在我看来,“中医”应该涵盖“汉医”、“蒙医”、“藏医”、“瑶医”,各种民族医学。这里就有医学生态的多样性问题,没有必要“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梁漱溟先生就看到了生态的多样性,没有那么狭隘,超越了那个二元对立。这里边就可以引出包括“宗教”与“科学”,包括“集团”和“非集团”,包括中国的“人情”和西方的“法治”。“法治”可以看到,本身是一套纪律,某种程度上,西方的“法律”不仅来源于是“宗教”,但是,中世纪增加了法律的神圣性。所以,为什么说,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这句话,大有深意,西方的法律渊源,要追溯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历史。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有着很长的历史,不妨把镜头向中世纪延伸。第一,有宗教,宗教里有戒律,大家要遵从这个戒律,大家要守规矩;再一个作为一个世俗的国家,大家要守规矩。以前呢,以前有“教民”,“教民”不大在乎“国民”的存在。现在有“国民”,也有“教民”。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中国没有很强的“国民”观念,与什么有关系,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没有关系,梁漱溟先生还“埋怨”过,中国非国家的取向;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在西方,“国民”也是晚近的事情,千年中世纪,都是“教民”。那与什么关系大呢?与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态关系大。就是什么东西,找坏的就找到传统上去了,找好的就找到核心上去了。计划生育国策,执行正酣的时候,可没有少埋汰孔子,孔子怎么样,怎么样,言外之意,老百姓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积极,受到孔子的不良影响。孔子对祖国的贡献有多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贡献太大了。就是,一窝一窝的,你杀不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文化长在人身上,千万不要在人之外去寻找文化。大家注意,书里的文化,都不是“真”文化,都是对文化的“臆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做梦,生活中的文化才是真实的。老太太喜欢过年,年味就浓,有的地方年味淡,是这个样子的吧。传统深厚的地方,年味就浓,传统急剧流失的地方,年味自然就淡了。很多时候,说中国不好,大家注意,没有考虑现实处境。比如说中国人不守规矩,就是没有制定规矩,或者制定规矩的人,不守规矩。大家你看看,制定规矩的不守规矩,希望老百姓守规矩。“政法王”到法庭上竟然说自己法律意识淡薄,遥想当年,“政法王”到处给大家普法:最关键是老百姓,大学生一定要守法。“政法王”身边的,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俯拾皆是,居然忘记了给政法委书记普法,可笑呗,是这样的吧!说起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时,主事者满脸愁容:由于受“封建”社会影响,人们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如果那样的话,就得从“基因”找原因啦,岂不是中国人投错胎了,中国人守不了纪律啦,中国人过不了集团生活了,中国人没有公共观念了,中国人不能过组织生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了。其实,以上这些理由都不成立,是什么啊,是现实处境,改变了那种处境,按照那种法律制度安排,实际上,可以走出来。那以前,以前呢,都是“非集团性”的那种生活观念,中国人对“集团”,确实存在警惕之心。君子“群而不党”,只要一说结党,必然是“结党营私”。法治什么的,就是“集团性”本身带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胎里带”。“集团性”本身就是组织啊,法律啊。比如说,所有人都信教,谁不守“教规”,就得被受收拾,收拾到什么程度,有纪律的啊,这是“集团性”本身带来的。而中国呢,有着绵长的“家法族规”,但是,在“家法”和“王法”之间,是不是有广阔的空间?怎么办啊,看着办吧,大家看是这种情况呗,那看着办,有可能往左边看,有可能往右边看,大家看是不?实际上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中国要由“非集团性”,过渡到“集团性”的生活,那就得守规矩。大家看俄罗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时候,排队买面包。七八点钟,天还黑,寒风凛冽之中,人家排队。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愿意加塞,不喜欢排队。这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吧,人家有东正教,是这样的吧。俄罗斯转型时期,不能承受之“重”,人家就承受下来了。就是人家生活,公交车,买面包,该排队就排队,是这样子的吧!中国呢,还没建立这种最基本的秩序。总得有一个开头啊!总是听到主事者说,老百姓没有纪律观念,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还是老一套:最关键的是教育老百姓,让老百姓知法用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现在建立“集团性”的体制,就会有与“集团性”相匹配的这种规矩,这种规矩建立以后,那就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埋怨的时候,埋怨中国传统,感恩的时候,感恩党和政府。什么东西弄不好,就会埋怨孔子,那什么东西好的时候,一带一路啊,是不是也得感谢孔子啊。一个道理啊,为什么,世界上的“点赞”和“拉黑”是相匹配的,对传统全“拉黑”,对现代全“点赞”,哪带这么玩的啊!等于传统时不时得给当代中国背黑锅啊,背到什么时候啊!在我小的时候,传统文化就为现实处境背黑锅,改革开放以后,继续背,包括计划生育,就是怎么样,高王凌和李零所说的,倒霉看反面。别把古今看的失衡,别把古代看的特别不好,与其相匹配,也不用把古代看的特别好。相当于,不要把现在看的多么不好,也不要把现在看的多么好。现在有现在的处境,天花板处境,达摩克利斯之剑,古代有古代的处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比的过清朝,为什么呢,清朝的科举制就读四本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何时考政治课呢,康熙思想,雍正理论,乾隆三个代表,举子不必学的,孔子和孟子的指示就OK了。再一个,中国和外国,不要倾斜,古今中外不要倾斜,为什么呢,平常心嘛,对吧。不要轻易的说所有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佛教就不是从欧美来的;也不要轻易说,所有坏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所有好东西都是中国自己的,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偏颇。今天的“席明纳”,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交流的效果,是这样的吧?大家参与其中,挺有趣的。大家尽情尽兴的交流,我觉得今天达到了有史以来,“席明纳”的最佳效果。首先,刘惠玲学友梳理的好,是吧。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大家伙听得特别明白,特别明晰;再一个,大家有问题意识,充分调动了“当身历史”就是怎么样,较劲的地儿,大家拎出来了;呃,再一个,谢学友相对比较低调,先前我没说,大家说的就相对多了,畅所欲言。这是一个成功的“席明纳”,这是一个胜利的“席明纳”,这是一个团结的“席明纳”。 (2017年5月20日,《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席明纳”所做发言,录音整理:河北科技大学2015级裴海涛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