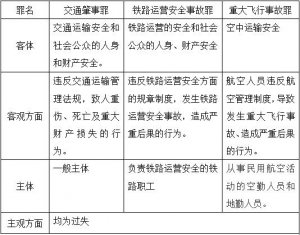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周氏一言堂 错案责任机制之反思——兼议我国司法责任制度的完善进路 【内容摘要】由于事实生成过程以及法律适用结论的可错性,使我们不可能设定出逻辑圆洽的错案实体标准,进而可以认为,“错案”无法作为一个法学或法律专业术语而成立。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当下对错案的认知存在方向性偏差,而相应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的设置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浪费,更是一种逻辑上无法成立因而应当予以摒弃的司法改革举措。当然,主张废止“错案”概念以及当前错案责任机制并不意味着对它曾具有的积极价值之全面否定,更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放任法官任意或恣意裁判,而仅仅意味着需要换一种规训司法的思路,也即由结果、实体导向的错案责任追究换作行为、程序导向的司法责任监控。【关键词】错案;高贵之梦;事实;条文意义;人民司法 司法责任机制是规训司法、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保障,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我国已建立起以错案责任倒查机制为核心的司法责任制。可以说,当前我国所有司法责任制度都紧紧围绕着错案责任倒查机制展开。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欲健全、完善我国司法责任制,首先必须对错案责任机制作出准确的分析、评断。通过检索可以发现,作为一项重要且少有的全程贯穿近几轮司法改革过程的举措,错案责任机制自推出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各方的非议、批评[①],但所有这些批评、质疑并没有导致它的废止,甚至也没有导致它的动摇——毋宁说,实践中它恰恰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加强。那么,是理论界的批评欠缺力度,还是错案责任机制本就没有问题?本文的研究将尝试表明:一方面,尽管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曾经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价值,但由于它存在着内在的、根本的逻辑缺陷,故而应当予以废止;另一方面,综观几乎所有相关研究,支持、赞赏错案责任机制的固然没有给出有力且符合逻辑的理由,但反对、否弃它的同样没有给出有力且逻辑圆洽的批评,甚至可以说其中的很多批评根本就不得要领。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当然还将提出规训、监控司法的因应建议。一、“无的放矢”与“叠床架屋”:对错案责任制的初步定性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就开始陆续探索并尝试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②]。从逻辑及经验上讲,这一制度的目的或者说设计初衷应该是:通过审查案件审判结果的对错,对错案承办法官进行责任追究,进而倒逼法官提高办案质量,减少错案的发生,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错案责任官方文件中,却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错案”本身进行界定。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1995年),又如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最早系统确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1998年),以及最近一次涉及错案责任问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甚至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专门针对错案问题颁行的《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2013年)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通行于法院系统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等,虽然都把“错案”当作一个关键词来设置相应规范、制度,但却都没有直接对“何谓错案”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对于这种制度安排,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的说法,实际上是有意为之。他撰文指出,反对设立错案责任机制的观点认为,“错案本身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错案概念模糊不清,认定错案标准和范围难以确定;错案责任追究不当,会使法官时常处于被追责风险之中,有形无形会影响审判行为的独立性;法官害怕发生错案,会想方设法将案件决定权转交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和上级法院,实现责任转移,违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基本原则;同时追责不当也会影响法官独立品格的塑造等。这些反对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意见》综合考虑各方观点,最后删去了‘对错案和错案责任定义’的条款”;那么,为什么仍然要坚持出台错案机制,这是因为“错案是客观存在的,法官要对自己的审判行为和案件质量负责,裁判出现错误,倒查法官是否有责任也无可厚非”。[③]从这段文字可以很容易看到,第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其实非常了解错案责任机制反对者的声音及理由,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认可,所谓“这些反对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第二,当前错案责任机制的根本基础就在于“错案的客观存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逻辑问题:一方面,制度的设计者很清楚无法界定错案,也就是说,很清楚自己不清楚什么是错案;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错案“客观存在”。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格局?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正如我们可以不必知道对“人”的清楚概念界定但却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桌子不是人而苏格拉底是人一样,对错案概念的不予界定,并不构成实践中处理错案以及相应责任问题的障碍。这种回答乍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漏洞:第一,当我们判断桌子不是人或苏格拉底是人时,实际上作为判断者的“我们”,内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关于人的界定,只不过我们没有说出来而已,但你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说出这个界定就否定这个界定的存在。更大的漏洞则在于,第二,当我们遇到非典型情况时,我们会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对“人”的界定确实会构成实践中相关判断的巨大障碍,譬如“人兽怪”(人与动物交配后的产儿)是否是人?又譬如“狼孩”(出生后从来没有接触过人及人类的小孩)是否是人?另外,第三,这一类比可能还不甚合适,因为对人的不同界定所带来的可能主要只是一种理论争议,但对错案的不同界定却可能导致法官以及相关关系人很多切身、现实且直接利益的变更、剥夺。综合这第二、三点,则可以说,我们无法也不应以一种看待纯粹理论争议的方式来看待错案的概念界定问题。另一种可能的回答则是:虽然相应文件没有明确、直接地界定何谓错案,但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从中推断出错案的概念。譬如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4条之规定“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导致评议结论错误的,由导致错误结论的人员承担责任”,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5-27条之规定,其实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对错案的界定: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事实认定确有错误的案件[④]。这大体上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者们对错案的界定,该法第243 条第1 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尽管理论界对于“错案”的概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⑤],但从实践来看,法院似乎也只能、事实上也确实是按如上推断界定错案:即适用法律或事实认定错误的案件。这种回答的可能问题则是:第一,与前述制度设计者的主观且明确的认识相左,如果错案真的可以如此容易地得到清楚界定,为什么实际上其他的很多文件或规定却放弃作出界定?第二,如果错案就是指“适用法律”或“事实认定”错误的案件,那么,由谁又依据什么来判定一个既有的判决“适用法律”或“事实认定”错误?表面上看,现有的这些规定已经对如上第二个问题作出了部分但清楚的回答,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7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34条规定,“需要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一般由院长、审判监督部门或者审判管理部门提出初步意见,由院长委托审判监督部门审查或者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说这种回答是“清楚的”,是因为它明确了错案的认定主体;说它是“部分”的,是因为它并没有明确判断标准,逻辑上的推论只能是:只要人民法院审判组织(如审判委员会)判定一个判决错误,那么,就意味着错案的出现。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何以审判委员会或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以下将错案认定主体简称为“追责者”)的判定就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可以是现有的判决才正确?又或者,为什么不可能仅仅是两者各有不同但都正确或都不正确?申言之,只要标准不明确,则错案的认定机制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强盗逻辑的基础上:这其中,追责者是那个“强盗”,而当前判决的作出者是那个“被挟持者”。那么,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的标准是否可能得到明确?对这一问题,笔者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详细的回应。现在我们可以确知并应重申的是:当前的错案判准阙如。错案判准的缺失,必然导致的问题是:作为“被挟持者”,也即作出当下判决的法官(以下将这一主体简称“责任法官”),处于绝对弱势且十分不确定的状态,因为他根本无法预知追责者将作出何种判断,也因为他根本无力影响、抗衡追责者的决断。错案责任机制的设计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相关文件特别明确无需承担错案责任的具体情形(详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8条及《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2条)——正如前文一个脚注所已经明确的,这些免责情形实际上就是试图把没有主观过错的错案排除在追责范围之外,但必须再次马上予以明确的是:这些情形中的案件首先仍然是错案,只是无需追责而已。我们固然应当替责任法官欣慰于这种制度安排的存在,但恰恰也正因如此,使得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请注意,不是整个的“司法责任制”,而仅仅是其中的错案责任机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重复制度建设,换言之,一种纯粹的立法浪费,并且——考虑到制度的重复建设几乎必定意味着立法的冲突——还是一种可能造成立法冲突的立法浪费。因为如果法官真的只有因主观过错而导致错案出现时方才承担错案责任,那么,我国《刑法》以及《法官法》等法律法规其实早已经作出了相应规定(详可见《法官法》第32条以及《刑法》第399-401条)。有人可能会说,即便上文关于立法浪费的判断能够成立,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也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既有的这些制度并没有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否则,何以错案“客观存在”且不断出现?对于这种可能的辩护,这里的回应是:第一,“错案客观存在且不断出现”这一判断可能自身就有问题,至于问题出在何处,本文第二部分将给予回答;第二,如果已有的制度因为得不到执行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有什么理由认为重新设计、甚至简单重申该制度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钱穆曾这样评断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引者注,原文如此)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⑥],后人把钱穆先生观察到的这一制度建设现象名为“钱穆制度陷阱”。我们虽不敢说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一定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病上加病”,但必须承认,它确实颇具叠床架屋、重复冗余之意味。错案判准的缺失,进一步导致的问题是,它使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多少有点儿“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意味:我们知道,堂吉诃德氏甚至都没有搞清楚风车是个什么东西,却无的放矢、勇猛果敢地与风车搏斗了n个回合。导致自己严重受伤不说,更重要的贡献或许是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经典的警示:在采取措施应对一个事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或至少应该努力尝试对之作一清楚的认识、判断。当然,倘若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真的可以达致其立法目的(降低错案率进而提升司法公信),那么,即便它确实是一种立法浪费也存在明显的钱穆制度陷阱以及堂氏风车大战之意味,也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这种判定并不足以导致我们非得否定它。再换言之,如果要证成本文之基本立论(当前错案责任机制由于建立在不能成立的“错案”认识逻辑基础上因而应当予以废止),还须给出更有力的理由。二、“高贵之梦”终究是梦:对错案责任制的进一步认识前文的分析表明,错案责任机制的逻辑根基在于错案判准的确立,但当前错案机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否视,所谓“删去了对错案的定义”;而在经验中,又注定只能以后审[⑦]作为实际上的错案判准,但这一实践做法又显然存在诸如何以认定后审一定比前审更靠谱等前述问题。因此,无论从逻辑或是经验上讲,我们都必须尝试着对错案判准以及错案本身作出界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国内学界几乎所有对错案责任机制的批评或赞赏,实际上都多少具有空中楼阁之意味,因为它们恰恰没有给错案判准这一错案责任机制的逻辑起点予以足够的关注、剖析[⑧]。那么,到底能否设定出“错案”认定的实体标准,进而达致对“错案”认定哪怕仅仅是相对客观、公正之效果?让我们以司法决策的基本结构(以规范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的推理)为依托,来尝试着给出否定的回答。1.事实生成的裁量本质与事实认定的可错性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事实的认定标准毫无疑问是客观事实,这可以从几大诉讼法中关于事实认定标准的如下措辞得到确认,所谓“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⑨]”(《刑事诉讼法》第51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73、195等条),“事实清楚”(《民事诉讼法》第85、139、142等条);也可以从我国实际上的无终审制度[⑩]等制度安排看出。在一个名篇中,哈特(H. L. A. Hart)曾戏谑地称那种认定在法律世界存在如自然科学领域中那般的确定性、客观性因而能够寻求到正确答案的主张为“高贵之梦”(noble dream)[11]。在本文中,笔者将“高贵之梦”的外延作进一步的拓展:它用来指称那些看上去很美因而具有可欲(desired)性,但实际上却决不可行因而也不具有现实性的各种法律制度设计或法律观念。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对于事实认定标准的设计就具有明显的高贵之梦的意味,这主要是因为它至少存在如下问题:它混淆了“作为司法决策结论小前提的事实”(以下简称“小前提事实”)与“上帝所知道的当事人实际做出的事实”(以下简称“客观事实”)。显然,对于后者,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且仅有一个惟一正确答案,并且其判准是、也应该是如自然科学般的“客观、准确、清楚”,如果径直把后者当作前者,则显然前者的标准也应当是“客观、准确、清楚”,这也正是当前我国相关制度安排之内在逻辑、理念。然而,问题却在于,小前提事实恰恰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观事实。利科(Paul Ric?ur)在论及历史学家的史实认定工作时曾作过这样的描说,“历史(学)的目标不是再现一系列过去的事实,而是重组和重建”,为什么不是“再现”而是“重组和重建”,这是因为“历史学家不面对过去的对象,而是面对过去的痕迹”,也正是“这种明显限制使历史(学)失去了科学的资格:在历史文献的痕迹中理解过去,确切地说是一种观察”,而“观察并不意味着记录一个原始事实”[12]。利科的这一描说道出了如下非常朴素但却坚硬的道理:一方面,由于我们不可能、至少现在尚无途径回到过去,因此,我们不可能看到作为历史事实的整体,充其量只能收集历史的痕迹,然后根据这些痕迹去重组、重建——显然,由于痕迹本身并不能自动回构出某种史实,因此历史学家所谓史实一定是“主观加工并制造”之产物;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所谓“史实”并不是纯粹的、赤裸裸意义上的物理事实,而一定是某种程度的“理解”、“观察”,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谓的史实一定是被赋予了某种或某些意义的“理解”、“观察”,而“意义”当然一定具有主观性,“纯然客观的意义”一如“不发光的灯”一样根本就是个逻辑悖谬。申言之,利科告诉我们的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史实一定具有主观性,因而历史学不可能具有科学之资格[13]。考虑到在司法决策过程中法官同样不可能回到过去,因而他同样也只能收集痕迹(证据以及案件片断[14])进而重组案情;当然,在案情被制造、复现出来之后,法官还需要赋予其某种特定的意义。因此,小前提事实之生成是典型的“法官制造”之过程,而客观事实则是当事人实际做出来的,因而两者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儿。两者有没有可能重合?当然有可能,但这种重合具有的却是“如有重合、纯属偶然”之意味,就正如“学习成绩好的男生”与“适合做好老公的男人”可能重合但却纯属偶然一样。同样明显的是,由于法官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对案情予以定性、也即赋予当前已确立之“赤裸裸”的事实以特定之意义,如认定“Tom握着刀刺入Mike身体”意味着“故意杀人”、“正当防卫”、“履行合同”等,而“故意杀人”等不过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小前提事实一如历史学家的史实,同样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综合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小前提事实的生成或认定,是一个典型的discretion、也即主观裁量之过程。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到前审-后审比较的环节,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本就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实质性、实体性标准来证成后审事实结论的“必然正确”或仅仅是“更正确”。与这一判断相呼应的另一个事实是,迄今为止,并且可以想见在将来的任何时刻,都没有人能够从逻辑必然性的角度证明后审结论一定就比前审结论更为正确、甚至更好,经验中之所以最终选择执行的是后审结论,不过是因为制度的硬性规定使然。另外尚需指出的是,我国当前把“客观事实”或“事实真相(象)”当作小前提事实判准的做法,除了忽视了两者区别之外,还存在如下问题:除了上帝,有谁知道客观事实或事实真相?显然,作为上帝子民也即凡夫俗子的我们,任何“人”都充其量不过是“以为”自己知道了客观事实或事实真相,而如果我们根本不确信自己知道客观事实是什么,又何以判断某个小前提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或“忠于事实真相(象)”[15]?换言之,又怎么可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小前提事实的判准?因此,关于小前提事实,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不同法官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他们得出不同结论是正常的,因为“台上一个哈姆雷特,台下有多少个观众就可能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或者用更为学术的哲学解释学术语讲则是“有理解,理解就会有不同”[16]。如果一定要对前审和后审结论作一比较,则只能是定量意义上的可接受性程度的比较:有些事实认定结论由于逻辑圆洽性以及说理充分性等方面更好,因而更不容易引起争议。换言之,后审没有推翻前审的事实结论纯属偶然(后审法官在如上痕迹收集、案情回构以及意义赋予等三个环节上正好与前审法官完全一致),后审推翻前审结论才是必然。总而言之,至少作为司法决策结论小前提之事实,本质上就具有典型的可错性[17]意味。或许也正因如此,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在谈到西方初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时才作出如下断言:“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这里所应达到的是确信,而不是更高意义的真理”[18]。2.语法-语用意义的二分与法律适用的可错性很多时候,“依法办事”或“严格依法办事”几乎成了法治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皆然,最早的版本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谓“优良法制的一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定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们遵从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9]。然而,正如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或说法尽管被广泛接受但其自身逻辑未必成立一样,“依法办事”这种说法亦具有明显的似是而非意味。从逻辑上讲,“依法办事”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在办事之前相关主体知道第一,存在相应的法,而且第二,知道这法的具体规范内容,与此同时,至少地位相当之其他人也知道。这就是说,如果在办事之前并不存在一个人所共知的法,或虽然大家都知道存在先在的法却并不知其具体内容,则所谓“依法办事”就不过是另一个梦。表面上看,由于法律早已经为立法者所颁布,其规范意义也十分清楚,换言之,存在先在的法并且人们知道其规范内容是不言自明、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更大的可能是,人们以为存在其规范内容早已经确定并被确知的法。让我们结合“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我国《婚姻法》第6条)这一法律条文来作出说明。首先,该条文本身的先在性当无可置疑,但其次,该条文具有怎样的规范内容,则并不具有先在性。因为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它到底具有怎样的规范意义,譬如其中的“男”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它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取决于法官在具体语境中、面对具体案情时的判断/择取:举例而言,如果一个25周岁的中国男孩甲与另一个21周岁的中国男孩乙来登记,是否属于这里的“男”?尤其是,甲和乙谁才适用“二十二周岁”之条款,还是两个人都必须适用?此时,法官就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断,如果“案发”时全社会对同性恋现象普遍宽容、接受甚至祝福,并且如果该法官自身心态也相对开放,则他很可能会认定,《婚姻法》第6条中的“男”当然包括同性恋者[20];当然,在另外的情形中,法官则可能认定,此处的“男”不包括同性恋者;或者,法官虽然认定“男”包括同性恋者,但同性恋双方都应适用二十二周岁之限制;又或者其他规范内容。显然,不管法官最终选择了如上哪一种理解,“男”字到底具有怎样的规范内容都实际上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方始经由法官才最终得以确定。那么,如果法律条文的规范内容必得面对具体案件时方能确定,又如何解释在许多情形之中,我们似乎总是可以观察到人们落实的是一种先在的规范内容,否则,所谓法律后果的可预测性岂非根本不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区分如下一对范畴:法律条文的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在本文中,所谓语法意义(semantic meaning),指的是一个法律条文依据构成它的语词之词典或通用法学意义以及句法结构所具有的意义。譬如,“22周岁以上男性”的语法意义可能是“一个过了第22个生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士”。而所谓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则指的是一个条文在具体语境中,实际上被理解到的规范意义。同样以“22周岁以上男性”为例,它可能具有“除男同以外的22周岁以上的男性”,或“除女性以外的22周岁以上的人”(此时,则各种所谓雌雄同体或天阉亦属于此处男性),或其他可能的意义。当然,语用意义也可能大体上与语法意义相同——例如当面对典型案件时,用法者从该条文中理解出来的语用意义很可能就与其语法意义相同。可以想见,相对而言,一个条文的语法意义总是具有更明显的确定性、规范性和社会化的约定俗成属性;而语用意义则具有可变性、个别性和个人主观性,但正如前述用法者真正落实的却只能是法律条文的语用意义。同样不难想见的是,一个法官为了降低其法律适用结论的争议可能性,或减免其说理、论证责任,在决断一个条文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意义时必定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地与该条文的约定俗成的语法意义相同。法官的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外部效果是,第一,法官的法律适用结论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进而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第二,法官只不过在落实一个条文先在的规范意义或内容,所谓“(严格)依法办案”。但必须明确,第一,不管法官最终选择了更为接近语法意义的理解因而降低了自己的风险、成本,还是选择了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的另一种语用意义,终究都不过是法官的“一种”(a)选择,显然,在他作出具体选择之前,并不存在一个注定将被他选择、落实的先在的规范内容。这就是说,法官只是看上去在依法办事,实际上依据的不过是自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事实上,第二,选择更接近语法意义也只是法官等用法者的一种倾向,而非他们的必然之选择。譬如,当依据语法意义(或接近语法意义的语用意义)不利于己方利益或目的的达成时,包括法官在内的用法者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把立法条文的语法意义搁置一边。让我们以“外来机动车辆不得入内”这个规则为例来作出说明:在通常情形中,“机动车辆”的语法意义是“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21]。但不难想见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官,当遇到诸如一辆响着警铃的救护车等情形时,一定会将“救护车”这一典型的“机动车辆”排除出“外来机动车辆不得入内”的适用范围,尽管这意味着你对“机动车辆”这一术语的理解明显超出了其语法意义。相对应地,如果你是一位其他用法者,假如你综合过去几个案例发现法官几乎总是愿意放任救护车入内,并且你正好又是开救护车且想入内的人,就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入内;相反,尽管你综合过去的几个案例发现同样的内容,但你却是门卫且不想让某辆救护车入内——基于你的这个已然确立之立场,即便你明知法官过去都判决救护车可以入内,也就是说即便你发现对法官来说“机动车辆”的语法意义并不包括“救护车”,你也将故意寻求某些理由(譬如“今天是校庆所以即便是救护车也不能入内”等,甚至可能是那些你自己也未必认同的理由)来支持你的立场,而非倾向于去追随法官在过去司法经验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解。申言之,考虑到法律纠纷中往往有立场鲜明对立的双方,因而比较符合经验逻辑的实际情形是,当且仅当追随立法之法的语法意义有助于证成己方立场或主张之合理性时,法官以及其他用法者才会表现出如上倾向。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颇为认同苏力顺着波斯纳(R.Posner)思路及逻辑所作出的如下论说,“对于优秀的裁断者来说,许多规则尽管被称之为规则,在其司法实践中其实只是被视为事实之一,是他在决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约束条件,却不是他必须遵守的唯一命令。法官高度重视是因为,他有责任努力实现立法者的追求,确保自己决策的合法律性,他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决策是否会因缺乏法律根据而在上诉被推翻,或是为后来的法官以判例推翻或是立法者以立法来推翻等。但即便如此,这仍然不一定是迫使他必须遵守的全部动力,只要可能且符合情理,他还是可能不予遵守一条规则。契约必须遵守这是通则,但民法实践上却一致允许效率违约”[22]。如果法官真正落实的只是自己对于法律条文之语用意义的择取,那么前审与后审法官作出不同的择取就实属正常、必然,如果二者作出同样的选择反倒是意外、偶然。3.错案的无实体标准性与错案责任机制的高贵之梦意味如上的考察表明,由于当下办案人员无法回到过去,因此对法律人来讲,所谓事实,尽管有其客观基础(案件片断),并且受到逻辑圆洽性等限制,但从根本上讲却是实实在在的主观造物,因为它根本上只能通过人的主观回构才得以生成,并必须仰赖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某种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由于人毕竟不是上帝,而显然只有上帝才知道客观事实是什么,任何“人”都充其量不过是以为自己知道客观事实而已。因此,我们不可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小前提事实的判准。与此同时,对法律条文语用意义的选择、决断,也注定是一个没有先在实体标准的过程。这就是说,在司法决策的过程中,无论是小前提事实的确定,还是大前提规范的选择,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可错性,这使得我们不可能预先地设定一个错案(或对案)的实体判断标准——或者说,从实体上讲,任何一个判决都同时是对的和错的。尽管由于实践中我们只能执行一种判决结论,因而实践中我们往往只能选择执行后审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审结论更对或更好,而毋宁说是一种制度强制安排的不得不然。事实上,从逻辑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怀疑、诘问:当后审结论与前审的不一样时,为什么就不是后审有问题而一定是前审错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杰克逊(RobertJackson)何以断言,“联邦最高法院并非因为它的判决总是对的(infallible)而被认定为终审法院,而是因为它是终审法院故而其判决总是对的”[23]。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错案”可以是个哲学范畴、社会学概念、文学术语或日常用语,但根本就不应是个法学、法律术语,在法律的世界符合专业逻辑的说法只能是“改判案件”。如果一定要将“错案”用于法律、法学的世界,或许我们惟一有把握的用法仅仅是:当一个前审判决被宣布为错案的时候,其实质是追责者(或其他作出这种宣称的人)自以为自己掌握了对的判决,但除非追责者是上帝本人或具有与上帝一样的神通,否则这种宣称本身很可能就已经意味着他作出了一个错误判断。换言之,此时他办了个“错案”,因为他至少具有“过于自信的过失”。总之,在法律的世界并以专业的眼光来看,不存在所谓错案[24]。因此,即便一个前审判决被后审推翻,也并不意味着前审是错案[25]。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之初衷或许是好的,但由于其关于“错案”认识的逻辑根基并不成立,因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高贵之梦:虽则可欲,但却并不可行因而也不具有现实性。总而言之,尽管它可能十分高贵,但高贵之梦毕竟也只是个梦,而梦注定是虚幻的。三、“人民司法”理念:当前错案责任制的主要动因在本文的开篇,笔者曾提到:尽管错案责任机制一路走来伴随着各种质疑、批评,但却并未因此而被废止,相反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加强。如上第二部分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所有相关批评并未能从逻辑上真正消解、击倒错案责任机制存续的合理性。但即便如上第二部分的分析能够成立,充其量也只是消极地证否了当前错案责任机制存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并没能解释何以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更高的决策层如此积极地推行这项饱受争议的责任机制。换言之,前文的分析充其量只是解释了何以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放弃这项机制,却并未能解释它何以如此坚决地推行、推广这种机制。如此一来,合乎逻辑的解释就只能是:一定存在一些特殊考量或支撑因素,使得最高人民法院有足够动力义无反顾地去推行这项机制——即便其自身也深知“……错案责任追究不当,会使法官时常处于被追责风险之中有形无形会影响审判行为的独立性;法官害怕发生错案,会想方设法将案件决定权转交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和上级法院,实现责任转移,违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基本原则;同时追责不当也会影响法官独立品格的塑造等”,并承认“这些反对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语)。那么,具体是什么因素给了法院系统以如此强大的动力续推错案责任机制呢?达玛斯卡(Mirjan R. Dama?ka)曾界分两种典型的政制模式,进而提出了两种不同面向的司法,“如果把政府视为一个社会的总管,那么司法活动就必须致力于贯彻国家的纲领、执行国家的政策。相反,如果政府仅仅负责维持社会的平衡,司法的目的就必然同解决冲突和纠纷联系在一起。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描绘两种法律程序的原型:一种致力于解决纠纷,另一种致力于执行政策”,其中,“政策实施模式更加偏爱官方调查的方法,而纠纷解决模式则对竞争式的方法情有独钟”[26]。考虑到中国从古至今素来具有国家-社会不分之政治观念,而现实经验中也确实存在相应的整体结构[27],这使得中国政府几乎总是更倾向于扮演“社会的总管”之角色,进而使得自古以来中国之司法几乎总是更加亲睐“官方调查的方法”或扮演“执行政策”的角色。至少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当下中国司法也确实如此:首先,考察我国几大诉讼法,很容易发现所有审判程序都依托于庭前调查(刑事案件中公安、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并紧紧、仅仅围绕着庭审调查这一核心展开,尤应强调指出的是,无论庭前还是庭审中的调查,在当下中国显然都以“官方”为主导。因此,尽管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开始有意识地增强司法审判的竞争性意味,但总体上看,当下司法仍更多地属于达玛斯卡所谓的“执行政策”型司法。其次,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考量,新中国司法几乎总是自觉自愿地扮演党的革命以及和平建设事业之服务工具的角色,对于这一角色,《人民司法》曾在一篇社论中作了这样的描说,“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工具,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必然使法院工作失去统帅、迷失方向。人民法院能不能正确地执行和完成审判工作的任务,首先决定于是否真正听从党委的话,是否真正按照党的意志办事,成为党的一个驯服的工具”[28]。在这里,我们不妨用“人民司法”来指称新中国以来法院系统所扮演的这一政策执行角色[29]。当然,必须明确的是,“人民司法”理念在不同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更加强调的是动员、改造群众以及宣传、支持革命的一面,所以此时特别强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30]。有时为了更好地达致保护、动员、改造群众拥护革命之目的,甚至主张“法庭是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群众自己也必须执行;……”(为表述的方便,不妨称之为人民司法理念“版本1”)[31];在和平建设时期,则更加强调“司法为民”,此时一般不再刻意强调司法由“人民”掌控,而只是强调其圭臬、评判主体是“人民”即可,所谓“一心为民。落实司法为民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做到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坚持能动司法,树立服务意识,做好诉讼指导、风险提示、法律释明等便民服务,避免‘冷硬横推’等不良作风”[32],或人民法院应“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紧紧抓住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期待改进的司法问题……”[33](“版本2”)。 可以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以及历史经验,无论我们给予“人民司法”理念及相应实践怎样正面的评价都不为过。然而,“人民司法”理念的可能局限也恰恰在于它仅仅具有历史合理性,具体说来,这种合理性表现为:第一,在国家正式司法力量不甚强大,在需要动员更多群众支持革命的年代,“人民司法”几乎是司法价值最大化的惟一有效途径;第二,在社会分化程度并不甚高,司法机关专业化程度不够以及司法官专业素养偏低的改革开放前30年,“人民司法”理念可以、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本来,如果司法机关本身就不够专业,必然意味着它的所作所为将很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进而当然也就意味着它本不应该具有所谓“司法的”公信力,但人民司法理念的宣传和实践,却通过一种专业问题的非专业处理之置换机制,使司法工作获得了非专业民众的认可。这一方面使得大陆地区的司法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并没有明显或严重的公信力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也确实使人们忽略了司法长期以来的非专业化问题。显然,只有按照新中国法院系统秉持的“人民司法”理念,我们才能对法院系统积极推行片面结果导向之错案责任机制作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等之所以积极并大力推行错案责任机制,恰恰是它仍然遵循着人民司法的逻辑来思考、应对相应问题,因为诚如前述,一方面,错案责任机制存在根本的逻辑缺陷;但另一方面,按照朴素的生活逻辑,“错案”显然并肯定是存在的;再一方面,人民司法的逻辑又可以缓解司法本身因专业性不足本应带来的包括司法公信力欠缺等在内的各种问题。因此,为了让人民满意,为了保卫司法公信,就必须、也只能回应社会大众的相应关切,至于这一关切在专业逻辑上是否讲得通,反而成为了不那么重要的议题,所谓“错案是客观存在的,法官要对自己的审判行为和案件质量负责,裁判出现错误,倒查法官是否有责任也无可厚非”[34]。申言之,“人民司法”理念可能正是当前法院系统明知“错案”以及错案责任机制存在种种问题,却坚持推行之的真正且主要之动因。这一方面决定了错案责任机制其实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而也揭示并解释了何以错案责任机制本身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却仍然被一次次地重申:当司法本身的专业性不强时,通过诉诸人民司法理念的错案责任机制,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发挥规训司法任意并加强其公信力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却也揭示出时至今日确实不宜继续推行错案责任机制,或至少是当前这种仅以人民群众是否感性上满意为圭臬的错案责任机制,因为第一,由于当前错案责任机制的真正动因是人民司法理念,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它错把司法这一专业活动建立这朴素的大众司法观念基础上,而这很容易导致司法队伍已经较高程度专业化的今日中国法院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具体说来,首先,大量“科班出身”的专业化司法官几乎注定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某种专业标准办案;但其次,按照人民司法的要求,法院的专业工作却要接受社会大众的检评,而后者秉持的却仍然是朴素的、日常生活标准。虽然在有些情形中司法的专业逻辑可能与朴素的生活逻辑并无明显的冲突,此时,司法官按照司法的逻辑办案亦会得到不错的评价进而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另一些时候,司法的专业逻辑则可能与朴素的生活逻辑发生冲突,此时,民众一定会给予司法以负面评价进而当然也就意味着司法公信力的下降[35]。此处不妨以当年著名的“佘祥林案”[36]为例来揭示这种冲突:在该案中,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然而,佘祥林服刑若干年后,作为本案受害人的佘祥林妻子“亡者归来”。于是,舆论哗然,人们普遍认定法院显然判了个错案,人们作出这一判断的逻辑是:既然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佘祥林,那么,当他妻子事实上仍然还活着时,则法院必定判了一个错案、冤案甚至可以说是假案。笔者并不认为这一逻辑本身有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生活逻辑。然而,如果按照司法的专业逻辑,则佘祥林妻子是否活着回来并不必然意味着这是个错案:因为一方面,有可能当时所有证据都指向佘祥林杀人,并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之“确凿充分”的程度,此时,即便事后被害人活着回来,也并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罪名的成立,或至少不必然意味着这是一个所谓“错案”。更重要的其实是,另一方面,按照我国刑法,故意杀人罪罪名能否成立,本也不以被害人真实死亡为构成要件(是否真实死亡可能只是既遂与未遂的区别)[37]。不难想见,当司法逻辑与生活逻辑相冲突时,司法官们几乎注定将陷入如下困境:若按司法逻辑办案,则人民不满意、司法公信力下降;若放弃司法逻辑,先不说可能最终仍会因各种专业监督措施的存在而被改判,也不说此时还是否为名副其实的“司法”活动必成疑问,对司法官而言首要的困难将很可能是,连自己的专业良知这一关都过不了。 当前这种以人民群众是否感性上满意为圭臬的“人民司法”理念(版本2)本身已不合时宜,除了它必然会带来如上司法困境外,也因为第二,今日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并且深深地依赖于当前的全球一体化格局,这意味着今日中国大陆地区法院面对的任何一个案件,其利害关系人、尤其是其评判者都很可能是除国人以外的“地球人”。尽管作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我们并无政治义务去关切所有地球人的所有司法需求,但除非我们准备重新闭关锁国、退出全球化进程,否则,为了促进全球资源的中国利用,很大程度上就必须给予任何一个案件以符合抽象、普适司法逻辑之对待[38],因而也就注定无法单纯以“人民满意”作为司法的惟一圭臬。因此,尽管按照本文的分析,我们应当废止当前这种片面结果导向的错案责任机制,因为“错案”是一个不符合圆洽专业逻辑的术语,但必须予以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定错案责任机制曾经的经验价值,对此致机制的合理定位或许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错案责任机制是新中国规训司法任意历史进程中的一环,因此,尽管它曾发挥了重大价值,但毕竟也仅仅是一环,并且应该仅仅是一环,因而注定要被翻越。这就正如“人民司法”理念的历史:虽然它的特定版本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当它由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因素转变为减损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时,基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面向和需要(法治的专业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片面牺牲法治的专业逻辑),我们就只能“走进新时代”,也即赋予“人民司法”理念以新内涵,进而根据新内涵来重新审视、检讨包括错案责任机制在内的各种司法制度安排。[39]事实上,考虑到正如前文所述,“人民司法”本也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并且事实上已发生过从“人民作为司法主体”到“人民是否满意”这样的转变,因此,面对新时期、新情势,不仅仅有特别的必要赋予它以新的内涵,而且这种新内涵的赋予实际上也将反过来加强“人民司法”理念的活力。那么,这新内涵应当、可以是怎样的?一言以蔽之,即:在坚持司法活动专业逻辑的基础上、前提下寻求人民群众的认可、满意(“版本3”)。如果检索最高决策层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近些年的官方文件就可以发现,这种新理念实际上已经有了萌芽并呈现出茁壮成长之势,譬如党中央决议就指出,“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力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一号召意味着法律及其内在逻辑是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的”,在专门指涉“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问题的部分亦特别明确,人民司法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全程掌控司法,而是从目的上 “坚持司法为人民”,从具体措施方面则强调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部分领域或环节的参与,所谓“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40];如最高院就曾经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公安部也要求,“要进一步强化依法办案意识,通过组织开展冤假错案剖析点评和“回头看”等活动,教育广大民警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时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绝不能因为舆论压力、领导意志、立功心切等,突破法律底线,违法违规办案”[41]——可以看到,在这些文献的这些表述中,既不像“版本2”那样将朴素的“民意”(舆论)置于“法律”(专业)逻辑之上,并且也不再像“版本1”中那样强调“司法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此处尚需明确的一点是,尽管本文将此前我国力推错案责任机制的动因归之为“人民司法”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从外围呼应、助推着这一制度实践。事实上,包括早年司法官素质不足够高、诉讼程序设置不尽合理、诉讼理念方向偏差、甚至单纯政治动员的需要等各方面因素,都或多或少对于推动错案责任机制的建立及运行起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必须马上予以明确的是,所有这些其他因素,都可能不是错案责任机制运行的内在动因,而只是外围影响因素而已。四、因应思路:以行为-程序监控替换结果-实体导向在上文中,笔者得出了一个可能看上去令人惊诧的结论:法律的世界不存在错案。这个结论之所以可能令人惊诧,是因为它很容易从逻辑上最终引致这样的担忧:如果法律的世界不存在错案,那岂非我们根本无法监控法官的任意?另外,这一结论似乎也与如下经验相悖:已经有法官(或其他法律人)因枉法裁判等原因而受到了惩办,并且显然他们并不是被冤枉的。对于如上担忧或质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回应,而这些回应其实也正是本文对于错案责任机制的处置建议:第一,如果一个法官专业能力足够高明、但人品却又足够的坏,他本来就可以“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并且还总是有理,或至少从法律角度看总是能够讲得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了德萧维兹(Alan M. Dershowitz)的如下略显无奈的慨叹:“(对于司法)人们有理由持怀疑的态度,而怎样才能使他们相信他们对大法官的信任再也不会遭到破坏了呢?我们必须保证,只有那些最为正直和卓越的人才有机会执行美国国家制度中这独一无二的职能(审判、尤其是司法审查),这是唯一的方法”[42]。与此同时,第二,我们才有特别的必要设计各种程序来规制、制约法官的任意,因为最终的司法结果是一个典型的主观造物故而无法预先设定实体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司法人员的行为以及办案程序来实施规训、监控。这其中,除了当前我国已经在做的诸如审判监督程序、上诉程序等以外[43],笔者这里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必须大力推动法官的判决说理,至少他必须就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一定的说理,而不能用“不予采信”或“本院认为”等不讲道理的方式简单粗暴地提出自己的结论: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特定的重组、回构案情之思路?换言之,为什么律师、检察官或其他什么人的别种重组思路没有被采纳?他为什么赋予某个案件事实以这种意义而非另外一种意义?当下案件为什么应该适用A法的第n条而非B法的第m条?当前已被选定的某个或某些法律条文,为什么一定要作这样的理解,而非那样的理解?等等。如果在每一个判决中,或至少在每个有争议的判决中,法官都必须就如上方面作出详细的说明、论证,那么,就将极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解法官的任意和恣意。第三,部分法官之所以最终被以枉法裁判等罪名论处,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明显违背程序判案,或明显违背法官职业操守、行为规范办案,譬如接受诉讼某方的宴请、行贿等。此时,他之所以被追责,可以不必是因为他的具体审判结论被认定为错,而仅仅因为这些违背程序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论处。二是一个法官并没有任何违反程序、伦理或行为规范的事实,却仅仅因为其结论被后审推翻而被追责,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只能说:该法官不过是前述强盗逻辑及其实践的受害人——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存在这种被追责[44]的事实本身就得出结论并进而认定他枉法裁判了。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推敲前文提及的几个设置错案责任机制的文件,就可以发现其真正指向的也仅仅是如上第一种情形[45]。换言之,我们真正应当追究的只是程序上可见、可控的错误行为或事实。因此,再次强调,第四,当笔者反对“错案”提法[46]、主张废止当前的错案责任机制,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无需规制、监控法官的任意,毋宁说,笔者的真正主张是:我们只能从行为、过程、程序角度监控法官,而无法从结果上制约、要求法官,也不应从结果上监控、追责。换句话说,笔者否定的只是片面结果导向的司法责任制,而非司法责任制本身——如果一种司法责任制建立在行为、过程、程序基础上,并作出符合其他司法规律、专业逻辑的具体制度安排,就值得给予特别的尊重[47]。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真正要做的其实不是继续完善所谓错案责任机制,而是完善各种法官职业伦理、行为规范以及诉讼程序。最后,尚有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前的司法改革会出现包括错案责任机制等明显具有钱穆制度陷阱意味的现象?如果对比1998年《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我们会发现,其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按照本文逻辑,其中真正有意义、能够成立(从程序、行为角度追究司法责任)的部分仍然存在,其中不能成立、无甚意义(从实质、结果角度追究司法责任)的部分同样仍然存在;并且,其中能够成立的部分其实在《法官法》、《刑法》甚至《公务员法》中早已经作出了规定。为什么会反复进行重复的制度建设并且犯同样的错?这除了前文述及的“人民司法”这一强大动因外,合乎逻辑的可能解释有二:其一,我们在设计相应改革制度时忽略、无视了既有法律规定,这样的改革策略当然十分不妥,因为它随时可能让改革成为法外飞地,而这对于法院这一“法律的守护神”来说尤其不妥;其二,我们对于某些看上去理所当然但实际似是而非的事物采取了一种不思的态度,这当然同样十分不妥,为什么?或可借用密尔(J. S. Mill)当年的如下告诫来回答,“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过半数的原因”[48]。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本文所谓的“行为、程序导向的司法责任制”就不会沦为新的“钱穆制度陷阱”?这主要是因为,依据本文逻辑设计的是一种与既有的片面结果导向之错案责任机制并不相同的新制度,并且,这种新制度并非为了让旧有的制度得到更好的落实,而是为了取代旧有制度,因此当然也就不可能陷入“病上加病”的状况。也因此,即便这新制度可能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也不是因为它堕入到“钱穆制度陷阱”之中,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本文原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专业文章支持错案责任机制(以“中国知网”检索范围为限),并且即便是这些文章,也承认该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典型的相关文献如李少平:《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应当处理好四个关系》,《法制日报》2016年2月24日;朱孝清:《冤假错案的原因和对策》,《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等。[②] 就笔者的检索而言,最早的相关正式官方文件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纪律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5月),其中规定,“在审判活动中主观臆断造成错判的,给予降级或记大过处分,对其他责任人给予记过以下处分”(第15条),“在审判活动中因失职造成错判的,给予记大过以上撤职以下处分”(第16条)。[③] 李少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应当处理好四个关系》,《法制日报》2016年2月24日。此处之所以注明作者职位,是想通过这种注明来明确作者的制度设计者身份。[④]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按照现有规定,办案法官的主观过错并非错案的构成要件,相应规定强调的仅仅是,如果法官不存在相应主观过错,则“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详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28条)或“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详可见《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2条)或“法官、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11条)。这种精神旨趣在中央政法委领导最近一次(本文定稿日期为2016年11月)的讲话中再次得到了体现,所谓“人的认知能力、科技发展水平往往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据司法职业特点,对办案中存在的瑕疵,如果不影响案件结论正确性的,不宜追究司法责任。由于司法是衡平和裁断的艺术,因对法律的理解或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不一致造成错案的,也不宜轻易追究司法责任”(孟建柱:《坚定不移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开展》,《法制日报》2016年10月20日)。[⑤] 相关典型文献,可参见朱孝清:《对“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几点认识》,《检察日报》2013年7月8日;胡常龙:《论检察机关视角下的冤假错案防范》,《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李建明:《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张保生:《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等等。[⑥]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7页。[⑦] 在本文中,“后审”是相对“前审”而言的,它可能是上诉审,也可能是再审,或任何其他在时间顺序上后来发生的审理。从制度逻辑及实践经验看,后审结论总是优于、并可推翻及取代前审结论。进而言之,如果“前审”是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如公安机关),那么,对公安机关而言,移送审查起诉之审查主体(检察院)就是“后审”;相对应地,相对公诉机关检察院而言,一审法院是“后审”。[⑧] 相关典型文章如刘品新:《错案责任追究制:看上去很美》,《人民检察》2005年5月(上)期;魏胜强:《错案追究何去何从?——关于我国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思考》,《法学》2012年第9期;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董坤:《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治对策》,《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胡常龙:《论检察机关视角下的冤假错案防范》,《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以及前引诸篇文献等。[⑨]此处或有必要提及笔者的一个不解之处:从语文上讲,所谓“事实真xiàng”之“xiàng”应该是“相”而非“象”才是,因为按照现代汉语的一般解释,“象”具有的是“形状、样子”或一种四肢动物之意,而“相”才是“相貌、相态”之意,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立法者偏偏如此任性地造一个“真象”(按字面意思,这个词指的应该是“一头真的象”)用来指称案件事实。关于现代汉语中如上诸字、词之用法,笔者参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版),第1490、1491、1730页。[⑩]表面上看,我国实行的是“四级两审终审制”,但由于“可无限再审”这一尾巴的存在,使得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无终审制。无终审制度设计的逻辑基础只能是:每一个案件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并且这答案只能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因此,只要“发现确有错误”(《刑事诉讼法》第243条),案件就可以、也应当进入再审。[11] H. L. A.Hart, American Jurisprudence through English Eyes: 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Dream, Georgia Law Review, Vol. 11 (1977).[12] 【法】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13]波普尔(K. Popper)经由一条不同的思路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所谓“不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利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赋予它以意义”【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417页。[14]“证据”与“案件片断”都属于法官收集之“痕迹”的范畴,两者虽有重合但侧重有所不同:证据强调的是“具有证据资格”的痕迹,而案件片断强调的则是“是否属于案情的构成要素”的痕迹。举例而言,一般并不认为案件发生时间或场所(特定案件除外)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显然属于案件片断,并且事实上法官在重组案情时显然会把时间、场所因素考虑进来;相对应地,证人证言不属于案件本身的片断,但却属于证据。[15]非常有意思的是,不知何故,当前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尽管有些并没有明确宣称,但其实都或明或暗预设了一个“人”可以达致的终极、标准答案,这当然极大地降低、甚至消解了这些研究的说服力。相关典型文献,除前文所援引之国内文章外,还可参见【法】弗洛里奥(René Floriot):错案》,赵淑美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美】佩特罗(Jim Petro)等:《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苑宁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劳丹(Larry Laudan):《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英】卡德里(S. Kadri):《审判为什么不公正》,杨雄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16] 【德】加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3页。[17]“可错性”(fallibility)一词源自皮尔斯(C. S. Peirce)的科学哲学。根据皮尔斯,所有的自然科学结论都可能被后来的发现、认识所推翻;后来,波普尔(Karl Popper)顺着皮尔斯的这一思路提出了著名的证伪观点,即只有那些可能被证伪的观点或结论才是科学的(详可参见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ed.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i: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 尤其是其中的第1. 120节“The Uncertainty ofScience Results”;关于皮尔斯可错性理论及其影响,可参见TedHonde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 267-268)。本文此处借用这个词语,主要是用来表达前审结论所必定具有的可推翻性。[18]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20] 事实上,遍览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立法规定,并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婚姻,因而根据私人权利可推定之原则,同性恋者本也可以申请登记结婚。[21]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2年5月11日联合发布,201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第3.1条。.[22] 【美】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代译序”第6-7页。[23] Brown v.Allen, 344 U.S. 443, 540 (1953).[24]也正因如此,当前几乎所有相关理论文章动辄探讨结果意义上的“错放”更可取还是“错判”更可取,或探讨所谓“错案”成因或错案应对策略(典型者如:闻一:《错判,还是错放?——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保生》,《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9期;黄士元:《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刘品新主编:《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8-11 页;张保生、张晃榕:《检察业务考评与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4期;以及本文前引诸文献等等),就实在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所有这些讨论都建立在一个不能成立的“错案”观念基础上。当然,必须立即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说它们的探讨完全没有价值,应该说对于完善办案程序、提升办案质量,相关的研究、建议其实具有相当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把既有研究中对错案成因及应对策略的探索看作对提升当前办案质量(也即增强结论可接受性)的探索,则这些研究当然具有很高的价值。[25] 令人担忧、或许同时还应令人羞愧的是,“后审改判则意味着前审错误”正是当前我国实践中认定前审判决是否是错案的实际做法。尽管在实践中基于各地法院具体操作的不同因而被后审改判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前审法官被追加多么严重的责任(相应经验考察,可参见王伦刚、刘思达:《从实体问责到程序治——中国法院错案追究制运行的实证考察》,《法学家》2016年第2期),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逻辑上讲,只要我们承认错案的存在,只要我们继续当前错案责任机制的实施,大概也只能如此——我们总不能用前审作为判准来认定后审是错案吧?[26] 【(前)南斯拉夫】达玛斯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27] 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天下-国-家”同构之特质,有关这一点,得到许多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认同。相关典型文献,可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3-184页;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9页;等等。[28] 《坚决贯彻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精神》(社论),《人民司法》1958年第14期。[29]关于“人民司法”的缘起及其本身表现,可参见吕伯涛:《董必武:人民司法传统的缔造者、传承者和发展者》,《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陈洪杰:《人民司法的历史面相——陕甘宁边区司法传统及其意义符号生产之“祛魅”》,《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何永军:《人民司法传统的表达与实践(1978-1988)》,《司法》第3辑(2008年);等等。[3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第17条。一般认为,《共同纲领》第一次以最高决策文件(《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当时的临时宪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人民司法”概念。[31] 《谢觉哉同志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摘要)》(1949年1月),《人民司法》1978年第3期。[32] 《法官行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4日发布,2010年12月6日修订)第5条。[33]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25日)。[34] 前引李少平语。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某次国家检察官学院开学典礼上亦确认了这一点,所谓“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相关报道见http://www.spp.gov.cn/zdgz/201409/t20140904_79635.shtml, 2016-3-1。[35]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一篇论文中,笔者曾特别强调,只要社会大众仍然惯于以生活逻辑来评价司法,所谓司法公信力可能根本就是镜花水月。详可参见周赟:《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经验维度——来自司法一线的调研报告》,《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3期。[36] 关于“佘祥林案”案情本身的简要介绍,可参考“百度百科”词条“佘祥林”,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RrYplfyxZHWTxhmiPG7h03X3olVIcC-kGYV5ZAbItzpjxkNoTE5hJqW5tuln54FRfgRjCKK5QwfEAlwCCHTUa, 2016-3-10。[37] 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假设:如果承认错案的存在也承认本案是个错案,那么当佘祥林太太活着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发现,是否就意味着本案就不成其为错案了呢?若果真如此,则错案的判准显然过于偶然,因为活着的佘祥林太太会否被发现实在是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另外必须明确的是,笔者此处无意为佘祥林案再翻案,事实上,这也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在没有掌握更多的经验材料之前本也不宜草率评论案件结论本身)和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只是以该案为例来说理。[38] 有关这一点,笔者主要受益于吉登斯(AnthonyGiddens)关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之思考、分析。有兴趣者可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7页。[39] 此处或许会进一步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民司法”这样——按照本文逻辑——明显专业上讲不通的司法理念在历史上会长期存在并且甚至还某种程度上维续着司法系统的公信力?这除了前文提及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实质正义或者说结果主义导向等原因外,也可根据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良知”(consciencecollective)理论进行解释、理解。涂尔干认定,正是集体良知构成了一个社会的黏合剂和终极契约,说它是终极的,是因为它本身是否逻辑上合理、可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一个社会形成了相应共识并深深烙入民众的思想,它就将成为事实上的是非善恶标准,直到社会转型形成新的集体良知为止(【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72页;如欲更为清楚地把握涂尔干相应理论的脉络、逻辑,可见帕森斯[T. Parsons]:《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380页;而这种理论的法理学版本,则可参见Lord Patrick Devlin, Morals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Ronald Dworkined., The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6-82)。显然,按照涂尔干的这一经典判断,则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民司法”理念基于迫切的现实政治需要,并借由强大的政治宣传机器而被塑造成为新中国关于司法的集体良知这一事实本身就解释了它的“有效性”。[4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41]请分别见《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0月9日)第一条第2项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公安部,2013年6月5日)第一条(着重号为引者加)。[42] 【美】德萧维兹:《大法官的偏见》,廖明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28页。[43] 非常有意思的是,许多论者一方面并不反对加强各项针对审判的监督程序,另一方面又主张法律的世界存在惟一正确、客观答案,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两者其实是相矛盾的:如果法律的世界像自然科学的世界一样,则根本就没有必要设计、推行各种必定需要耗费各种成本的诉讼程序——事实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的数学老师在计算算术题或我们的物理老师在做物理实验时必须履行何种程序、仪式?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不必如此,原因就在于同一个算术题,有且确实有惟一正确答案,并且谁做都是如此;而法律的世界恰恰相反,因此,法律的世界才必须仰赖程序来制约法官,让他的决断尽可能地具有可预测性。[44] 此处所谓“责”,仅仅指依据法律而承担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而不包括法院内部的组织责任(如年终评优资格的丧失等),因为如果仅仅是组织责任(当然必须是法律允许的),则特定组织设定相对严苛的标准也并无不可。[45] 当然,在有些基层司法、警察机关所设计的错案责任机制中,采取的是更为严苛的标准,而把如上第二种情况也包括进来(对相关实践的介绍,可参见张保生:《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但显然,按照本文的逻辑,这种做法明显不合理。[46] 笔者尤其反对在专业领域把“冤”、“假”与“错”联结合并成“冤假错案”一词。从专业逻辑的角度讲,打官司就必定有人赢有人输,对于输方(败诉方),任何判决结论可能都是冤、假因而错的。考虑到几乎所有案件(调解结案的除外)都必定有败诉方,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任何判决在部分人看来都一定是冤假错案,就正如任何判决在部分人(胜诉方或支持胜诉方主张的人)看来都一定是“实真对案”一样。[47] 有学者曾从“错案追究制主要是源于司法系统自上而下的压力”、“面临法官司法权力和责任的不平衡,法院也需要保护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实践当中法院往往事实上也将制度层面的结果导向之责任追究机制落实为程序导向的责任追究做法等几个方面来证成何以应当在法院追责过程中“从实体问责到程序之治”的转变(详可参见王伦刚、刘思达:《从实体问责到程序治——中国法院错案追究制运行的实证考察》,《法学家》2016年第2期)。应当承认,相应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与此同时,必须立即指出的是,这样一种纯外围的、纯经验式的论证,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成何以法官问责必须走向“程序之治”,而只有基于内部立场的、符合逻辑的分析及论证,才可能真正证成此一命题。[48]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