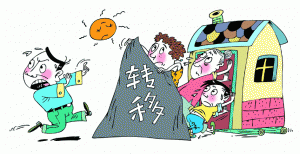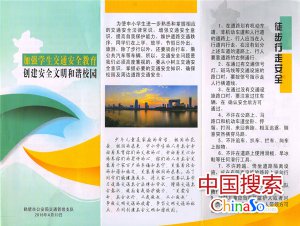|
首先,从案涉业务的磋商过程看,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是在当地政府的行政协调下参与了案涉业务的联系和沟通过程,并非案涉业务的真正买受人。根据原一审、二审和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椰林公司的前身槟椥厂是儋州市外贸总公司与越南方合资兴办的工厂,是儋州市政府确定的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为解决前期生产资金紧缺的困难,槟椥厂于1997年4月28日向儋州市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申请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的请示》,请求政府帮助与银行协调贷款400万元人民币给该厂作为流动资金,销售产品后分期还清贷款。该报告经时任政府主管领导批示请儋州人行、儋州建行给以支持。嗣后,槟椥厂于1997年5月5日向儋州建行打报告,恳请儋州建行赊借白糖(一级)1000吨以缓解前期生产资金紧缺的困难,待生产转入正常销售产品后,方可与该行结算。1997年5月21日,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的时任行长分别在该报告左下角写明“儋州市春江糖业有限公司,该厂报告上的情况属实,经与建行商量,同意先提糖,后办理有关手续”、“同意”的内容。同日,春江糖厂时任领导黎有章在该函件的背面上方批示:“同意按两家银行的意见办理,按每吨叁千玖佰元计,以后由财务部与银行结算(厂库交货)”。本院认为,单纯从上述买卖合同磋商过程中的若干行为外观看,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在磋商中的确具有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参与的某些特征,但解释和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离开我国经济生活的现实背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的企业解决资金困难而与相关单位联系开展协调工作,观念上被认为是政府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在接到任务后,协调当地国有企业为政府重点项目提供支持,观念上被认为是通过调剂余缺服务地方政府工作大局的正常做法。在联系和协调的过程中,儋州人行作为银行业监管派出机构,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协调商业银行调剂资金余缺;儋州建行作为商业银行,按照地方政府和人行的要求利用其所掌握的客户资源,就槟椥厂的需求与春江糖厂联系;春江糖厂作为儋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有企业,经两家银行协调后为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提供其需求的生产资料加以支持。在这一系列的协调行动过程中,各方的角色和地位是明确的。质言之,当时我国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是因政府的要求才与春江糖厂进行协调,其自身既无购买白糖之意愿,亦无相应的经营范围,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应属于按照行政指令进行协调和联络的角色。也只有立足于这一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才能够理解春江糖厂为何在既没有预付款、亦没有任何还款保证的情况下,即按照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的协调意见向槟椥厂提供了案涉白糖。 其次,从案涉合同目的看,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并无与春江糖厂订立买卖合同的意图。本案基本事实表明,槟椥厂是因资金出现困难而向政府报告请求予以解决,在当地政府的要求之下,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均同意并将报告批转给春江糖厂。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批转报告等行为系协调当地国有企业为政府重点项目提供支持,是就槟椥厂的需求与春江糖厂联系,而非替代槟椥厂与春江糖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就交易目的而言,槟椥厂的最初与根本目的在于解决资金困难问题,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正是在无法发放贷款但又需要协助政府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促成春江糖厂与槟椥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若其意图系先与春江糖厂订立买卖合同而后再赊给槟椥厂,则不如直接向槟椥厂发放贷款来完成政府要求,此于其自身而言,不仅更为稳妥直接,而且有利可图。若如春江公司所主张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行为目的在于与春江糖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姑且不论该行为违反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即便从合同目的合理性而言,该行为也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故本院难以从本案事实推定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具有与春江糖厂订立买卖合同的主观意图和目的。 再次,春江公司在案涉赊销合同成立时及成立后对其合同相对人是槟椥厂均存在明确的主观认知。本案各方当事人在槟椥厂报告上所留下的文字,较为完整地反映出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在当地政府的行政协调之下,为解决槟椥厂的资金需求与春江公司联系并商请该公司向槟椥厂赊借白糖的磋商过程,应当作为探究当事人在行为当时的真实意思的基本依据。根据该报告上各方写明的文字内容,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在联系和协调的过程中,已经指明了白糖的需求方为槟椥厂,春江糖厂对此是明知的。且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槟椥厂的负责人羊东广于1997年6月10日提取了案涉白糖,并以自身的名义向春江糖厂出具了货物收据;春江糖厂在其1997年8月31日的明细分类账中将案涉白糖款390万元的付款人记载为椰林公司(槟椥厂)并于1997年11月10日以槟椥厂为收货人开具了四张销售发票。本院认为,槟椥厂以自身名义出具货物收据,春江糖厂的账目记载及开具发票的行为,充分证明了双方当事人在案涉赊销合同实际履行的过程中对于债权人、债务人身份的主观认知。因此,无论是在案涉赊销业务的协调过程中,还是在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之后,春江公司对于该笔业务的货物买受人是槟椥厂这一事实在主观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虽然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在槟椥厂的报告背面写有“后办理有关手续”、“具体结算手续后办”,春江糖厂的领导亦注明“以后由财务部与银行结算(厂库交货)”等内容,但并不宜由此得出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应为案涉白糖支付货款的结论。如前所析,儋州人行和儋州建行的批示等行为只是意在为落实政府行政指令而进行磋商和协调,而最终是否同意提糖要求和结算方式等,仍由春江糖厂自主决定。当然,作为国资委下属的国有企业,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支持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也是企业的重要任务,但这并不妨碍其依据自身经营状况提出交易的具体方案和意见,诸如买卖价格的确定、买卖数量的增减等。本案事实已经表明,春江糖厂提出按每吨3900元计的合同价款。关于报告所载批示所提及的结算问题,槟椥厂在报告中明确说明先予赊购,待企业经营好转后再与银行结算。据此,春江糖厂是在明知供糖对象且知悉结算方式的前提下同意按照银行协调意见办理的,故不应将通过银行结算方式解释为银行具有购买白糖并为之付款的意图并由此认定银行为买受人。如果银行有代槟椥厂垫付货款的意图,如前所述,其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向槟椥厂发放贷款来完成政府要求,而无需通过调剂资源方式促成槟椥厂与春江糖厂的合作。因此,本院认为,将案涉白糖的实际需求方和使用方槟椥厂认定为白糖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更符合当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