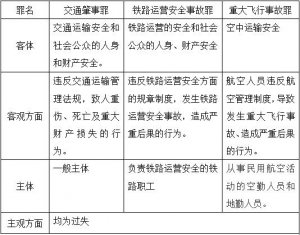没有“裁判者良知”则无“良法”
来源:边缘漫步 作者:边缘漫步 发布时间:2017-06-07
摘要:文:朱祖飞今年1月份,我在微信上阅读了谢晖先生《法治思维的九个向度》一文,留言道:“阅读了此文,没想到与谢老师的分歧已经大于共识,当年是看谢老师等人著作逐步走入法理学的”。谢老师回道:“期待祖飞批评。还有,批评时请关注我的两个体系——法哲学
|
文:朱祖飞今年1月份,我在微信上阅读了谢晖先生《法治思维的九个向度》一文,留言道:“阅读了此文,没想到与谢老师的分歧已经大于共识,当年是看谢老师等人著作逐步走入法理学的”。谢老师回道:“期待祖飞批评。还有,批评时请关注我的两个体系——法哲学体系与法律哲学体系的区别,否则,或许会远离我的主张”。与谢老师的分歧大于共识,其中第六向度占了很大的比重。谢晖教授第六个向度主张,“技术决定价值(道德)——技术优位”。他认为:“法律是‘公正善良之术’,这是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斯的一个重要结论,可见,他把法律这一事物当作‘术’来看待。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谈到‘术’这个词时,往往以为‘术’是次要的,即工具理性是次要的,价值理性才是重要的,当年我也持这样的看法。1994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法律工具主义评析》,专门剖析并反对法律工具主义。现在回过头来,当时写的这篇文章还是多少有点愣头青。那么,当法律技术和道德价值相冲突时,究竟要秉持技术优先还是价值优先?我现在的主张是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生冲突时,一定要强调工具理性、或者技术理性优先。这里涉及到刚才张先生谈到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刑法(刑)和民法(礼)相分立的背景之下,强调道德(礼)优位于法律(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法律已全方位地介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再这样强调就名不副实了,再强调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不但是说外行话,而且会在德治的名下,解构法治。所以我认为如今对这两者的关系,要强调一是以德立法,我们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刚才徐先生就讲了要建立以德立法的良法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一旦建立了,则要毫不迟疑地强调以法统德。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特别对于公权主体而言,法律之外再没有其他道德。一切道德,不论是私人道德、职业道德、公共道德还是政治道德,都被结构在法律当中。这方面我有一本书叫《法治讲演录》,其中有一讲叫‘德性的法治’,对此有专论,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总之,要强调法治思维,就必须强调法律技术优位于道德价值。”谢晖教授思路相当清晰,良法统德。但是,这是高贵之梦,也是一厢情愿,根本无法实现,否则,就会走向专制之路。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就是良知统法。若司法独立,法官恪守良知,不管制定法多么荒唐,也会走向良法之治,判决公正。否则,不管法条多么美好,也是走向恶法之治,出入人罪。第一,“良法统德”,难以可能。2012年爆发的方韩之争,方舟子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侵权呢?《侵权责任法》有明文规则,主要就是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但是不同观点仍然相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认为:“迄今为止,无任何证据表明韩寒存在著作权纠纷,舆论应到此止步,这就是私权的最后堡垒,是打着言论自由、公共利益、诚信任何旗号的行动边界。而疑韩人士因其文本分析等各种手段的目的是指向韩寒有人代笔———也就是说要证明一个作家是骗子,从而严重突破私权保护的底线,极端粗暴地践踏了一个作家的尊严和人格”。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对本案拟判是:方舟子称韩寒的文章系他人代笔,无事实依据,但文章未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驳回韩寒的诉讼请求。此判决,还韩寒以清白,给言论以自由。”方舟子坚信自己的推定,确信韩寒有他人代书行为,主观上到底是否具有“过错”呢?萧瀚及路金波等等许多人认为,方舟子是打着逻辑推理的旗号,行诽谤之实,这就是无厘头的推定,纯属过错行为;有人认为,依据比较充分,足以推定成立,根本没有过错。既有“过错”的概念,又有事实的行为,为什么难以清晰得出方舟子是否“过错”的这一结论呢?传统三段论在这里面临着考验。传统法学三段论认为,通过逻辑三段论就可以将待判断的案件事实“涵摄”到法律概念之下,无须评价。同样的法条(大前提)及事实(小前提),不管是谁,都可以依照形式逻辑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但是,现实告知我们,这根本不可能,不管认定方舟子侵权与否,都需要裁判者主观价值的加入。这就是裁判解释学的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需要裁判者的价值补充。一旦进行价值补充,司法实际已经成为立法了。所以,许多的案件,法官实际上都在“造法”,只不过有些法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天下只有类似的案件,没有一样的案件。每一个案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具体的案件,有它的具体语境。从理想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案件都应当对应着一个特殊价值评价结论。在价值补充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补充方法,就会走向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原教旨主义重字面的解释就会走向恶法,走向专制。在日本,强调利益衡量,由法官依照良知进行判断,如星野英一说:“当法律解释出现复数结果的时候,必须要彻底搞清楚何种价值以及何种人的何种利益在实际上是如何被实现、保护或者相反被压制、否定的,但这最终要通过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来决定。” 也就是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如何进行取舍,需要解释者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为了确保解释者的中立性,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1946年日本宪法第76条第3款明文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与大陆法系信赖法官良知的不同,普通法系则有陪审团良知的加入,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里,陪审团成员就是依照良知和法官指示作出判断,所以,才有“陪审团的不法是法律在其实际运作中的最伟大的矫正器”之说。当然,前述仅仅举出方韩之争的例子,一叶而知秋,现实中办理案件都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补充及取舍。即使是类似于先例的简单案件的判决,裁判者内心其实也已经作出了案件事实不属于例外情形的价值判断。非类似于先例的案件,如许霆案件,如“微信”案,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所以纯粹依靠法条,将寸步难行。怪不得一位有仲裁员身份的法学博导感叹,参与仲裁才知道,现实中案件极少与法律条文一一对应。我曾经问一位民法学者如何进行仲裁案件,他说要先进行直观判断。纯粹法条的逻辑演绎,没有裁判者价值介入,是无法解决实际案件的。若无良知统括法律,即使制定出良法,也会走向法律的背面。所以,法官的法律素养及人格良知的独立,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第二,单纯的法律条文,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部门法教义学的训练,单纯的法律条文,就是天书,比老子的《道德经》更难理解。一旦进行了部门法教义学的训练,法律条文就会渗透了法学专家的个人意见,各师各法。而且教材中的例子,都是抽象的,典型的,难以与现实一一对应。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纯粹的法学理论演绎,对立的原则之间经常会走向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比如诚实信用和私法自治原则,各自成立,但相互矛盾;交易安全原则和保护财产安全原则,也是如此。一些具体规则也是一样,比如《合同法》第114条规定一方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合同法》第91条第二项规定,合同解除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那么,合同解除约定违约金的条款是否也一并解除呢?要不要支付约定的违约金呢?这就不是逻辑所能解决的问题。再如《合同法》第114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这一条款就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违约一方当事人没有到庭参与诉讼,或者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的离谱,法官能否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主动予以调整呢?司法实践也有法官作出肯定的答案。一部民法史,就是一部法官发现矛盾法律规范的发展史,如侵权法从过错责任原则,逐步发展出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这些都是先司法后立法的,都是法官依照良知予以突破现行法的规定。否则,坚守法条,必然脱离实际。二律背反,就是理性的超经验运用所出现的幻相。自以为部门法教义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其实无非就是自以为是的片面独断而已。这就是法律有规则必有例外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也可以据此解释,为什么研读部门法学的书籍,读的越精细,就越发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越脱离形式逻辑。为此我十分赞同吴经熊先生的以下观点,抽象的法律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在真实的世界中存在的只是个别特殊的法律;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问题常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谬”。 法律条文的逻辑及法教义学,就是法律借助“数学模式”来解决人文之理的工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模式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法律体系超经验的构筑所出现的自以为是的,相信依照形式推理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幻相。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体,法律正义来自非理性的信仰,理性只是非理性信仰的工具,法律之本在情。裁判者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应当考虑多数人的良知所向,少数服从多数,最好方式就是采取陪审团制度。否则,一断于“法”,相信“法哲学体系与法律哲学体系”的区分,无视良知为法的根基,法之根基必为权力所占、所腐,鸠占鹊巢。法律脱离良知,这也是秦朝兴于法家,也速亡于法家之故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焚书坑儒,“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前车之鉴,这也是仁义的儒家成为后世治国安邦首选之道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