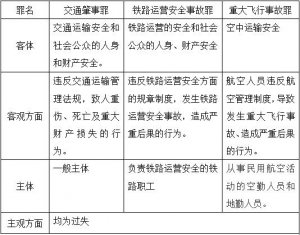司法改革中可能的“异化”风险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发布时间:2017-06-01
摘要:转载研究 作者:马长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新一轮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启动级别、改革深度、目标指向上,还是在方案设计、具体举措、推进速度上,都远超以往,人们也对司法改革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期盼。
|
转载研究 作者:马长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新一轮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启动级别、改革深度、目标指向上,还是在方案设计、具体举措、推进速度上,都远超以往,人们也对司法改革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期盼。然而,这样一个重大、复杂而至关重要的改革工程,需要精心筹划和稳妥推进,特别是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异化”风险更需认真对待和防范。 一、“去行政化”的行政化基于既有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弊端,本轮司法改革推出了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策略。一些省级司法机关已开始积极筹划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在目前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尽管也有由中央“统管”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个层级,省级“统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两个层级,同时,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采取“上提一级”管理的现实考虑,但不管怎么设计,这个省级“统管”如果仍然放在检法系统内,并依托于省级检法机关来实施,都存在着“再行政化”的风险—也即出现“去行政化”的行政化。司法的行政化不仅体现为“外部性”,即在国家机关整个体系中的行政化配置;更根本、更经常的行政化则在于“内部性”,即司法机关系统内部及本单位的自我行政化。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的调研视察、讲话座谈、两会报告、“四五”改革纲要等对全国法院系统提出的要求和工作安排中,就可看出其中的某种领导、规划和管理味道。如果“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统管”举措放在检法自身的系统来进行,那么,可能的情况是消解了市县之间的行政化倾向,却强化了省级的行政化、集中化倾向,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许并不比原来轻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出台后,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统管只是依托省一级的制度平台统筹管理,并不是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上下级法院仍是监督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但这种“统管”的实际运作并不会如此中规中矩,司法干预、审判独立的问题可能仍难解决,甚至会变异为上级对下级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控制”,有悖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据我未必准确的观察,当下检法系统对省级“统管”的改革策略比较积极,而检法系统各自建立相应的法官、检察官遴选与惩戒委员会,将出现每个层级都有4个“委员会”同时运行的状态,这难免会出现臃肿繁杂、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的状况。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和法治建设目标,在省级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基础上,改建并设立统一的司法委员会,并下设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司法经费管理委员会等具体工作机构,进而实施省级“统管”,可能效果会更好、也更恰当,这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 二、资源重置的利益固化每一次司法改革,无疑都是一次司法资源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本轮司法改革尤为明显。事实上,通过改革获利的预期会直接决定人们对待改革的心态和取向,而“局中人”对此反应会更加灵敏和直接。因此,这些改革无论如何都回避不掉“局中人”的态度和行为,何况现在很多改革方案都是由“局中人”来具体设计和操作实施的。这样,在改革的资源重置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规避“减法”,增多“加法”,进而固化其既有利益,抑制受损,就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某种策略性选择。比如,司法机关都很愿意把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的权力增大,但对其监督和制约机制的设计则明显不足;而院长、庭长不大可能情愿在改革中被权力“虚置”,他们对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的裁判行为也不可能没有影响,并会在改革方案及其具体实施举措中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再如,检察院、法院之间资源分配与平衡的问题,这种系统之间的“切割”就更复杂了。不消说在刑诉法与律师法之争上的那些众所周知的背后博弈,就拿当下司法体系与功能设置而言,要真正从司法规律、法治逻辑和世界经验出发,就应该是公诉方为诉讼一造,当事人(律师)为诉讼另一造,二者应该是地位对等的;而法院则应该居于中立地位,平衡两造的主张和诉求,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进而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司法公信。也就是说,法院在整个国家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职薪保障也应该是最高的,但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却不是这样。由于检察院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就经常“亲自下手”,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两高”司法解释(甚至有时还与公安部三家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种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法律依据一直是个疑问,其中也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嫌疑。此外,还有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进行“现场”监督的机制等等。公安系统由于具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地位,因而也备受重视,特别是在周永康主政司法时期,形成了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惯例,而政法委又是“协调”公检法的领导部门。这样看来,法院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似乎是较低的了,不利于审判独立和司法公信的建立。在本轮司法改革中,检察院、法院之间的司法资源重置并没有被作为重点,但检察院会在积极参与省级“统管”、检察官遴选、司法职业保障等改革方案中,有意无意地强化其职权地位,可能的利益固化情况在所难免。于是,对法院所赋资源与职能地位的任何调整,都难免会遭遇到某种攀比、分割与制约,这就会加大改革的难度。当然,在目前六省市的试点方案中,除上海由高院主导外,其余都是由省委政法委主导,这些方案已统一报送中央政法委,而政法委在司法改革中的角色也值得注意。 三、化减目标的改革举措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了几轮,效果都不是很好。个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些涉及到重大职权或者利益减损的改革目标,难免会遭遇到被改革对象的消极抵制或者“打太极”式的策略化解。上轮改革中,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2月),将检察院的刑侦职能剥给公安部(局)、将法院的执行职能剥给司法部(局)、将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剥给司法部(局)等,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当初那些司法职权重新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独立等雄心勃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也就均未能得以落实。尽管这其中有该《意见》的改革力度以及科学性、合理性问题,但被改革对象对改革目标的化减意向和策略选择也是不能否认的。如今这次深度司法改革则会触动更多既有职权、地位和利益,因而上述问题可能会依然存在。比如,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33%也好、40%也罢,其中最关键的是计算方法和根据。有的试点单位只把仍在综合部门的人变身为法官(审委会专职委员)或司法辅助人员,却忽略了许多在一线工作的专业性法官,更不用说员额制各种比例基数之中的“门道”和算法之中的“折扣”了。当然,让相当一部分原本身居法官检察官“主流”队伍的人,退而转为“司法辅助人员”,这一“刀”切下来确实压力很大,也很艰难。不过,员额制的原本目标也就在这种“打太极”式的改革举措下被化减了。同样,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制度运行机制,如果设计不周或者决策不当,也会存在这种改革目标被化减的风险。 四、过高期待的现实难题本次司法改革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背景下,并由中央决策来启动的,因而改革的深度、改革广度都是空前的,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然而,尽管方案中有些改革举措的大方向是对的,基于历史和国情却不能给予过高的期待。例如去地方化问题,只能是尽量减少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率”和不当干预,但事实上想完全排除地方影响、跟地方没关系,这也不太可能。拿法院来说,即便是省级“统管”,但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像案件执行、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都难免与当地部门产生关联。就是在美国,设在各州的联邦法院也难以彻底排除地方力量的某种影响。再如,“终身负责制”也同样不宜过高期待,因为在法官检察官尚未完全独立处理案件的情况下,这种“终身负责制”是难以奏效的,更何况有些情况是无法通过“终身负责制”来获得制约或挽回的(如裁判者移民、人头落地的死刑判决等)。此外,还有职业保障、待遇提高、司法民主化等问题,都会遇到职业攀比、财政支撑等难题,以及潜在的司法大众化甚至“民粹化”风险。因此,对这些改革举措固然要积极推进,但更要理性设计和操作,不可过高期待,否则不仅欲速不达,还会带来消极影响。 五、顶层设计下的“关门”方案为了提升规格、加大力度、提高效率,本轮司法改革采取了“顶层设计”的路径,这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现在的问题是,最高决策层的司法改革《框架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纲要》、各个试点的改革方案等重要文件,都只见于媒体和发布会上的主旨介绍和概要描述,并没有全文公布。然而,各地、各部门又在不断搞社会调研、专家座谈、意见征询,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在不甚明了方案的情况下不断论证探索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顶层设计”下却出现了“关门”方案。由于它缺少多元参与、广泛讨论和深度论证,在“秘密”与“匆忙”中加速推进,就很容易导致方案与现实相脱节,也容易被一些部门主导、操作而发生目标“异化”,因而不利于通过集中集体智慧来推进司法改革。 六、“于法有据”的突破探索本轮司法改革的力度和使命超过以往,因而,改革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就摆上了前台。这是一个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而方法、路径会对目标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看到,现有改革方案中的很多举措,如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员额制、省级“统管”、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等等,都会与《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甚至《宪法》等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而改革又要突破既有条框,这就形成了一个改革与法制的悖论。从目前来看,我们是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的方式来化解这一问题的,[1]但各试点方案也需一并授权才更具合法性,至少是个过渡性的办法。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与突破探索的改革张力,即便是良性违法,采取以违反法律的方式来推进法治也是很尴尬的,并会带来一些难解的问题,进而影响司法改革的效果甚至成败。总之,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改革举措不好或者无法推行,而是意在说明,对待新一轮司法改革不能过于乐观,而应该时刻注意每项举措所面临的潜在“异化”风险,进而扬长避短、规避风险,有效促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作者简介】马长山(1964-),男,黑龙江肇东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注释】[1]如今年6月的《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