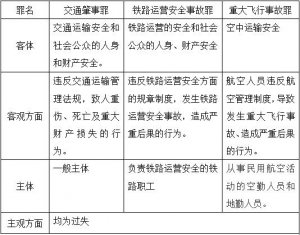|
王敏远教授强调,这是一个立法规定试图解决,但是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刑诉法第37条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核对有关证据。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对于这个“有关证据”到底是什么含义,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认为,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有多维视角。一个是历史的维度,问题都是一步一步慢慢解决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进步。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权利保障。言辞证据的有效质证,对于辩方来说,就是要反复核对。当前,认罪认罚制度改革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这个前提建立在当事人对相关的事实和证据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这才能保证认罪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律师一定要有效介入,核对言辞证据是基本权利。他甚至主张审讯的时候必须有律师在场,否则不能保证认罪的真实性和自愿性。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 田文昌律师在研讨中详细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以及立法上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无论从个人权利保障来讲,还是从节省庭审时间的需要来讲,不让被告人、嫌疑人在庭前了解案件材料的全部内容,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律师的辩护权也不能代替被告人、嫌疑人本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更不能以担心翻供和串供为由否定这个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张保生教授 张保生教授介绍,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证据的角度来说,包括不得自证其罪权、质证权等。质证权又可细分为交叉询问权和对质权,对质权是一个宪法性的权利,中国的说法叫共同被告人之间对质的权利。还有一个叫特免权,这种权利保护的是秘密交流,就是说只有在当事人和律师进行充分秘密交流的前提下,律师才能给委托人做最好的服务和辩护。从根本上来讲,律师的辩护权是依附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满运龙教授 满运龙教授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域外经验。他说,在美国,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最终和最高的目的,是用所有的法律保障被告人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美国只有5%的刑事诉讼,才走到审判这一步,95%的案子实际上在审前都已经解决了。进入诉讼程序中的案件,只有在控方充分开示证据,辩方充分了解证据的前提下,才能达成诉辩交易。在美国,检方充分披露所有证据是法定义务,但是并没有要求辩方一定要完全披露。当然,美国各个州执行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州要求完全披露,有的州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在没有要求完全披露的州,律师的地位非常重要,律师要知道向检方要什么东西,主动要了不给,那就是检方的问题。所以,检方可以不披露,但是那样的话即使一审胜了,上诉之后案件可能被翻过来,所以检方有这种顾虑,他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确实没有什么理由不让律师与被告人讨论、核实所有证据。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先生 刘桂明总编从法律媒体人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做了充分阐述。他认为,由于现实生活中人权意识和程序意识的缺乏,对当事人质证权缺乏足够的重视,才导致这个分歧存在。对于到底刑诉法37条的规定是指核实物证还是人证,可能因为言辞证据不好固定,才使司法机关有了更多的担忧。但是他认为,刑诉法第37条的规定是保障权利,而不是约束权利;是规范执业权利,而不是限制执业权利;是促进人权保障,而不是管制人权保障。所以律师应该有向当事人核对人证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中教授 张中教授从制度、理解、操作这三个层面来讨论律师是否有向当事人核实人证的权利。他提出,辩护权是针对指控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没有指控就没有辩护。辩护权没有强制力,这是与公诉权没法比的。为了把这个天平稍微的扭正一些,需要规定一些特权,只有当事人能享有。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控方的全面开示义务,而被告人只有有限的开示义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应允许当事人在庭前了解所有的证据,包括人证。
最高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先生 高贵君先生强调,从法律条文解读上看,这个问题立法上没有说得特别清楚,是核实有关证据。这个“有关”本身有一个空间,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办案机关当然不希望律师跟犯罪嫌疑人透露更多的信息,因为案件还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当然希望能够跟犯罪嫌疑人做很好的沟通,核实有关的证据,才能够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之所以实践当中会产生这种问题,办案机关有一个司法观念转变的问题。如果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已经介入了,跟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充分沟通,特别核实了人证,可能就会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地方不愿意让律师核实人证。但是,现在最高法院也越来越强调客观证据的重要性,特别是死刑复核案件,即使在没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也能定案。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翻供了,案件也能定。所以,他认为,从立法本意上来说,不应该排除律师核实人证的权利。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