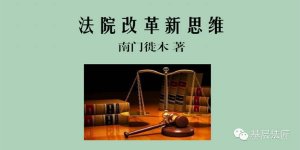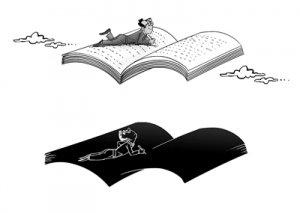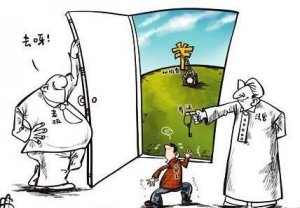苏力:法学教育的两个根本任务
来源:基层司法 作者:基层司法 发布时间:2017-04-26
摘要:基层司法的前沿动态 法学教育的两个根本任务苏 力本文系苏力教授在“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 2007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论坛”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载《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感谢主持
|
基层司法的前沿动态 法学教育的两个根本任务苏 力本文系苏力教授在“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 2007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论坛”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载《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来做一个很难的大会发言。难是因为,一方面,题目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听众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在座的都是法学院老师,大多是校长,院长,事情很多,除了自己的科研教学之外,还有许多杂事;找钱、“挖人”,或者“反挖人”,要争取项目,要争取硕士点和博士点、重点学科,到处求人,等等。所有这些具体工作都非常重?,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第一,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近3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合格法律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仅仅法律?近些年来,鉴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美国法律人的经验,法律人治国的说法颇为流行,我们的许多学生也都比较简单地接受这个假定。但我们的法学院教育真的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吗?真的像现在这样学了法律,或者学了这样的法律,就特别能从政了?难道我们的课本中,我们的法学教育和训练中真有什么治国的仙方秘诀吗?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就是法律系毕业的,而里根则连正规大学都没上过;但仅就从政治国而言,戈氏是失败的,而里根成功了。我不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而是仅就他们的从政结果,从他们的政治实践带给本国人民的福利,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来评价的。如果有人一定要跟我抬杠,说能把苏联搞垮,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成功,那我也只能闭嘴。只是这种“成功”,恐怕还是与法学院教育无关,我相信莫斯科大学法学院不会以此作为其最大的光荣。我们也还应当看看中国台湾。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甚至马英九也都是学法律的,但他们对台湾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贡献,对台湾人民的福祉,包括到对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的贡献,真的要比蒋经国先生那一代人更大、更重要吗?更不说他们个人的人格和道德品质,更不说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了。同样,我的这些评价也不只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说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否定法律人治国。我个人也真切希望并且相信中国的法学教育能培养出真正能使国家富强和人民福利改善的伟大政治家/法律人。但希望归希望,我更得面对现实,从经验上验证和反思一些流行并看似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发现法学教育的问题,重新界定法学教育的追求。太多的例证表明,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能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过去100年来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说实话,我们许多老师对此有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对中国经验是否学术,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理论意义,或缺少自信,或无力表达,只能以各种方式回避中国经验。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也确实有个两难。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还是举几个例子,免得空对空。法学和法学教育界从1980年代中后期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调解,这也影响了后来法院的改革。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司法专业化了,职业化了,但近年法院系统才发现,在中国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离开调解,才重新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调解重新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即使如此,对调解的重视往往要借助或更多借助某些虚构或真实的外国评价,什么“东方一枝花”之类的;对调解的理论分析也往往借助了ADR的分析框架。还有,近年来提出了“反性骚扰法”,好像很有新意,但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7条就是“不调戏妇女”。还有,近年来有人开始论证辩诉交易的正当,但多年来不少人一直批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很少去清理其中的些许道理。也因此,在中国学界,可以名正言顺地赞美英国的“治安法官”,却拒绝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转业军人进法院”。我并不是说上述或其他中国的经验做法都对了,其中是有问题,需要改进,也能够改进;有的即使原则上对,也还缺乏学术的分析论证,或论证得很意识形态化。但即使有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制度发展不能总是“而今迈步从头越”,都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第二,我们更应当反思,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妄自菲薄?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只有等到某个或某些外国人说了,我们才敢想,才敢说?为什么什么东西加上个洋文包装,就可以当成创新,有销路?仅仅借用或基于外来概念来讨论问题不仅是缺乏学术诚实和学术能力,最重要的是,这对中国社会,中国经验,中国人的智慧不公平。你变个说法不仅抹去了中国的长期社会实践,使之成为需要填补的法治空白,它还完全抹去了在这类本土说法下中国社会实践的正当性和理论意义。似乎中国的前人都白活了,法治和正义都是从我开始,是从现在开始。可这还是法治吗?这是在摧毁法治。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在中国学术有自信。如果没有对中国经验的自信和认真总结,只是以外国人的观点作为判断标准,把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当成不规范、不合格的产品,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大问题。这一点还有更大的意义。最近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推出了《2008世界展望》,报告认为,2008年可能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它的根据是,2008年,中国将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还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的进口规模会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宽带网用户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主导全球电子商务的国家;此外,还有北京奥运会。媒体说事当然会夸张,也必须夸张;无论说好还是说坏。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面?无数问题,甚至有一些潜在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已是大国,国际影响日益增强。然而,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如果一个人刻意追求开放,开放也成了一种必须刻意维系的姿态时,这不就是一种保守?不也就失去了心灵的真正开放和自由?我在此同法学教育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