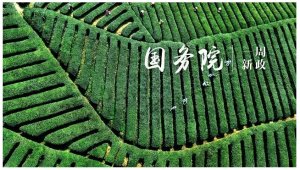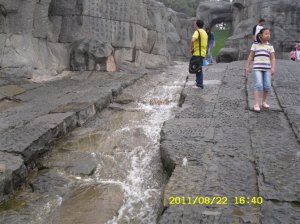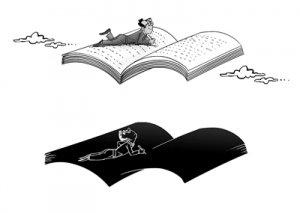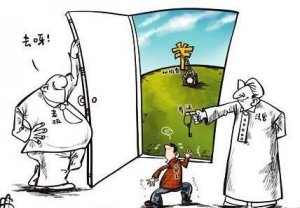读西方法律思想史偶得
来源:勇思谨律 作者:勇思谨律 发布时间:2017-05-19
摘要:法意闲情 由著名法学家、翻译家潘汉典先生译成于1947年的《博登海默法理学》,是一部集中世纪以来西方法学思想之大成的不朽之作。这部法学著作分“权力与法律”、“自然法”、“形成法律的力量”和“实证主义法理学”四篇,译自于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综合法
|
法意闲情 由著名法学家、翻译家潘汉典先生译成于1947年的《博登海默法理学》,是一部集中世纪以来西方法学思想之大成的不朽之作。这部法学著作分“权力与法律”、“自然法”、“形成法律的力量”和“实证主义法理学”四篇,译自于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综合法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埃德加?博登海默1940年版《法理学》,该书后经两次大幅度修改以《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出版,并成为不少国家大学法理学教科书,以“给那些对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工具的法律的一般问题感兴趣的法律与政治学学生或研究者提供帮助”。据说博登海默此生在法理学领域共奉献了四本专著及许多论文,而《博登海默法理学》是最终奠定其声誉基础的最主要专著。可以肯定的是,在写作该书之前如果作者未对西方法理学、法律哲学各学派的著作和思想作过精意覃思研读,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么一部似辞书一般的法理学名著的。而且,只要我们在阅读时能做到心无旁骛,就一定会被博登海默儒雅、睿智、严谨和宽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尤其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作为一位德裔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在书中既不简单排斥异己的观点和理论,也不刻意逢迎与自己所坚持的根本真理相悖的言论和学说,而是“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理解法律在人类秩序中的位置之中”,对各派法理学尽可能冷静、客观、翔实地予以介绍,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西方法学特别是西方法理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并立志循着千百年来法律智慧凝聚的足迹毅然前行。博登海默是“学术理想的生动体现”。在读了《博登海默法理学》一书之后,读者就会感到他同事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在书中,他从福迪名著《鲁滨孙漂流记》讲起,以故事主人翁鲁滨孙和黑人伴侣星期五之间的支配与臣服关系来阐释权力关系,以鲁滨孙和船长之间的交易契约与平等关系来解释法律关系,极其浅显易懂地揭示了权力与法律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差别。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在社会生活的世界中,“权力代表搏斗、战争和支配等因素”,是一种扩张的和革命性的力量,其常常是破坏性的,而“法律代表互让、和平和合约等因素”,是限制的和保守的,其作为静止的力量“可能是追求某项目的优良工具”。大概因年轻时代深受德国纳粹专制之害,博登海默对纳粹德国将“权力可以用一种纯粹专擅恣意的方法行使”的那段血淋淋历史一直心有余悸、深恶痛疾,因而很不认同孟德斯鸠们迷妄地认为“强大的政治权力欲能够由迁就和‘抚慰’的姿态加以控制”,并以专制必然“在人民中产生一种危险与不安的感觉”来警告世人。在论及“法律的理想型”问题时,他认为“在最纯粹的和最完善的法律见诸实现的社会秩序里面,私人以及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是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即“‘一个法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Law)固然必须有充足的权力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可是他却不应享有无限制的权力”,因为“无限制的专权并不是法律,而正是法律的反对者”,“法律愈朝着它的理想形态——睽离权力前进的话,它必定愈强调平等的实现”。因此,他强调“法治的最好的保证就是有一部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宪法,按规定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并认许人民有某些基本权利,不能轻易地被侵犯或剥夺”。显然,作者既反对无政府制,也反对专制,主张政府权力必须有着某种制衡制度加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在博登海默看来,“正义意谓以平等对待平等的人们”,“正义的实现要求在处理两个重要情况相同的事件时以同一的办法处之”。因此,他既不认同柏拉图、尼采等人所主张的“人类自然不平等”、“不应该使不平等的东西平等”和“统治者应被赋予绝对权力”等正义观念,认为这种专制政治很容易流于专横和任性的统治,会使社会弥漫着一种专擅的偏爱和不合正义的共同感觉,也不追随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正义信条,认为这会让最恣意的人攀登到社会阶梯的顶端,使国家面临无政府的危险。相比较而言,作者似乎更倾向奉行亚里士多德“平等者应该获得平等的分儿”的正义理想,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告法律是实现正义的基本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以“中庸之道”、“比例”为正义定义是其对于法律一般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只有认真地实现法律与公道的基本要件与原则,而不能诉诸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方法。”虽然博登海默对法理学各派及其观点的介绍多是描述性的,但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忠实信奉自然法理念的法理学家,他对待各学派学说的态度却是鲜明和理性的。比如,在评价古典派代表人物奥斯丁的主权论时认为,“法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命令的创造”这种说法,只成立于专制统治或一个无所不能的议会统治的国家,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断然是不正确的。再比如,在介绍托马修斯、康德的法律与道德学说时认为,“以法律为人类生活的外在规范,道德为内在规范”这种有势力的学说并没有说出永恒的真理,因为“现代极权主义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社会秩序,如果根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以绝对强迫的制裁为后盾的社会政治集团的道德原理,这个社会秩序必然是自由与个体自主完全被蔑视或抛弃的一种秩序”。博登海默一直信奉自然法的理念,他的“法律主要是一种理性的规定”的观点,与斯多葛派关于“理性是法律和公道的基础”的主张如出一辙。作为“综合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称“希腊人是哲学领域中的先锋,而罗马人却是建立伟大的天才的实际法律体系之第一人”;“人道思想的长大——在某方面可能追溯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观与平等观——同样可能在罗马家族的法律的发展看出来”;“洛克的法学说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论合并起来形成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的哲学基础”;“卢梭的学说可能容易地做成一种绝对的民主”。作者没有简单否定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对于法理学和法治思想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对斯多葛派、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学派和现代复苏的自然法等学派,还是对历史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理念观点,都秉持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体现出一名现代法理学家应有的历史、严谨、理性、公允、谦虚的治学立场。比如,尽管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是一个保守的贵胄,他嫌弃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的理性主义”,边沁、耶林、奥斯丁、凯尔森等人的分析实证主义和龚普洛维奇、庞德、卡多佐、梯马舍夫等人的社会学实证主义共同存在着“把形而上学的和哲学的思辨从法律理论中剔除,并把法律研究的领域局限于经验界这种倾向”,但博登海默认为“唯有融汇自然法学者采取的方法和现代社会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法律基础受着考验的时代所需的法理学才能够实现它的再生”。“形成法律的力量”是多元的,因为“从权力到法律的转型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过程,不能归于单独一个原因的作用”,“在法律秩序的生长、发展与衰微上,有无数的力量起作用”,如政治力量、心理力量、经济力量、民族和种族因子、文化元素等等。从政治原因看,博登海默认为“法律起源于国内两个敌对群体的斗争的妥协——最好的史例见于罗马《十二铜表法》的历史”,“在英国宪法史上法律限制专擅权力方面,是从《大宪章》里面获得它的基本轮廓的”,而“在专制的统治指示下制定的拿破仑法典就是现代立法领域上最伟大的建树之一”。从心理力量看,他认为“在人性的深处坚定地环绕着对于法律的生长发生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如常习与习惯不仅说明了法律的起源,还解释了法律在社会上的继续存在,而人类爱和平的欲望及人性里孕育着爱好秩序和有秩序的欲望也是赞助法律与文明的强有力的因素。从经济力量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毫无疑问有其精到之处,法律只是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生产的经济制度变更,在历史上往往是法律实体变更的原因。从民族的和种族的因子看,他赞同萨维尼和普赫塔所持“法律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及特有精神的产品”的观点,认为英吉利民族像罗马人一样赋有法理学和法律的天资,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却反映一个国家和一定的种族是同一的,法律的目的不再保护公民的私人范围,只为由希特勒独断决定的国家利益服务。从文化决定论的元素看,他认为法律制度是深深地受到整个文明命运的影响,虽然黑格尔、梅因和斯宾塞的见解并不合一,但他们都深信法律是文化演进的一种产品,法律在它的进步的发展上是促进自由的重要工具,而且在罗马法与英吉利法等“所有伟大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上曾经数次地发生,而且这些法律体系纵有许多基本的差异,在某方面是同样地经过若干相似的演进阶段”。当然,正如作者本人在1962年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在读完《博登海默法理学》之后,我的直观感受是这部著作对西方法理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似乎没有充分阐明作者自己的法哲学思想和对各种思想流派做出批判性评价。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该书对于我们找出在社会制度中个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必须怎样分配以便保证法治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对于立法者、司法者和律师养成一种能够察觉威胁法律的危险的敏锐感觉以及形成在复杂和濒危的文明中坚守社会平衡的方式方法的明智判断,对于激发政治学和法学学生讨论与法律制度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兴趣,无疑具有“非常贵重”的帮助和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