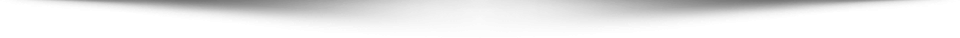案情
原告系患者谢某的直系亲属。患者谢某于2016年1月31日因发热、乏力到被告某乡镇中心卫生院门诊处就诊,被告的门诊医师对其进行体查,体察结果为38.8℃,诊断为:1、发热因查,上呼吸道感染;2、糖尿病。并根据病因对其进行静脉注射的治疗。2016年2月1日、2月2日,谢某再次到被告处就诊,被告的医师对其进行与之前相同的常规检查及注射治疗。2016年2月3日患者谢某仍觉身体不适,原告将谢某送往市级医院救治,市级医院的医师对其拍照观察后,下达病危通知书,称谢某已很难救活。2016年2月4日患者谢某因抢救无效在市级医院死亡,后经检查谢某为H7N9患者。原告认为被告某乡镇中心卫生院在对谢某的最初的诊断及用药存在过错,导致谢某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死亡,故诉请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另被告尚未能提供谢某的就诊病历,亦未申请对患者谢某进行鉴定,被告某乡镇中心卫生院与用医的医生之间订立了聘用合同。
分歧
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医院对H7N9病毒携带患者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医院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患者谢某为H7N9病毒携带者,H7N9病毒潜伏在人体中,人体的表现症状同感冒、发烧极为类似,难以被发现。且日常生活中H7N9患者甚少,在发病人群中所占比例不多,医院医师按常规思路对患者进行了常规的检查,确诊后对其进行相应的治疗,已尽其相应的治疗义务。
第二种意见认为,医院存在一定过错,负次要责任。禽流感患者的发病行为虽与感冒发烧相似,但仍不尽相同,医院未尽到相应的注意、观察义务。又因被告医院系某镇上的中心卫生院,医疗条件较为简陋,且H7N9病毒在县级医院也难以发现,需送往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才能得以检测。故医院虽存在一定过错,但负次要责任即可。
第三种意见认为,医院存在重大过错,负该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患者所患的禽流感虽难以被检查出来,但患者接连几日身体不适,高烧不退,在被告医院进行就诊。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在患者谢某接连几日在其医院里久治不愈的情况下,有义务对可能引发的相关病因进行有效判断,从而采取有效应急措施。H7N9的潜伏期到发病期速度极为快速,医方耽误患者治疗最佳时机,该过错极为加重了患者疾病发展的可能性,在疾病发展中起到主要作用,因此医方对该医疗事故负主要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评析如下:
一、医院需对自身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在举证责任的倒置关系中,医院需主动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这是因为在医患关系中,医学技术及知识的复杂性、专业性,非医学专业的患者不可能对此完全了解和掌握,而医院却能准确地判断出是否在医疗事故有过错及找出事故发生原因。由于证据偏在的关系,患者往往处于举证弱势地位,举证责任倒置保护了处于弱势病患的权益,也强化了处于优势地位的医方的责任。因此,在医疗事故纠纷案中,原告只需对医方责任构成的医疗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以及因果关系加以证明,而医方则需证明自身不存在医疗过错,如医方对过错责任证明不能,则需承担败诉风险。本案中,医院应向法院提供与该案件有关的患者的病例资料而拒绝提供,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规定的情况,故应推定医院在对患者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二、医院应尽“最善诊疗及注意义务”
医院的“最善诊疗及注意义务”是指:医方对患者的治疗首先应具备一定的“医疗水准”,即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及技术水平,符合一般医疗专业医师所具备的普遍标准,按照“医学判断”的专业标准做决定;其次,医方对患者病情要准确的把握及思索,对患者的诊断必须是“最佳判断”。本案中患者所感染H7N9病毒,其发病病症较为明显,医院对患者的疑似病例明显存在预见的可能,但却因未尽到 “最善诊疗及注意义务”,导致患者基于对医院的信赖而延误了及时诊疗时间或失去了其他可能的诊疗机会,进而病情恶化死亡,医院在本案中构成不作为的侵权。
三、疾病诊断的高度风险性不能免除医院的侵权责任
患者所感染的H7N9疾病虽属于自然疫原性疾病,若不经医院相应的治疗,病情可能发展更快,甚至死亡更早。医院在对患者诊治期间,若按相关的医疗规范,尽早应用当时已公认的特效抗流感病毒药物等治疗,存在减缓病情或治愈的可能性,医方的行为与病患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此,病患虽患的是难预测性及高度风险性的疾病,但这不影响医方侵权责任的成立;相反,如果医方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对避免结果的发生未采取适当措施,则仍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四、医师的诊疗错误应由医院对外承担侵权责任
一般而言,行为人对自我过错应自我担责,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某乡镇中心医院属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该医院与本案直接诊断医师之间订立了聘用合同。聘用合同产生隶属关系,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监督和控制的权利,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组织、支配和指令,加之出于“风险归于利益的享有者”的原则考量,故在工作过程中的风险责任须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本案中的医院成为赔偿义务的主体,其承担的侵权责任以医师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为前提。但鉴于患者的死亡与诊疗医师的重大过错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故医院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医师进行追偿。(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 刘琼英;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