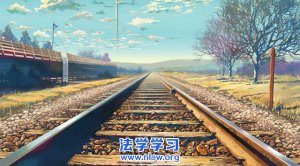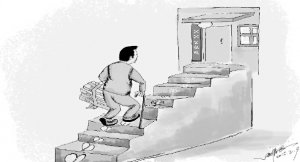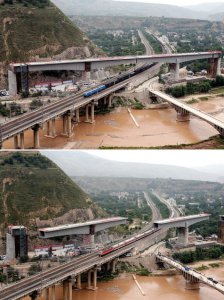|
工商银行鄞州支行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信用证议付中存在欺诈是正确的。本案所涉信用证并无真实基础交易相对应,受益人提交的商业发票、装箱单、原产地证明、质量证明书等单据均是盛通公司或其关联公司职员在没有真实内容对应的情况下制作的假单据,签字也都是伪造的。本案及一系列信用证案件中的信用证欺诈均是建立在一个虚假交易的基础上,该交易仅是出于骗取开证行的授信,进而非法套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的非法目的,并无进行货物买卖的真实交易目的,货物也从未被处置或在市场流通。仓储环节的欺诈与否不影响对信用证欺诈的认定,本案实际是史明等人以非法融资为目的通过其控制的境内外关联公司进行虚假的、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的“自买自卖”,并提交虚假单据套取信用证款项方式,实施的多起信用证欺诈中的一例。(二)二审判决认定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信用证欺诈知情是正确的,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其是善意第三人的说法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本案中,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主观上对联创公司在其开立的账户系虚设、史明等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内外关联公司实际进行的是没有真实基础交易的“自买自卖”、其目的是套取信用证这种方式系明知或应知,客观上在信用证通知、交单、审单、放款等多个环节持续地为史明、盛通公司等利用信用证进行名为进口实为融资提供协助和便利,并在多个环节违反银行应当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和银行业的专业准则,其主客观均不能认定为“善意”。(三)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事实的片面描述,回避了涉及信用证欺诈和自身过错的关键事实:1.2006年以来,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为史明等人设计了通过设立多家离岸公司与其控制的多家国内公司进行自买自卖和信用证进行融资的“结构性融资框架”。史明等人根据此建议和安排,骗取其公司门卫人员严爱国、陈招仁、张荣杰等人的身份证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地设立了多家虚假离岸公司作为“自买自卖”交易的卖方及信用证的受益人。该事实一方面表明涉案所有基础交易的卖方离岸公司均是虚假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料上显示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上对该公司的设立及公司的所有行为均不知情也从未参与,从未签署过基础合同项下、信用证交易项下、沉默保兑交易项下的任何文件,因此所有包含离岸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及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包括向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开户申请和开户资料,以及沉默保兑项下的融资申请、各种资金往来调拨等都是他人冒名虚假签订或签发,离岸公司签订的基础合同均包含虚假内容,受益人递交的信用证单据也均是包含了虚假内容 的单据。因此,本案明确存在信用证单据欺诈和基础合同欺诈。另一方面,该事实表明澳新银行上海分行自始就明知史明等人完全是出于非法的融资目的,此后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又在各交易项下通过一系列行为配合并最终促成了史明等人利用虚假交易和虚假文件及虚假单据达成其融资目的,因此,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信用证欺诈的实施实现是明知的,具有明确的恶意,显然不是善意第三人。2.在具备了非法融资的主体注册基础后,澳新银行上海分行违反法律和诚实信用原则为虚假离岸公司开立了假名账户。其在开户过程中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要求客户在开户资料上面签,而是直接将空白开户资料寄给了史明等人,并且在明知开户资料上显示的严爱国、陈招仁、张荣杰等签名均为虚假的情况下,仍在开户资料上载明鉴证签字属实。史明等人正是通过这些虚假离岸账户完成了每一笔信用证交易项下的资金的套现和转移,而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故意违法为史明等人开立假名账户,进一步证明了其在信用证交易中的“非善意”。3.在具备了所谓“结构性融资框架”项下非法融资的主体基础和转移资金的账户基础后,史明等人开始利用其控制的不同公司进行大量、频繁的利用信用证从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套取资金的虚假交易,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再通过与离岸公司之间的虚假的《沉默保兑协议》通过将贴现款项支付给离岸公司,事实上信用证的开立仅出于套取资金的目的,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背景,而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和签字也都是虚假的。4.由全国各地不同银行开立的上百个信用证全是经由澳新银行上海分行进行通知、交单、审单和贴现的,而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在各个环节均未尽合理审慎之责,且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恶意。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已经知晓信用证的通知对象本身应该通知给信用证受益人,但是每次信用证都通知给盛通公司,并且每次在信用证项下的交单人均不是信用证受益人,对这一违反常规的现象其是自始明知的,也从未提出异议,而是一直密切配合。仅在2008年3月13日至9月24日半年内,通过澳新银行上海分行通知、交单的信用证多达83笔,这些信用证项下单据上的公章与受益人在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开户时预留的公章有一定差异,但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从未提出异议。83笔信用证项下的仓单被多次重复提交,其中94张仓单被提交多达204次,有43张仓单由同一审单员或几位审单员在间隔短短一周的时间内重复审核。在明知结构性融资背景的情况下,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短时间内大量仓单重复提交从未采取任何识别措施,不负责任地放任和配合交接单据、审核单据,将虚假的单据、重复提交的单据以交单行身份反复递交给不同的开证行,并要求开证行对不同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做出付款。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从事了上述系列非审慎和非诚信的行为,其显然不具有善意第三人地位。(四)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再审申请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承认“盛通公司取得世天威公司仓单后从未向世天威公司提取过货物,代表同一批货物的不同或相同世天威公司仓单分别在不同信用证下交单议付”,“代表同一批货物的相同或不同仓单重复流转,贸易量及融资金额亦因此倍数增长”,并承认本案存在“关联交易和放大交易”,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基础交易的虚构没有异议,其应该得出存在信用证欺诈的结论,但其却称“二审判决认定存在欺诈是错误的”;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承认其对关联交易及利用关联交易融资知情,其行为已经不符合“善意”的要求,但其又称“二审判决认定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所谓欺诈知情是错误的”,自相矛盾。(五)一审、二审判决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再审事由。在认定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及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的情形时,本案一、二审判决均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及第十条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经查,本案与本院受理的其他29宗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再审案件案情近似,性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