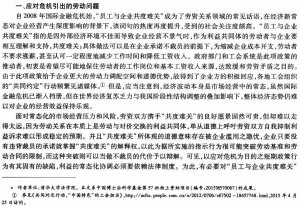|
尽管宪法中没有规定法院工作报告应交付同级人大表决,但仍然有宪法学者认为这可能违宪。因为宪法渊源不仅包括宪法条文,还有宪法惯例。1980年代之后,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直到今年“两会”,全国人大还在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进行表决。一旦改革,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将在中央、地方形成两种不同模式,法律制度的连贯性、内部统一性,都会产生问题。 南方周末:目前的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试点,情况如何? 陈瑞华:人的方面,一些地方的省委政法委下设了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只有经过遴选委员会的笔试、面试,法官才能入额。也就是说,那些由同级人大任命,但没有通过遴选委员会遴选的法官是不能办案的。那么今后,人大任命的法官可能成为一种没有实际审判权的职称。 钱的方面,有些省级财政厅将省以下三级法院都作为一级预算拨款单位。但财政部门不了解法院的具体情况,很难细致考量各地市、区县间的差异。比如上海的浦东新区法院和崇明县法院,案件数量、案件复杂程度、办案花费差别很大,但财政部门不可能考虑这么多。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财政部门只与省级高院对接,让高院成为三级法院的预算编制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权就被高院攥在了手里。 但必须要小心,在挣脱区县级、地市级地方化的过程中,很可能陷入省级高院的权力扩张,落入省级地方化的窠臼。而且现有的改革,大大弱化甚至架空了同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省级人大对省级高院的监督也没有得到加强。 南方周末:在行政领域,省级高院加强了对中级、基层法院的管控。这种管控有没有可能延伸到司法裁判权上? 陈瑞华:依据宪法,我国的上下级法院间是监督关系。监督意味着在司法裁判领域,没有经过上诉、抗诉,上级法院不能干预下级法院办案。 而根据现在的改革思路,最高法院领导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高级法院领导辖区内两级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这种被列入“垂直领导”的司法行政事务不仅包括财、物,也包括人事、监察、司法警察等多个方面。 比如人事方面,高院可以指派中院院长,中院院长、党组书记可能同时也是高院党组成员。这与行政机关的体制完全相同,就像南京市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委常委一样。再加上入额法官要经过院长提名,院长便牢牢掌握了所有法官的生存命运。 汉密尔顿说过,“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面对院长不独立,下级法院面对上级法院不独立,司法裁判系统也就不可能独立于司法行政系统之外。我担心法院系统内部的请示汇报会愈演愈烈。而在请示汇报中,审级、两审终审都将沦为摆设。因为下级法院的态度就代表了上级,上诉只是徒劳。 南方周末:早在2010年,最高法院就印发过《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以杜绝请示汇报。但5年多过去了,为什么收效甚微? 陈瑞华:首先,司法责任制越来越严格,下级法院为了逃避错案追究责任,主动将矛盾上交、风险转移;其次,我国法院特有的考核制度中,有一项是上级法院对案件的发回重审率、改判率。如果下级法院在裁判前就向上级请示,上级不可能撤销自己给出的结论,因此发改率就会降低。第三,法院不是活在真空中,要应对整个社会大环境。当下级法院无法抵御外部干预时,就会本能地寻找避风港。比如一个中级法院审判的案件,当地领导要求案子必须这么判,但这违反法律。中院就会搬出高院,“看,这是上级说的,不是我说的”,以此规避外部干预带来的政治风险。 这种情况下,上级法院也怕引火烧身,往往极不情愿表态。中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相互推诿责任、转嫁风险的关系。有些案件在五六年甚至十年中,不断上诉、发回重审、上诉、发回重审,多的能达到8次,上级法院明知裁判有错也不肯直接改判,就是这个原因。 业务庭和审委会或可取消?
南方周末:本轮司法改革取消了庭长的审批权,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走得更远,比如2014年辽宁葫芦岛中级法院打破了13个业务庭,重新划分为25个合议庭。这次修法是否涉及法院内部业务庭的设置? 陈瑞华:没有。葫芦岛中院的“扁平化”改革取消了庭长、副庭长职务,让他们也进入法官员额,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最高法院并没有取消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的打算,而且他们当然地成为入额法官。 事实上,本轮司法改革提出“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也就是说,庭长不能干预那些不是自己审判的案件。如此一来,庭长最大的作用便是审判自己的案子,不能再为其他法官签署意见,那么有必要保留这么多庭长、副庭长吗? 葫芦岛中院的改革是很有益的探索,可惜没能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可选择项。在我的理想中,一所法院只需要一个行政中心,统一处理所有非审判事务。设一名专职副院长,不审案,只管理政治部、人事、纪检、后勤等各项行政工作,相当于这所法院的总经理。 在取消行政级别的同时,还应该激活《法官法》中关于专业等级的规定,将法官专业等级与工资、待遇等挂钩,形成激励机制。 南方周末:审判委员会制度被学界诟病多年,认为其违背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基本司法规律。此次修法,会对审委会的权力加以限制吗? 陈瑞华:一直以来,审委会被人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黑箱操作。一群审委会委员在会议室里听案件承办法官口头汇报,既不到法庭亲历庭审,也不阅卷。而且审委会讨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公正性难以保证。 在最高法院的改革思路中,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和决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只在“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中,进行事实认定。这是一点进步,说明法院已经认识到了仅听法官汇报,不能对案件事实下结论。 可问题在于,对案件的法律适用,不听控辩双方观点就可以下结论吗?在很多案件里,尤其刑事案件,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法律适用问题,比如有罪无罪、量刑、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官的口头汇报,很难将双方观点说清。 南方周末:哪些属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有没有什么判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