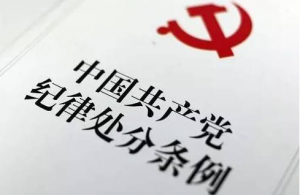|
从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的角度展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新发展,相信这项改革任务的完成一定为期不远。 最高人民法院于“二五改革纲要(2004-2008)”即提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任务,继而在“三五改革纲要(2009-2013)、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中就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出部署安排。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战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在全国确定了50家法院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做出了以点带面的部署,全面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2015年4月9日,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首次召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司法规范性文件,标志着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到达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规范性文件从法院建设诉讼服务中心等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推进诉讼与各种纠纷解决方法及机构的对接、探索或健全多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完善相关的具体制度和程序安排、加强对于开展多元纠纷解决工作的保障等等角度做了相当全面深入的安排。从文件的这些内容来看,可以说是集10多年来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经验之大成的结晶。《意见》的实施推行可望产生一系列当下和长远的效应,为司法改革的推进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带来积极的影响。 从短期内的效应来看,《意见》的出台正值改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本轮司法改革各项任务在全国法院的展开,对于不同改革任务之间协调或相互配套的要求也在提高。尤其是在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和法官员额制改革之后,“案多人少”的矛盾或困难在一些法院表现得更加突出,亟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予以缓解。强调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改革正好能够成为应对这种矛盾困难的一个有力举措。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意见》的基本价值还在于能够努力充分地动员社会自身的力量去应对矛盾的化解、秩序的维护乃至正义的实现等等多方面的社会需求,从而能够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向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善治的转型创造必要的条件。不过,要使这些积极的效应和重大的价值或意义真正体现出来,关键在于今后如何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制度或程序建设任务。 《意见》亮点措施很多,限于篇幅,现就《意见》第四部分第二十七条“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的规定谈一点浅见。该规定的内容是,“探索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范围和案件类型。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这里所讲的调解前置,指的其实就是在立案登记阶段采取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措施,将某些类型的纠纷首先纳入调解渠道加以处理。只是在调解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才能转化为诉讼案件。这项程序的建立牵涉到合意与强制、当事人意愿与法院职权等复杂的“二项对立”命题,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过种种的教训和经验。 我国社会从传统上看,与其他的文明相比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即已形成人际关系浓密却又极富流动性、因而“摩擦系数”很大但各种灵活多样成本低廉的纠纷处理解决手段亦非常发达的特点。尽量向所有人低成本地提供纠纷解决的公共服务,也是公共权力“亲民、便民”获得民心的一种重要的正当性依据。在历史上,司法服务向一切纠纷开放的公共政策总是与社会自身能够处理消化绝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琐细纠纷的机制紧密联系。到了当代,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进展,在法院“案多人少”的同时,重构社会自身处理消化纠纷的能力或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却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议题。 不过,由于前些年的司法政策过于强调“调解优先”,在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这方面也出现过某些偏差。部分法院对于立案阶段的案件分流或诉前调解等设置了过高的考核指标,结果导致一些当事人对自己的起诉因反复调解而迟迟不能得到受理,或者对立案阶段事实上被前置了法律外的程序环节表示不满或抱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目标之一原本在于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但近年来某些地方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即在案件分流多元解决方面做得较好的往往是一些收案量不那么大的法院。一些案件压力大却又明显缺乏人手的法院受制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反而无暇顾及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其原因之一在于强制性的调解前置存在无视当事人意愿和无法可依的风险,但过于强调自愿性又可能导致案件分流被轻易地否决。 目前看来,一方面已不能回到重新设置诉前调解率等考核指标,不得不或隐或显地对当事人的意愿强加干预,事实上造成对诉权行使的侵害这种旧路。另一方面,从繁简分流的司法规律入手,同时也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预期,对于若干往往比较琐细零碎或不一定适合采用正式程序审理判决的纠纷种类试行调解前置,应当作为今后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如何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又能采取带有某种程度强制性的引导措施,则是进行这种改革尝试并取得可让社会接受的成果之关键。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不妨对司法实务中相关具体操作稍作一点分析。 首先,在现行法律有关“先行调解”等规定的既有框架之下,就存在着将一些类型的纠纷纳入试行“调解前置”范围的余地。预先设定此类细化了的规则,意味着法院可对这些纠纷采取带有某种程度强制性的引导。在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如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将来还可以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大强制性引导的力度。 其次,在这种明确规则存在的前提下,原告将纠纷诉至法院,如果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认为该纠纷符合有关调解前置案件适用范围的规定,先可以做的事就是设法联系被告。在被告联系不上甚至送达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该纠纷就不具备调解前置的基本条件。但若是能够方便地告知两造当事人,他们之间的纠纷应适用调解前置,相信多数情况是原、被告都未必会明确表示反对。 第三,如果一方或双方聘请有律师代理,预先设定的规则可发挥更为明确的引导作用。不过,万一有一方或双方的当事人都对纠纷适用调解前置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或明确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原则上法院不应强行依据既有规则适用这种程序。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便以“依法办事”为由强制性地适用调解,其结果也往往是合意难以达成,甚至还有影响此后诉讼程序进行之虞。 总之,并非预先设定哪些纠纷应适用调解前置的规则,然后照此办理即可了事。对于这些规则的运用,还是应根据具体情况权衡什么场合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有关调解前置的实务操作过程中,充分理解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引导与对于当事人意愿的尊重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并巧妙把握其尺度或分寸,正是成功运用这种程序的关键之点。 以上不过是对“多元解纷改革意见”众多内容之一例的初步解读,如果我们秉承“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在不同领域以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不懈地探索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和做法,相信这项改革任务的完成一定为期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