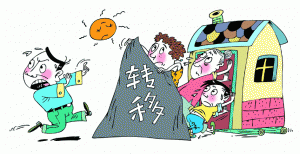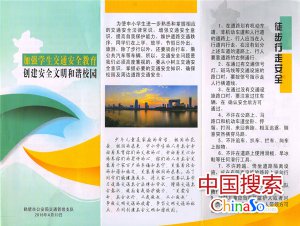|
肖景文和东达公司主张吉昌公司所缴纳的承包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06年1月。但根据肖景文与吉昌公司于2006年1月1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中关于“合同的履行期限为2006年12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合同生效日期为2006年12月1日”的约定可知,该合同书为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在附生效期限的合同中,履行期限是以所附期限到来为必要条件,所附期限尚未到来之前,履行义务并不存在,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因此,肖景文和东达公司所称“合同履行期限的起始时间为2006年1月”与合同的约定不符。关于肖景文和东达公司主张“存在除合同书以外的口头合同”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此,肖景文和东达公司应对另外存在的口头合同成立承担证明责任。但从肖景文和东达公司提出的证据看来,既没有相关的直接证据,也没有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并且能得出唯一结论的间接证据,因此,对此事实理应不予认定。对于肖景文和东达公司主张的吉昌公司在2006年1月开始实际经营的问题。证据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肖景文和东达公司所称吉昌公司于2006年间产生的费用均系吉昌公司以白条方式出具,此种费用表现形式难以证明该费用即为涉案海域实际生产经营的费用,亦即证明费用产生的证据与海域实际生产经营的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认定吉昌公司已经实际经营的证据。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合同履行期限的起始时间为2006年12月并无不妥。 (二)关于吉昌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是否有违约行为。 肖景文和东达公司主张吉昌公司违约行为有两项:一是欠付承包金;二是违反合同约定捕捞海螺。本院认为,关于吉昌公司是否欠付承包金。如上所述,因证明东达公司及肖景文主张的合同履行期限为21年(即自从2006年1月开始计算承包期限)的证据不充分,因此本案合同履行期限应为承包合同约定的20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吉昌公司拖欠承包金的事实。关于吉昌公司是否违约捕捞。根据双方合同第8条的约定,合同履行期内吉昌公司必须按肖景文统一安排,允许黄泥洞村民以任何方式赶小海,下小网;海螺等其它产品归本村村民所有。由此可知,一方面,合同并未约定禁止吉昌公司捕捞海螺等其他产品,所以肖景文与吉昌公司签订转包合同后,依据合同约定,吉昌公司当然享有肖景文从东达公司处获得的承包权范围,即有权捕捞;另一方面,在合同纠纷中,认定违约的依据是合同约定,吉昌公司即使存在捕捞,亦应由被侵权人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吉昌公司无违约情形并无不当。 (三)关于肖景文与吉昌公司《承包合同书》的效力状态。 肖景文主张吉昌公司延期缴纳海域承包费,双方之间的《海域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东达公司主张,一、二审判决遗漏了东达公司已将案涉海域另行发包他人经营这一重要事实,造成判决无法执行。本院认为,首先,肖景文与吉昌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期限起始于2006年12月1日,吉昌公司在履约期限内不存在欠付承包金的行为,肖景文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其次,根据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东达公司曾直接收取吉昌公司交付的承包金,也自认曾向吉昌公司送达过解除合同的通知,说明东达公司明知案涉海域的实际承包人为吉昌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即使东达公司依合同约定解除其与肖景文之间的合同,也不必然及于吉昌公司与肖景文之间的合同效力。最后,东达公司及肖景文除了提供将案涉海域重新发包的合同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涉海域已经另行发包。一、二审期间,法庭均要求东达公司通知新承包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而东达公司均以种种借口表示新承包人不能到庭,故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案涉海域重新发包的事实。由于东达公司与肖景文之间合同解除之效力并不能及于吉昌公司,所以在吉昌公司仍享有承包权期间,即便东达公司擅自转包属实,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的情形,享有追认权的吉昌公司,仍主张承包权的行为将会导致无权处分合同归于无效,而一个无效的合同并不能阻却生效裁判的执行。综上三点,肖景文与吉昌公司间合同的效力状态为有效,一、二审判决吉昌公司与肖景文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并无不当。 综上,肖景文和东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肖景文和瓦房店市东达海水养殖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梁曙明 审 判 员 张 纯 代理审判员 武建华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徐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