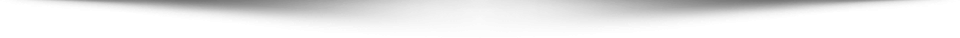内容提要:建构“职业歧视”法律定义是解决我国禁止歧视法律制度空转的前提。定义职业歧视首先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根据可识别性、可保护性和可延展性标准廓清法律禁用的归类事由;其次,法律应当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做出的行为模式,即不得基于禁用归类事由做出区别对待、区别影响、骚扰、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以及报复等行为;最后,法律还有必要设定真实职业资格、正当经营所需、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以及平权措施等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在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雇佣自由之间达至合理平衡。
关 键 词:职业歧视/法律定义/归类事由/行为模式/抗辩事由
标题注释: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禁止职业歧视法律进路研究”(项目号skq2012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成,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一、导论:作为枢纽型概念的“职业歧视”
严重且持久的职业歧视只会招致贫穷与排斥。①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态度鲜明地提出要“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②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近来亦先后表态指出制定反职业歧视法确有必要。③
实际上,立法者很早已经意识到职业歧视的危害并试图做出回应。自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在我国首开禁止职业歧视先河以来,④《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多部法律亦先后作出类似规定。⑤然而,将近20年的时间跨度并未带来立法上的实质进展。2008年《就业促进法》除了将禁止职业歧视的范围延伸到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以及农村劳动者外,其采用的立法技术依然停留在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和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水平——仅仅满足于设置一般禁令,即用人单位不得实施职业歧视。在最关键的职业歧视法律定义问题上,立法者一直缄默不语。什么是或者不是职业歧视始终隐身于法律文本的迷雾当中,不曾显露真容。
立法者回避职业歧视法律定义或许是希望为法院预留足够的裁量空间,进而经由司法实践完成对职业歧视定义的建构。但实践证明,慷慨如此反而极大束缚了法院的手脚。在缺乏法律引导的情况下,单凭法院一己之力殊难判断用人单位五花八门的雇用行为是否就是立法者意图禁止的歧视行为。越来越多职业歧视案件审而不判,调解结案,正是法院在法律规定缺位与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夹缝中勉力支撑的真实写照。⑥考虑到现阶段法治环境中法院相对弱势的地位,寄希望于法院独立完成对禁止职业歧视这一中国法治处女地的拓荒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禁止歧视早已深度嵌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职业歧视法律定义不彰成为我国在履行人权保障国际义务中的软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导下的普遍定期审议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的公约机构在有关中国公约履约情况的审议意见中均对我国立法上没有界定歧视表达了担忧和关切。⑦
酝酿中的反职业歧视法被寄予确保中国社会流动性,促进边缘群体融入主流的厚望。要确保这部孕育中的法律不再重蹈“仅仅看上去很美”的覆辙,如何定义作为整部法律枢纽概念的“职业歧视”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目前学界有关职业歧视的定义大抵脱胎于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⑧但问题在于,《消歧公约》仅仅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定义职业歧视的框架——“职业歧视”是归类事由(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行为模式(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的区别、排斥或优惠等)与抗辩事由(基于特定职业内在需要等)三者的结合。完整定义职业歧视还需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标准和中国实践进一步明确归类事由、行为模式和抗辩事由的具体内容,即用人单位基于哪些归类事由,做出的何种形式的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法律效果的行为应当被法律视为职业歧视,除非被特定抗辩事由阻却了行为的违法性。
由此,本文将着力回答上述三个界定职业歧视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归类事由、行为模式和抗辩事由三个基本要素的解析,本文期望能够初步明晰我国职业歧视法律定义的基本思路,推动反歧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破局。
二、职业歧视的归类事由
定义职业歧视首先需要厘清禁止用人单位使用的归类事由,其实质是明确法律应予保护的对象人群。禁止歧视的种类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应该根据国情和需要来决定。⑨事实上,用人单位据以挑选劳动者的归类事由从性别、种族、残障到学历、专业、容貌,各式各样,不可胜数。法律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将所有事由逐一禁止,关键在于如何在名目繁多的事由中合理取舍并导入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一)确定禁用归类事由的标准
1.事由关联的人群具有可识别性
可识别性意味着依据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能够判明特定个体是否具备某一集体身份,即是否属于归类事由关联的人群。一个具备可识别性的事由可以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将人群分为“我们”和“他们”。事由具备可识别性是其被纳入禁用目录的必备条件。因为“如果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话,那么对外部群体成员的歧视就是难于实现的,而且也是难于觉察的”。⑩易言之,区分“我们”和“他们”是歧视发生的基本前提。实践中,诸如种族、性别、年龄、残障等是常见的具备高度可识别性的事由。
不具备可识别性的事由不应纳入禁用事由目录。例如,容貌是典型的不具备可识别性的事由。学界一直存在禁止基于个人美丑实施的“容貌歧视”的主张。(11)但问题在于,对美与丑的评价是高度主观的个人体验。“世人之于美的标准不过是其道德观、健康观、财富观以及种族观的投影。人们期待一个道德的、健康的、成功的以及被社会所认可的人能以与众不同的形象呈现于世。”(12)不仅每个时代关于美的定义大相径庭,每个个体对美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即使是立法者或者法官,在判断美丑的问题上亦无最终发言权。可以预见,无论法律如何雕琢,一旦诸如容貌等不具备可识别性的归类事由为法律禁用,法院必将在劳动者是否可被归入此项事由关联人群的问题上陷入旷日持久的分歧。(13)这也正是许多国家在是否禁止基于“容貌”的职业歧视问题上态度谨慎的原因所在。(14)
2.事由关联的人群具有可保护性
禁用归类事由的取舍是由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因素和发展程度所决定的。(15)可保护性强调立法者在对诸多事由进行取舍时,应当确定事由关联的人群是否是因为受到排斥而确实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边缘群体,或者有足够理由认为因为其很有可能在未来出现的排斥而沦为边缘群体。“法律资源并非无限,为求得有限资源的最大社会效果,必须分清主次,集中力量打击危害最严重、民众呼声最高的歧视类型,而不能搞‘敞开大门’、‘多多益善’。”(16)只有当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数量庞大的特定人群丧失通过市场竞争合理获取资源的可能之时,相应事由方得被考虑纳入禁用事由目录。反职业歧视法应当聚焦于劳动力市场中大规模的排斥行为,断不能越俎代庖主导本该通过市场竞争完成的就业和职业机会分配。可保护性标准强调立法资源的善用,排除那些虽不尽合理,但在劳动力市场中尚未产生规模排斥效果的归类事由。用人单位无法确保一切雇佣决策皆源于客观理性,基于劳动者星座、酒量、姓氏等事由作出的雇佣决策显然有悖情理。(17)但实践中以此事由遴选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凤毛麟角,受到影响的劳动者数量较少。劳动者完全可以通过更换求职单位等低成本方式解决这些障碍。与其耗费宝贵的立法资源回应小概率事件,不如交由市场自净。毕竟,法律不理会微不足道的小事。
3.事由外延的可延展性
事由外延的可延展性要求在有多个相似事由可供选择时,法律应在保证可识别性、可保护性的前提下审慎选择外延相对较大的事由,为法院等通过扩张解释事由及时回应消除歧视的新需要预留出操作空间。例如,在立法中使用“性别”这一中立表述的事由而非带有明确指向的“女性”可以保证禁止性别歧视法律条款在保护女性的同时也得适用于男性或者其他性少数人群。(18)对归类事由延展性考虑欠周延而限制法律射程的例子则是2008年我国《就业促进法》第30条对基于传染病病原携带状况歧视的禁止。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而非“健康状况”作为归类事由完全排除了非传染病病患通过扩张解释获得法律保护的可能,劳动者因为色盲、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原因受到的歧视成为现行禁止职业歧视法律保护的盲区。(19)
(二)应予禁用的归类事由
考虑到事由的可识别性、可保护性和可延展性,我国在制定反职业歧视法的过程中应当考虑至少将下述三类事由纳入禁用目录。
第一,先赋类事由。先赋类事由直接因出生而获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并且后天几乎无法改变。一旦劳动力市场出现对特定先赋事由的滥用则意味着具备或者不具备此类事由的劳动者将面临不可逆转的排斥。因此,先赋类事由应当是反职业歧视法控制的核心对象。从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及地区立法情况来看,禁止基于特定先赋事由的职业歧视无不是法律规制的重点。(20)常见的应予禁用的先赋类事由包括公民的民族、种族、性别、基因、年龄、性倾向等。
第二,准先赋类事由。准先赋类事由虽非与生俱来,后天也并非绝对不可改变,但一旦获得,即比较稳定,轻易不会发生变动。如果用人单位滥用准先赋类事由,同样可能导致关联人群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充分融入劳动力市场,故其具备的排斥效果与先赋事由近似。反职业歧视法应予排除的准先赋类事由主要包括残障、宗教信仰、吸毒史、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等。
第三,自赋类事由。自赋类事由是劳动者后天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经由个人选择获得的事由。该类事由可以较为容易地生成、变更、消除,因此不应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重点。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确实普遍存在滥用特定自赋类事由损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情形,反职业歧视法仍得作出回应。法律须认真考虑禁用的自赋类事由包括劳动者的工会会员身份、从事岗位的性质(如劳务派遣工、兼职员工等)以及是否有检举、控告用人单位实施职业歧视的记录等。
(三)确定禁用归类事由的实践意义
确定归类事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有身份才有救济”。法律通过列举禁用归类事由厘定受保护人群范围,提示用人单位在作出招录、培训、晋升、奖惩、薪酬及福利待遇等决定时应当注意避免侵害关联人群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第三人不受歧视的权利。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在雇佣决策中基于禁用事由实施了职业歧视,那么,作为换取法律干涉用人单位雇佣自由的前提,劳动者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属于某一事由关联的特定人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cDonnell Douglas Corp.v.Green”案确立的职业歧视案件举证规则明确要求,原告若想起诉得直,必须首先证明自己属于某一受保护群体,即具备禁用事由关联的集体身份。(21)在“Canada(Attorney General) v.Mossop”案中,Mossop以其同性伴侣父亲去世为由向雇主申请休丧假,但被雇主以其伴侣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或伴侣(必须为异性间的结合)为由予以拒绝。因为诉讼当时《加拿大人权法案》(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尚未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认定Mossop不具有受法律保护的身份,雇主的行为不构成歧视。(22)
有必要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劳动者完全可能因为复数身份而受到歧视,如有残障的女性,此时即构成多重歧视。(23)一般而言,多重歧视包括三种具体形式。第一,累积型多重歧视。劳动者因具备复数归类事由受到歧视,但前述歧视分别发生于不同场合。第二,附加型多重歧视。劳动者因具备复数归类事由受到歧视且前述歧视发生于同一时间但互相之间没有关联。例如女同性恋者可能同时因为性倾向和性别受到多重歧视。第三,交互型多重歧视。劳动者因具备复数归类事由受到歧视,并且,复数归类事由互相交织,不可分割,共同导致了歧视的发生。例如针对黑人女性的歧视。(24)如果反歧视法律裹足于劳动者只能基于单一身份寻求救济的既有框架,那么,边缘群体中最不利、最脆弱的个体将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或政治救济。(25)因此,承认多重歧视的独立性是对既有法律实践中简单分隔归类事由导致瑕疵的重要修正。(26)事实上,部分国家已经在立法上允许劳动者得主张因复数事由受到歧视。例如,英国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第14条即禁止基于年龄、残障、性别重置、种族、宗教或者其他信仰、性别、性倾向等归类事由中的两项同时实施的多重歧视。
三、职业歧视的行为模式
在厘定归类事由基础之上,法律需进一步明确应被认定为构成职业歧视的行为模式,亦即用人单位不得基于被法律排除的归类事由做出特定形式的行为。
(一)基于禁用事由实施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27)指的是“在本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由于特定群体或个人的权利因法律禁止的区别事由而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比他人不利或优惠的对待”。(28)此类行为被视为“最容易理解的歧视行为方式”,(29)因为法律禁止职业歧视的初衷就是为了确保那些来自历史上蒙受排斥、偏见以及负面刻板印象群体的个人能在获得就业和职业机会中被给予平等对待。(30)
在禁止职业歧视的场域中,成立区别对待的歧视必须同时存在外在的引发不利后果的区别对待行为和内在的职业歧视动机,(31)盖因区别对待的核心即是用人单位故意地基于劳动者的性别、种族、残障等归类事由给予其不利对待。(32)在“谌某诉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33)、“郭晶诉杭州市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般人格权纠纷案”(34)等我国已有的少数职业歧视诉讼实践中,存在区别对待的行为和歧视的故意是法院最终认定用人单位实施了基于传染病病原携带状况和性别的职业歧视的重要前提。
当然,用人单位在实践中实施区别对待通常是复数事由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劳动者的种族、性别、残障等法律明文排除的归类事由与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修学专业等法律并未禁用的归类事由共同导致用人单位做出区别对待。就此类基于“混合动机”而为的雇佣决策而言,只要用人单位赖以行为的诸多事由中涉及法律禁用的归类事由,即应当认定成立区别对待的职业歧视,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二)对禁用事由关联人群造成区别影响
法律禁止区别对待以促成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但区别对待并非职业歧视的唯一表现形式,因为无视客观差异的同等对待同样可能导致不平等结果的出现。事实上,同等地根据学历进行挑选可能排除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者;同等地要求能够适应全职和经常出差的工作内容将会排除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劳动者。(35)因此,法律、政策或某个行为虽然表面上对不同群体适用同样的规则或标准,但是却会对某个群体不利,导致歧视的后果。(36)这种以看似公平的方式却实际上延续、加重法律禁用事由关联人群的边缘处境,即构成区别影响的歧视。(37)
相对于区别对待对歧视主观意图的强调,区别影响更看重行为导致的客观结果,(38)因为法律禁止区别影响是为了消除历史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或者说是为了防止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进一步固化。(39)在“Griggs v.Duke Power Company”案中,针对电力公司要求所有雇员需具备高中以上学历或者通过智力测验方能从“煤炭处理”部门转岗到操作、维护或研发等部门进而导致非洲裔员工被不成比例地排除在外的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职业机会平等不应沦为《伊索寓言》“狐狸与鹳”中只能由一方独享的牛奶,而必须确保所有劳动者能够均沾。法律不仅禁止公然实施的歧视,也禁止那些看似公平但却会导致歧视性结果的做法。(40)
(三)对禁用事由关联人群实施骚扰
骚扰通过有指向性地扭曲职场生态环境达到排斥禁用事由关联人群的目的。在本质上,骚扰是歧视的一种形式,是折磨少数族裔以及其他边缘群体成员的手段以阻止他们通过劳动就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41)骚扰行为破坏职场生态的路径有两条。
第一,营造敌意的职场环境,此即为敌意环境型的骚扰。用人单位(通常是其主管人员或者其他员工)经由做出指向个人种族、性别、残障等事由的不受欢迎的言词或者行为,造成胁迫的、不友好的、不体面的和敌对的环境,(42)从而将归类事由关联人群阻隔在职业领域之外或者从职业领域中驱离。当然,不能将敌意环境型的骚扰狭隘地局限在性别语境内,一切受到禁止职业歧视法律保护的人群,如少数族裔、残障人士、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等均可能成为敌意环境型骚扰的受害者。(43)
第二,将性作为利益交换的条件,此即为利益交换型的骚扰。这种类型的骚扰直接与性相关。有别于敌意环境型骚扰通过制造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达到排斥目的,利益交换型骚扰将性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即“领导或上司明示或暗示以性方面的要求作为员工或求职者取得职务或丧失职务或变更其劳动条件的交换”。(44)这种类型的骚扰既可以发生在不同性别之间,也可能出现在同性内部。只要性成为工作利益的交换条件,即成立利益交换型的骚扰。利益交换型骚扰传递着被骚扰者并非职场同仁而仅仅是性客体的消极信息,(45)通过对性的物化将特定性别的人群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增大这部分人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成本,达到固化其不利地位的目的。因此,无论是敌意环境抑或利益交换型的骚扰均有必要置于禁止职业歧视的法律框架下予以规制。
(四)拒绝提供合理的工作便利
用人单位除负担不歧视的消极义务以外,还应承担向有特殊需求的劳动者提供合理便利的积极义务。在禁止职业歧视的语境中,所谓便利就是对通常程序、步骤或者设施等的改造。(46)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要求用人单位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根据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调整其工作时间、地点、方式或者对工作场所等进行改造。这项义务的确立旨在通过非对称的平等抵消特定群体面临的不利限制,通过改造环境提升其参与程度,通过课予能动义务督促用人单位积极作为。(47)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合理便利诉求置若罔闻的,当以职业歧视论之。(48)
一般来说,宗教信仰上的少数派、残障、性别等是劳动者可以据以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合理便利的主要事由。事实上,最初也正是用人单位在予其员工便利以遵守宗教仪轨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方才促成合理便利这一积极义务的诞生。(49)在“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v.Simpsons-Sears”案中,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用人单位拒绝为因宗教信仰缘故不能在安息日工作的员工提供调整工作时间等合理便利的行为构成职业歧视。(50)随后,合理便利义务在禁止残障歧视中得到法律的广泛承认。用人单位但凡针对残障劳动者作出拒绝录用、解雇等不利决定,必须是在已经为残障劳动者提供了合理便利而其依然无法完成岗位主要职责的前提下。在“Chacón Navas v.Eurest Colectividades SA”案中,针对Eurest公司以Chacón女士患病不能坚持工作予以解雇的做法,欧洲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不经提供合理便利而径行以残障员工无法胜任工作为由予以解雇构成歧视。(51)
(五)报复反抗职业歧视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因员工举报其实施职业歧视,或者在其他员工举报单位实施职业歧视的案件中协助调查、提供证据或其他帮助而给予不利对待的,构成歧视性报复。报复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压制对职业歧视的挑战。达到此种效果甚至不需实际实施报复,只需让潜在的挑战者明白反抗必将承受高昂代价,远远大于可能的收益,就能迫使劳动者对歧视噤声。(52)由此可见,对报复的规制必然是禁止职业歧视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环。(53)
在诸项法律应当禁止的歧视行为中,唯有报复保护的对象不限于归类事由关联的特定人群而完全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因为实施了反抗职业歧视的行为而面临用人单位的不利对待。为了尽可能地鼓励劳动者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平等就业权利,对表现为不利对待报复的理解应当适当从宽,不宜局限于解雇、降职等较为严厉的行为,盖因用人单位可以采取不直接影响劳动者雇佣状态的方式实施报复或者在工作场所以外对其造成伤害。(54)报复的对象既可以是劳动者本人,也可以是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第三者。同样,对实施报复的时间判定亦有必要作适当延展。在“Belinda Jane Coote v.Granada Hospitality Ltd.”案中,欧洲法院即将雇佣关系终结后用人单位因曾被其举报实施性别歧视而拒绝为前雇员重新就业出具推荐信的行为判定为报复,进而纳入禁止职业歧视的法律框架中予以救济。(55)
四、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
法律禁止职业歧视旨在通过有限度地干预实现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雇用自由的平衡,确保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用人单位遴选适格劳动者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不得以禁止职业歧视之名强迫用人单位接受无法胜任的劳动者或者承受其他不合理负担。鉴于此,法律在限制雇佣自由——厘定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的遴选劳动者的归类事由和实施的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应当为用人单位提供有针对性的抗辩事由以阻却特定行为的违法性,确保雇佣自由不因禁止职业歧视而被过分压缩。
(一)真实职业资格
当被指实施了区别对待的职业歧视,用人单位得以真实职业资格抗辩。因为雇佣领域的机会平等只能是真实职业资格基础上的平等,即具备这种能力资格的人的机会平等。(56)真实职业资格是指用人单位据以区别对待劳动者的归类事由——该事由虽为法律明文禁止,是完成特定工作不可或缺的条件。《消歧公约》即规定,对任何一项特定职业基于其内在需要的区别、排斥或优惠不应视为歧视。(57)
真实职业资格强调,即使用人单位使用了法律所列举的归类事由做出了不利的差别对待,也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58)换言之,用人单位得公然基于禁用事由作出区别对待行为。例如,在电影摄制中基于性别为女性角色挑选女性演员而排除男性,或者为公共安全之故拒绝录用视力障碍者担任公交车司机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抗辩事由的真实职业资格主要针对的是积极实施的而非消极不为构成的职业歧视。(59)
真实职业资格可以阻却“歧视”行为的违法性,故对其适用应予必要限制,防止事由滥用动摇禁止职业歧视法律的根基。一方面,在立法上得根据本国消除职业歧视的客观需要限制真实职业资格抗辩事由的适用范围。(60)例如,为了应对国内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编在允许用人单位得以真实职业资格对抗宗教信仰、性别、原籍国等职业歧视指控的同时,完全排除了种族作为真实职业资格的可能。(61)欧盟在其《就业框架指令》(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中亦强调,宗教信仰、残障、年龄等仅能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成立真实职业资格。(62)另一方面,法院也得通过严格解释对真实职业资格抗辩事由的使用做出限缩。除非用人单位能够证明禁用事由关联人群均无法胜任特定工作或者在事实上不可能对禁用事由关联人群逐一评估其是否胜任特定工作,该事由不得成立真实职业资格。在“Western Air Lines,Inc.v.Criswe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循此逻辑否决了西部航空公司有关年龄得成立飞行员职业的真实职业资格,公司为保障飞行安全强制下属飞行员在60岁统一退休的做法不构成年龄歧视的主张。(63)
(二)正当经营所需
正当经营所需用于区别影响行为合法性的证成。(64)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用人单位任何形式的遴选标准都必然伴随部分人群受益、部分人群受损的结果。因此,一项表面中立的雇佣政策在实践中若对禁用事由关联人群产生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即为非法,但该措施是用人单位正当经营所需的除外。(65)例如,用人单位要求求职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考虑到农村籍大学生数量较少的情况,学历限制可能不成比例地排除农村户籍求职者,从而构成基于户籍登记状况的区别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经营所需作为抗辩,证明学历限制是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正当需要。
毫无疑问,正当经营所需是较为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抗辩能否成立有赖于法院在个案中具体裁量。但法律可以明确裁量的基准,即通过比例原则的检视。首先,用人单位表面中立的雇佣政策意欲实现的目的必须合法且具体,确系用人单位真实需要并且不包含任何歧视意图。(66)在“Brbel Kachelmann v.Bankhaus Hermann Lampe KG”案中,欧洲法院认可Bankhaus Lampe银行得因业务收缩裁撤部门之故解雇兼职雇员,其目的正当且足够具体,虽然此种做法可能对女性雇员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67)但在“Erika Steinicke v.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案中,德国一项禁止最近5年内未能全职工作满3年的老龄兼职员工继续出任公务员的规定被指对女性造成区别影响。针对联邦就业局声称该规定系为促进就业之主张,欧洲法院指出,促进就业确为正当之目的,但仅仅将此规定的目的概括为促进就业则过于笼统,不足以令人确信其无涉性别歧视之意图。(68)
其次,用人单位为实现其正当目的而在雇佣政策中选择的手段是否将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侵害限制在最小程度内。“遵守比例原则要求对个人权利的损害必须尽可能地在平等对待原则与其意欲实现的目的之间相互协调。”(69)只要还存在着既能满足用人单位经营所需又对事由关联人群侵害更小的其他手段,相应政策应无法通过法院检视而构成区别影响的职业歧视。(70)在“Loredana Napoli v.Ministero della Giustizia”案中,意大利法律规定担任狱警须接受为期12个月的实训,缺席训练30天以上不得参加狱警任职考试。Napoli女士因生产需依法休强制产假3个月而被终止训练资格。欧洲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为公共安全之故,法律确可依法拒绝未完成全部训练课程的个人参加狱警任职考试,女性因生产可能无法完成全部训练也是事实。但在为期12个月的训练中,对因生产强制休产假3个月的女性而言,法律既不考虑女性因生产而未能完成的是哪一阶段的训练,也不考虑其已经接受过的训练而一概剥夺女性参加任职考试的资格,换言之,在有多个方案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没有选择对女性平等就业权侵害最小的方案,当不能通过比例原则的检视。(71)
(三)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
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针对提供合理便利的积极义务。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特定宗教信仰、残障劳动者等要求提供的便利将会在实质上改变工作性质或者对其经营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度负担,则可免除提供被请求便利之义务。
实质变更重在评判便利措施对职位本质要求的影响。例如在声乐教师招聘中,学校得要求求职者做现场演唱以判断其声乐水平,有言语障碍的求职者当不能请求校方提供安排他人代为演唱等便利,因为这将在根本上改变岗位的实质要求。过度负担重在评估便利措施可能对用人单位造成不利影响的程度,亦即对用人单位经营能力的限制或对其他员工权利的损害程度。(72)法律可以规定过度负担抗辩事由,但考虑到用人单位千差万别的情况事实上很难给定具体的评判标准而必须由法院在个案中进行裁量。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Central Alberta Dairy Pool v.Alberta(Human Rights Commission)”案中即提出可以从提供便利措施的成本、对集体协议的背离程度、对其他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对员工队伍和设施可替换性的影响、用人单位规模大小以及安全保障等角度评估便利措施是否对用人单位构成过度负担。(73)
(四)平权措施
平权措施旨在对过去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延续进行补救,(74)以确保所有人充分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利。(75)其实质是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实现就业和职业机会等稀缺资源的逆向倾斜配置以优待诸如女性、少数族裔、残障人群等在历史上饱受歧视而处于社会边缘境地的群体,帮助其尽快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平权措施是国际社会和各国在就业领域中快速推进平等所仰赖的重要手段,涵盖从强力的配额录用到相对柔和的员工构成情况报告评估等诸多形式。例如,印度在1977年以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宣布在中央政府中为视力、听力障碍者各保留1%的职位并放宽对残障求职者的年龄限制;(76)奥地利要求用人单位每雇佣25人必须雇佣1名残障者;德国《社会法典》鼓励规模在2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雇佣至少5%的残障者。(77)毋庸置疑,平权措施是国家意志主导下的“职业歧视”,是相对于基于市场的竞争性资源配置以外的基于公权力的指令性资源配置方式。
平权措施的诞生源于对市场自身无法消除职业歧视的基本判断。无限制的市场竞争和资本累积只会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使很多低下阶层的人丧失有效实践各种自由的条件,又或是自由本身。(78)即使有法律对平等就业和职业机会的承诺,但长期遭受歧视的群体事实上根本无法以平等姿态参与市场竞争。貌似公平的竞争只会不断强化这些群体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经济歧视对经济上的少数派往往最为严重。(79)因此,必须向受到歧视的群体提供帮助,以达至基本的公平。(80)
作为消除职业歧视过程中必须承受的“恶”,平权措施被寄以改变社会机会、机构和程序,消除歧视背后所包含的权力支配关系、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偏见的期望。(81)只要是为了消除事实上的歧视,而且是合理、客观和有节制的手段,这种措施就是合法的。(82)但是,除指向对象略有差异,平权措施与区别对待的职业歧视在外观上几无二致——两者都是基于相同的归类事由(如种族、性别、残障等)有选择性地配置资源。正因为如此,法律必须明确将平权措施从职业歧视范畴中分离出去,单独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五、结语
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是作为基本权利的宪法平等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延伸,是用人单位肆行雇佣自由的终结。在我国宪法尚不能直接进入司法实践的情况下,平等权利在劳动领域的充分实现更有赖于专门的反职业歧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为保障劳动者不受歧视的权利,营造平等的劳动关系而努力。所有这些朴素的道理意味着,规制职业歧视必然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
仅仅在法律文本中嵌入禁止职业歧视的一般规定无法兑现“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的承诺。法律必须完成对职业歧视定义的建构,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确定禁止用人单位使用的归类事由、禁止用人单位作出的行为模式以及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让空转良久的法律禁令尽快落到实处。
消除职业歧视立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之上。(83)职业歧视的根本危害在于其否定平等、正义引起的严重后果——阶层因之而固化,群体因之而对立,社会的和谐稳定将无可避免地面临严峻挑战。毕竟,平等问题牵涉广泛、矛盾交织,如何解决会影响到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进程。(84)时至今日,美国、欧洲、南非等国家和地区依旧受累于种族歧视留下的沉疴痼疾,印度仍然身陷种姓歧视所造成的龃龉和嫌隙,非洲、日本等则远远没有摆脱性别歧视的拖累……职业歧视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职业歧视的代价必将由社会共同体一体承受,无人能在其中独善其身。职业歧视概念的法律建构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职业歧视问题,但在法律中写入职业歧视的完整定义无疑将会是我国消除歧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感谢《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批评意见,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Equality at Work:Tackling the Challenges:Global Report under the Follow-up to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ILO Publications,2007,p.10.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2013年第22期。
③王春霞:《全国人大财经委: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确有必要》,载《中国妇女报》2015年11月6日第A1版。
④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我国法律上最早有关禁止职业歧视的规定。
⑤详见《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订)第22条至第27条规定,《劳动法》第12条、第13条规定以及《就业促进法》第26条至第31条规定。
⑥近年来部分通过调解结案的职业歧视案件可以参见徐伟,孙怀君:《全国首例陈旧性肺结核就业歧视案结案》,载《法制日报》2012年2月25日第8版;宋利彩:《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和解结案》,载《中国妇女报》2013年12月18日第A01版;万静:《江西艾滋歧视第一案达成调解协议艾滋感染者首次获赔4.5万元》,载《法制日报》2013年1月26日第6版;罗双江:《拉锯15月,全国首例户籍歧视案调解》,载《扬子晚报》2014年8月9日第A2版。
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针对我国的普遍定期审查中,葡萄牙、爱尔兰、荷兰等国建议我国将歧视的法律定义写入法律或者设立反歧视法律法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2012年就我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履约情况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委员会赞扬缔约国法律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但对歧视残疾人的行为缺少全面定义感到关切……委员会明确鼓励缔约国对歧视残疾人的行为作出法律界定,并在其中列入禁止间接歧视的规定。”
⑧详见蔡定剑、刘小楠主编:《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喻术红:《反职业歧视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等。
⑨刘小楠主编:《反就业歧视的策略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⑩[美]埃里克·A.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11)参见刘海洋、陈世军:《劳动就业中的“相貌歧视”问题研究》,载《兰州学刊》2009年第5期。
(12)Bonnie Berry,Beauty Bias: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Power,Praeger Publishers,2007,p.6.
(13) See William R.Corbett,”Hotness Discrimination:Appearance Discrimination as a Mirror for Reflecting on the Body of Employment-discrimination Law” 60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615,626(2011).
(14)王彬、潘金文:《美国禁止容貌歧视的立法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3期。
(15)林嘉、杨飞:《完善劳动就业权法律保障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
(16)阎天:《重思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当代兴起》,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17)参见张时飞、唐钧:《中国就业歧视:基本判断》,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8)如变性者(Transgender)等即属于性少数人群范畴。
(19)对非传染病患者的职业歧视可参见赵文明等:《湖南现全国首例公务员考试色盲歧视案》,载《法制日报》2011年12月19日第7版;高培蕾、王帝:《成绩第一,却因高血压被拒聘》,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8日第3版;纪立农:《别歧视I型糖尿病患者》,载《光明日报》2012年7月29日第6版。
(20)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际人权法层面,联合国于1965年和1979年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国内法层面,英国于1965年通过了《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of 1965),禁止基于肤色、种族、原籍国等的歧视;1970年和1975年分别通过《平等报酬法》(Equal Pay Act of 1970)和《性别歧视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5);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编(Title VII of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用的五类事由中,先赋事由占据四类(即种族、肤色、原籍国和性别)。1967年,美国通过《雇佣年龄歧视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澳大利亚于1975年制定了《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5)。
(21)McDonnell Douglas Corp.v.Green,411 U.S.792(1973).
(22)Canada(Attorney General) v.Mossop,[1993] 1 SCR 554.
(23)多重歧视亦称”Combined Discrimination”或者”Compound Discrimination”。
(24)Iyiola Solanke,”Infusing the Silos in the Equality Act 2010 with Synergy” 40 Industrial Law Journal 336,344(2011).
(25)Colleen Sheppard,Multiple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ld of Work,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1,pp.2-3.
(26)James Hand,”Combined Discrimination-section 14 of the Equality Act 2010:A Partial and Redundant Provision?” 2 Public Law 482,483(2011).
(27)“区别对待”主要见于美国学界。在欧洲,对应的法律概念是“直接歧视”(direct discrimination)。
(28)周伟:《论禁止歧视》,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
(29)Teamsters v.United States,431 U.S.324(1977).
(30)Colleen Sheppard,”Mapping Anti-discrimination Law onto Inequality at Work:Expanding the Meaning of 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Law” 151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012).
(31)See Rebecca White,Employment Law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Essential Terms and Concepts,Aspen Publishers Inc.,1998,p.77.
(32)Barbara T.Lindemann,Paul Grossman,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BNA Books: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ect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ee,2007,p.10.
(33)详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828号民事判决书。
(34)详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2014)杭西民初字第1848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
(35)Sandra Fredman,Discriminati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77.
(36)陆海娜:《我国对平等就业权的国家保护——以国际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37)“区别影响”主要见于美国学界。在欧洲,对应的法律概念是“间接歧视”(indirect discrimination)。
(38)Barbara T.Lindemann,Paul Grossman,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BNA Books: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ect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ee,2007,pp.109-110.
(39)丁晓东:《探寻反歧视与平等保护的法律标准——从“差别性影响标”切入》,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
(40)Griggs v.Duke Power Company,401 U.S.424(1971).
(41)Gabrielle S.Friedman,James Q.Whitman,”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241,241(2003).
(4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43)就我国而言,性别领域之外的骚扰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中都未涉及。即使是在性别领域,除2012年《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在骚扰问题上采取性别中立立场,承认男性亦可成为性骚扰对象外,《妇女权益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诸多地方立法中均将免于性骚扰作为女性独享的特殊权益。
(44)张新宝、高燕竹:《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4期。
(45)Raymond F.Gregory,Women and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Overcoming Barriers to Gender Equalit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3,p.133.
(46)Lisa Waddington,Anna Lawson,Disabi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An Analysis of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Law within and beyond the Employment Field,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09,p.25.
(47)Sandra Fredman,Discriminatio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6-217.
(48)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Equality at Work:The Continuing Challenge——Global Report under the Follow-up to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ILO Publications,2011,p.47.
(49)See Dallan F.Flake,”Image is Everything:Corporate Branding and Religious Accommodation in the Workplace” 16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699,711(2014).
(50)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v.Simpsons-Sears,[1985] 2 S.C.R.536.
(51)Chacón Navas v.Eurest Colectividades SA,Case C 13/05.
(52)Deborah L.Brake,”Retaliation” 90 Minnesota Law Review 18,36-37(2005).
(53)事实上,我国《劳动法》第101条禁止用人单位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规定可以认为已经具备了禁止歧视性报复的雏形。
(54)Ilene V.Goldberg,Ira Sprotzer,”Protection from Retaliation for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Claims” 5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232,235(2010).
(55)Belinda Jane Coote v.Granada Hospitality Ltd.,Case C-185/97.
(56)齐延平、张录荣:《论平等雇佣的法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57)详见《消歧公约》第1条第2款规定。
(58)李薇薇:《反歧视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59)Evelyn Ellis,Philippa Watson,EU Anti-discrimination Law,OUP Oxford,2012,p.382.
(60)Samuel R.Bagenstos,”Employment Law and Social Equality” 112 Michigan Law Review 225,240(2013).
(61)详见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703条第(e)款规定。
(62)详见《就业框架指令》序言部分。
(63)Western Air Lines,Inc.v.Criswell,472 U.S.400(1985).基于类似思路裁判的案例还可参见International Union,United Automobile,Aerospace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Workers of America,UAW,et al.v.Johnson Controls,Inc.,499 U.S.187(1991).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雇主以工作涉及铅暴露,可能影响生育而不雇佣女性的做法。
(64)部分国家,如加拿大在“British Columbia(Public Service Employee Relations Commission) v.BCGSEU”案之后,不再继续严格区分区别对待和区别影响案件。两类案件得统一适用真实职业资格作为抗辩。See Joseph A.Seiner,”Disentangling Disparate Impact and Disparate Treatment:Adapting the Canadian Approach” 25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95(2006).
(65)Hiroya Nakakubo,Takashi Araki,Catherine Barnard,New Developments i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8,p.17.
(66)Christa Tobler,Limits and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of Indirect Discrimination,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8,p.32.
(67)Brbel Kachelmann v.Bankhaus Hermann Lampe KG,Case C-322/98。因Bankhaus Lampe银行兼职雇员多为女性,故裁撤兼职雇员意味着更多的女性将面临不利后果。
(68)Erika Steinicke v.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Case C-77/02.
(69)Werner Mangold v.Rüdiger Helm,Case C-144/04.
(70)See Sandra Fredman,”Addressing Disparate Impact:Indirec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ublic Sector Equality Duty” 43 Industrial Law Journal 349,354(2014).
(71)Loredana Napoli v.Ministero della Giustizia,Case C-595/12.
(72)Richard L.Wiener,Steven L.Willborn,Disability and Aging Discrimination:Perspectives in Law and Psychology,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0,p.23.
(73)Central Alberta Dairy Pool v.Alberta(Human Rights Commission),[1990] 2 S.C.R.489.
(74)敖双红:《平等保护还是隐形歧视——以劳动法为例》,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75)平权措施在美国通常被称为“affirmative action”;类似措施在欧洲的对应名称是“positive action”;在印度则为“compensatory discrimination”。持反对意见者称其为“reverse discrimination”。
(76)Jane Hodges-Aeberhard,Carl Raskin,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Employ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1997,pp.30-31.
(77)Marc De Vos,Beyond formal Equality:Positive Action under Directives 2000/43/EC and 2000/78/EC,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7,p.46.
(78)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5-36页。
(79)参见[美]加里·贝克尔:《歧视经济学》,于占杰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0页。
(80)Nicole Busby,”Affirmative Action in Women’s Employment:Lessons from Canada” 33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42,45(2006).
(81)李薇薇、Lisa Stearns主编:《禁止就业歧视: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82)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0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E/C.12/GC/20。
(83)林燕玲主编:《反就业歧视的制度与实践——来自亚洲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84)阎天:《反就业歧视法的一般理论——中美两国的建构与反思》,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本文刊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作者:李成,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