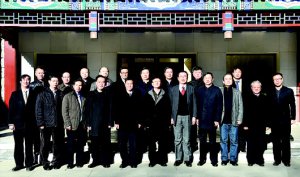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407号 再审申请人张湘琳因与被申请人林加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湘琳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与《合作协议书》是针对同一股权性质资产标的进行的交易。首先,《合作协议书》引言及第一条中都明确提到,转让标的为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永福贵公司)的40%股份,与股权转让协议完全一致。而且《合作协议书》中写明,厦门永福贵公司全资成立贵州永福贵公司,即由厦门永福贵公司出资。那么所谓的前期投资也应当是由厦门永福贵公司支出的,应属于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资产的一部分,不应当割裂。如果两份协议并不指向同一股权性质资产标的,则会出现重叠购买及2次付款的情况。如果张湘琳已经成为了厦门永福贵公司的股东之一,则无需再对设立的子公司贵州永福贵公司按股权比例进行出资,这部分是张湘琳已经持有的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应当包括进去的。其次,在林加其开出的收据中也写明收张湘琳、李至强支付的六百万元是股份款,并不是针对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前期投资分摊款。在张湘琳还未成为厦门永福贵公司股东时,先就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投资项目款进行支付,并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且贵州永福贵公司是由厦门永福贵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并不是个人,即便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也应当是与厦门永福贵公司签订协议书。张湘琳、李至强承担的所谓项目运作及筹办的600万元,实际上是通过厦门永福贵公司成本量化的股权价值,是计算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真正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作协议书》实际上是针对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这个同一资产标的的交易,且张湘琳已经完成支付,并不存在违约。本案判决仅根据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作协议书》就认定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忽视协议本质上针对同一股权标的,以及林加其亲手签署收据自认的股权标的款定性,是根本性的错误。(二)《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承诺合作协议签订之时,除员工工资外公司没有对外负担债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公司及贵州子公司的公司损益双方按照比例承担和分享”。这一约定首先表明甲方(林加其、叶彦君)是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承诺,其次表明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厦门永福贵公司与贵州永福贵公司的亏损和收益均按照股份比例承担和分享。这说明双方是对股东之间的权益进行约定,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是对项目前期投入的约定,也不是对项目合作事项的约定。因此,《合作协议书》本质是股权转让协议,无非是将子公司将来的损益进行了一并约定,说明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签订一个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转让和项目运作以及项目损益的承担和分享一并解决,但均以股权比例和600万元对价款为基础,并不是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为基础。这也说明《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而订立的,不需要实际支付对价款。否则,如果双方已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张湘琳成为厦门永福贵公司的股东之一,则张湘琳事实上已经间接享有了贵州永福贵公司的相关权益,间接承担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损失,不需要双方再签订《合作协议书》进行约定。这也从相反的方向推翻了林加其关于两个协议系两个法律关系的主张。(三)本案判决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而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令解除协议,适用法律错误。假设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在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也就是说,协议的解除只能是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且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的协议。本案中,张湘琳已经支付了股权款,且林加其已经收到张湘琳的股权款并开出确认收到股权款的收据,亦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不符合约定的解除协议事项。本案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双方对合同解除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除。而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解除条件,且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理应被遵守。况且,张湘琳已经成为厦门永福贵公司的股东,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并承担了股东的义务。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也应该维护公司股权的稳定性,只在双方之间形成债权而已,不应该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书》标的是否同一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转让标的是厦门永福贵公司20%的股权,转让价格是400万元人民币,付款方式是张湘琳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40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林加其。《合作协议书》在引言部分载有“现甲方与乙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将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的100%股权中的40%股权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还就甲方前期为水泥厂项目投入的相关费用,以及股权转让后总公司投资贵州子公司项目的建厂及投产后的相关发展事宜进行协商”,从该约定看,转让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和就项目前期费用及贵州永福贵公司建厂及投产后的相关发展事宜为双方协商的相互独立的两部分内容。《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张湘琳和李至强支付的600万元系分摊林加其、叶彦君为项目运作及筹办设立贵州永福贵公司以及购买项目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并未约定该款系厦门永福贵公司40%的股权转让款。结合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书》均系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难以排除《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转让股权的内容系重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可能性。因此,从协议内容来看,张湘琳关于两份协议标的均为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能否依据林加其向张湘琳出具的收据证明双方股权转让依据的是《合作协议书》的问题。虽该收据载明系根据2011年12月13日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支付的股份款,但鉴于《合作协议书》第一条并未约定转让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的对价为600万元,且“股份款”的解释即可能是转让股权的价款,也可能是分摊前期费用入股该项目的款项,本身涵义存在模糊性,张湘琳主张据此推断《合作协议书》约定的600万元即为转让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的对价,并进而主张两份协议书的标的同一,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