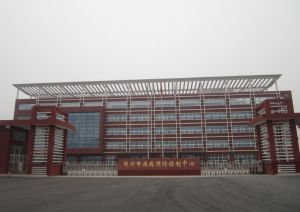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 季卫东 社会的法制化与“治理三重困境”问题 近些年来,“法治中国”的构想推动了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渐次呈现出来的具体现象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数量的急剧增加;交通整治和反恐举措使得管制型法规以及相应的有序化机制更加发达,在主要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街口、在交通干线的每一个交汇点,都可以看到警察和警车的活动;法律纠纷的规模、诉讼案件数以及律师人数都在迅速膨胀,再加上周而复始的涉法涉讼信访案件,已经造成审判机构的超载;积极有为的司法政策已然渗透到政法界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对非公领域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弱反倒有所增强,在防控风险的背景下,行政规制又重新得到肯定;等等。 我国当下的这种情形,与1970年代的欧美颇有那么一些形式上的类似性,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慨。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法治发达国家,社会的法制化程度日益加深,出现了所谓“法律的环境污染(legal pollution)”“诉讼爆发(litigation explosion)”“律师过剩社会(overlawyered society)”等病态,甚至引起了国家秩序的“合法性危机”。批判社会理论的旗手尤根·哈贝马斯把这样的大趋势表述为“生活世界受到(法律)系统的殖民地统治(colonial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by the system)”。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主流法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学者都参与到相关的辩论之中。其中衮塔·托依布纳教授指出,社会的过度法制化或者畸形法制化导致了“治理的三重困境(regulatory trilemma)”,即(1)法制与社会互相无视,或者(2)法制过度干预社会导致社会崩溃,或者(3)社会对法制提出过度要求导致法制崩溃这三种可能性,在国家权力、法律规范与社会秩序之间形成了某种“剪刀石头布”的关系(泽秀木:“介入主义的界限及其程序化——‘法化’研究序说”,载1990年《法的理论》第10号,117—179页)。 为了使社会去殖民地化,为了克服国家权力和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为了跳出社会治理的上述三重困境,欧美很多法学研究者和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对症疗法是从国家必须直接管制转向间接管制,充分借助社会的自治机制来形成和维护秩序,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有必要鼓励纠纷解决机制的自主化和多元化,特别是加强一定文化涵义脉络之中的调解机制。中国自古以来特别重视调解及其他非正式的解纷手段,相应地忽视了审判方式的合理化;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官僚机构的非正式主义倾向以及调解的蜕变,造成了强制与合意的短路连结。因此,我们的制度改革取向和路径当然与欧美有所不同,重点应当放在弥补自己的缺陷,加强法院的程序公正意识以及法律推理的技艺,并尽量让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解纷方式适当区隔。尽管如此,在社会法制化程度不断加深,审判的正当性资源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治理的三重困境”以及政法系统强势介入日常生活领域之类的问题的确已经浮现,有时甚至还出现了极端化事态。因此,欧美各国以及日本关于替代性或者选择性解纷方式的讨论和举措还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实现社会的自治 概而论之,社会自治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不同类别共同体,从传统的宗族(血缘共同体)、村落(地缘共同体),到当代的职场(功能共同体)、NGO(使命共同体)、地方(投票共同体),不一而足。共同体正义(communitarian justice)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次级秩序,与法律的关系是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群众运动体,包括所谓“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 和“抗议的营业(protest business,主要指通过专业工作人员运行的抗议运动,把获得支持作为收入来源并通过集权化的决策机制和信息提供活动来支撑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包括寻求罗尔斯式“重叠共识”的沟通平台。在欧美的语境里,“群众正义(popular justice)”本来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反命题,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质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司法和执法的群众路线,实际上群众正义已经被深深嵌入法律体系之中,形成了某种矛盾制度化的结构。在这里,群众正义既不是法律的次级秩序,也不是法律的对抗秩序,而是与法律犬牙交错在一起,构成法律体系的一个组织部分,显示了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社会自治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不得不把权利的诉求和实现与诉讼切割开来,使得动用正式的法律手段的决定在社会关系中适当相对化,从而使得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更加多元化。在这个意义上,依法解决纠纷的选项可以构成一个光谱般的清单,从表达不满、公开指责、提出诉求、进行谈判,到寻求调解和仲裁以及诉诸法院,诉讼成为穷尽一切自我救济方式之后的最后手段。奥斯丁·萨热特和杰尔·格鲁斯曼(Austin Sarat & Joel B. Grossman)曾经分析在社会语境中对纠纷进行界定的涵义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变数,例如强制的程度、制裁的范围和严重性、适用规范的性质和形态、第三者介入的程度和方式等,并通过公共性与私人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这两对概念建立了给不同解纷方式定位的坐标,得出了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私人的、非正式的解纷方式,主要指当事人之间通过沟通实现自我和解或私了,或者当事人双方都对调解人具有充分的信任。显而易见,在这里合意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第二种类型是公共的、非正式的解纷方式,包括不同领域的仲裁机构或者辩诉交易、审前协商。此外还有设立在行政部门(例如公平交易委员会、建筑工程纠纷审查会、公害投诉咨询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劳动委员会等等)的选择性解纷程序。第三种类型是私人的、正式的解纷方式,例如私立法院、民间的准司法程序、劳资纠纷解决程序。第四种类型是公共的、正式的解纷方式,这就是审判制度,当事人往往采取对抗的态度,决定起诉与否的因素主要是费用和效益的计算。 基于纠纷解决多元化的立场,上述四种类型其实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每一类型还可以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使得解纷方式不断趋于多层多样。例如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中心、医师赔偿责任审查会、国际商事仲裁协会、商事调解中心、承包合同投诉处理委员会、仲裁机构的调解程序等等。 嵌入审判制度的选择性解纷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