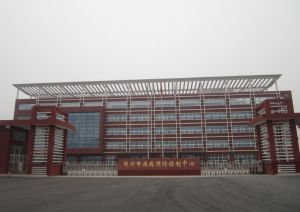|
田飞龙 从政治决策、专家参与到大众关注,民法典编撰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道绝美风景。民法学者自然奋身其中,唯恐在此历史关头错失角色与贡献,于是各家草案版本明面较劲,暗里互参。宪法学者亦不甘寂寞,不仅在民法学者预防针式的“宪法依据说”争议中迎头而上,更是以宪法至上、基本权利与教义学功底试图结构性切入这一民事立法过程,也符合宪法学界自身在体制化瓶颈下寻求以“部门宪法”路径别开生面的发展谋略。民法以权利本位和私法自治为圭臬,对规制性行政国家保持本能戒备,因此与热衷行政规制研究的行政法学也难有太多默契。甚至法律史学亦感觉到自身边缘化之危机,以文明复兴为政治正确凭据试图打破主流法学界的知识垄断和话语霸权,提示中国民法典需奠基于本土传统并亲和民意,不可纯凭理性自负而数典忘祖,孤傲强行,造成对本土生活方式的殖民化并与实践为敌。 从历史来看,各国民法典之编撰皆难以摆脱理性立法与传统基础之争议。1804年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律现代性的奠基石,按美国学者泰格的说法是现代法律意识形态的凝结,但熟悉法国立法史的人都知道,其中也存在理性与传统之争。在法国模范刺激下,19世纪初的德国启动民法典编撰工程,刺激萨维尼创立历史法学并发起路线争论,将理性立法与传统基础的张力显著化。1930年代,国民政府亦开始编撰民法典,面临同样困境,以启动民事习惯调查及开展一定范围公议作为科学工作程序,但成形法典对本土传统甚至民意习惯的吸纳依然有限。从现代法律史来看,尽管疑虑重重,争议不断,但民法典已成为一国法律体系的标准配置,成为指导民事基本生活与良好公共秩序的规范基石,成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甚至有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根据法律史以及民法的价值优越性,民法是当然的母法,有“民法根本说”。不过,在人类告别城邦自治走向大国共和的进程中,立宪理性逐步超越并吸收民法的自治理性,宪法成为政治国家的根本法,成为笼罩民法秩序的立体法律秩序,对此亦不可不察。因此,当民事立法或民事制度改革与宪法依据存在冲突时,我们仍需仔细检讨宪法规范的原旨及其解释空间,不可径凭学者的启蒙冲动与隐藏的自然法无意识而回避或曲解宪法依据。2006年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沸沸扬扬,十年后民法典编撰已大有改观,根由在于改革共识深化了,对宪法秩序内涵的理解更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严肃的民事立法合宪性问题一劳永逸解决了。 民法典编撰不仅有合宪性的一面,还有实质正当性的一面。这里的实质正当性,主要系于传统和民意。民法典不仅涉及财产保护和交易便利,还涉及民族传统传承、民间习惯保护与生活方式维系,涉及对市民社会中个体与社群之意义/行为的诠释和引导,因此其立法过程必须代入传统和民意。传统是整体法律秩序的历史基础和价值内核。民意则是当代存在的民事习惯与共同生活偏好。在这一实质正当性场域,通常被称为民法专家的立法工作者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和判断,而执政者又不适合直接作出代表性决断,因此需要开放给公认的科学立法程序:其一,民事习惯调查与整理,即将有效的本土民事经验吸纳入民法典,扩大民法典与民事生活的交融度与亲和性;其二,议题性公众参与,即在涉及具体制度选择与方案构造时,专家理性有不充分性,需要开放公众参与以吸纳公众知识,矫正专家偏颇,以立法民主性提升民法典的民意合法性,而具体工作方式上不宜太过粗放地搞一次性草案意见网上征集,而需要根据具体议题举行公众听证会、座谈会等,确立说明理由与意见吸纳情况公示机制,以多形式交叉反馈的方式增强立法公众参与的实效性,不搞走过场;其三,价值基础的反思与拓宽,即中国民法典不能仅仅以西方各国民法典或一般民法价值为完全基础,而需要接纳本土价值,比如将“家”作为正式民事主体,不仅作为契约主体,而且作为伦理与治理主体,再比如在夫妻财产制上需要体现对家庭整体性的保护,纠正2010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价值失衡;其四,立法谦抑性与对未来创新开放,即中国不是普通民族国家的标准转型,而是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体系性崛起,其内政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国与新党国交互建构,而在外向维度上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创新机制开辟超国家共同体秩序并暗含着更加远大的天下主义制度抱负,这一宏观历史进程必然包含民事价值与制度的超越和创新,民法典编撰是否能够在规范性、前瞻性和谦抑性上保持平和均衡,也是一个挑战。 然而,以上设想皆为程序性理想,具体成效如何笔者并不乐观。以民国民法典编撰为例,其中不乏民事习惯调查、社会公众参与等科学方法之运用,但最终结果并未如人意,假想的本土民事生活方式存在太多零散、冲突、矛盾之处,短时间内无法进行理论上的调理和制度上的优化,在面临立法选择时只能整体追从西方法典模范。任何带有商谈性质的公共理性过程都有一个严格的前提限制,即时间逻辑,具体而言就是立法是政治任务和政治程序,越理想化的工作程序其成效越低,命运越是不堪。我们当然希望制定一部综合古今中西的最优民法典,但这种穷尽一切的立法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自负,是不可能的幻想。时下民法典编撰中亦有学者强烈提出民事习惯调查、会通古典资源等要求,比如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秋风先生就对民法典编撰指导思想的“专家化”以及民法典总则草案的“西化”有着直接的批评,甚至提出了基于儒家立场的直接修订。然而,以目前法学界的知识结构及立法的时间限定,民法典的“儒家化”基本不可能,即便可能亦未必可欲,理由是中国民法典不可能背离中国全球化的现实而摆脱法律现代性的基本概念与框架,而且大陆新儒家的政法研究和现代转换并未成熟完成,中国法学亦未能有效承担尊重和转化本土民事习惯的理论工作,大的结构性突破在理性基础上尚不充分。其实回顾晚清民国之际的法律现代化包括民事立法,当时儒家未衰而西方法学未兴,最后仍主要以西方为模范,其中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理智性判断:中国在法律上学习西方的进程刚刚开始,传统和民意皆具有本土性的保守质地,不宜过度张扬。即便放置今日,我们固然在物质成就和政治心理上已然自信,但难言对西方法律充分把握,亦难言对自家传统与活的习惯已善加诠释与转化,而政治立法时不我待,故很可能重演旧时故事。 |